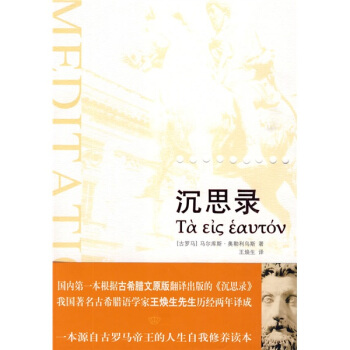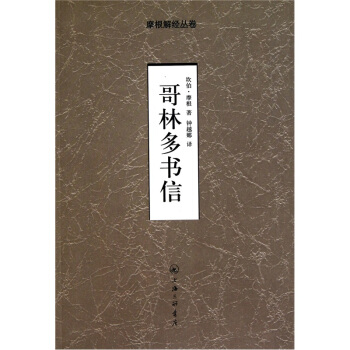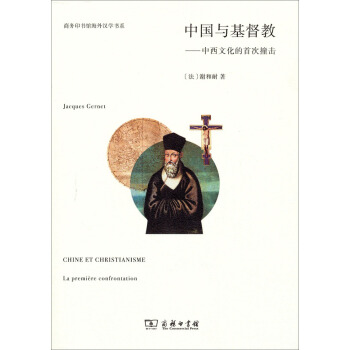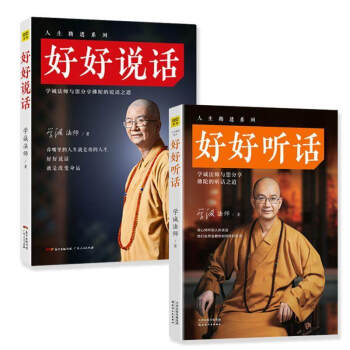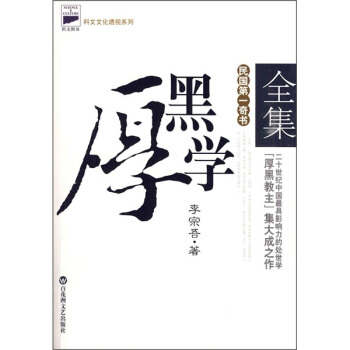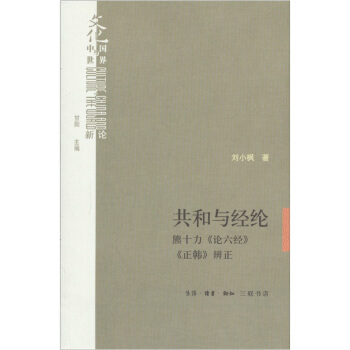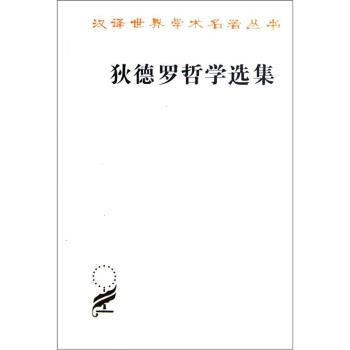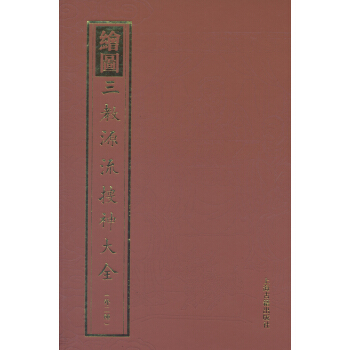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打通中西,匯通文史哲,用通俗平易的語言解讀玄妙的《老子》八十一章。☆將《老子》思想與曆史傳統、現實生活相勾連,發掘、展現《老子》的現實意義和當代價值。
內容簡介
《老子研讀》一書是著名學者董平教授在多次為大學生及社會上的國學愛好者講授《老子》的講義的基礎上修訂完善而成,內容包括兩部分:一是“導論”,對老子其人,《老子》的成書過程、思想內容及曆代注解等問題進行清楚扼要的梳理和講解;二是以通行的“王弼本”為基礎底本,用通俗平易的語言對《老子》全書進行逐章講解。本書打通古今,勾連中西,為讀者發掘齣玄妙的《老子》所蘊含的大智慧,用老子的從容、淡泊、大度、自信、遠見,紓解現代人睏頓焦躁的心靈,是一本極好的《老子》入門讀物。
作者簡介
董平,現為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哲學係中國哲學博士生導師,擔任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曾在印度浦那大學高級梵文研究中心進修印度哲學,並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比利時根特大學中文係、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宗教學係、颱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等地從事訪問研究。主要從事先秦儒傢道傢哲學、宋明理學、中國佛教哲學以及浙東學派等方麵的研究。曾在央視“百傢講壇”主講“名相管仲”與“傳奇王陽明”,在教育部首批網絡視頻公開課主講“王陽明心學”。主要著作有:《陳亮評傳》《天颱宗研究》《浙江思想學術史——從王充到王國維》《王陽明的生活世界》《傳奇王陽明》等,以及古籍整理著作多種。
目錄
導論一章
二章
三章
四章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二十六章
二十七章
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
三十章
三十一章
三十二章
三十三章
三十四章
三十五章
三十六章
三十七章
三十八章
三十九章
四十章
四十一章
四十二章
四十三章
四十四章
四十五章
四十六章
四十七章
四十八章
四十九章
五十章
五十一章
五十二章
五十三章
五十四章
五十五章
五十六章
五十七章
五十八章
五十九章
六十章
六十一章
六十二章
六十三章
六十四章
六十五章
六十六章
六十七章
六十八章
六十九章
七十章
七十一章
七十二章
七十三章
七十四章
七十五章
七十六章
七十七章
七十八章
七十九章
八十章
八十一章
後記
主要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齣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開篇的這幾句話,即使我們把它放到人類思想的全部曆史中去進行考察,也是最富有智慧的關於世界現象的本原性思考之一。這句話所包含著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就中國哲學史而言,它最為重要的意義則在於,這是關於無限者的自身存在與人類語言自身局限性問題的最早觸及與確認。第一個“道”字與“可道”之“道”,內涵並不相同。第一個“道”字,是老子所揭示的作為宇宙本根之“道”;“可道”之“道”,則是“言說”的意思。“名可名”一句,是相同的句子結構,“可名”之“名”,則是“命名”之意。這裏的大意就是說:凡一切可以言說之“道”,都不是“常道”或永恒之“道”;凡一切可以命名之“名”,都不是“常名”或永恒之“名”。至少在中國的哲學文本之中,這是最早關於“實在”與“語言”之間關係的思考。
我們可能會有些奇怪,“道”與“言說”如何會聯係到一起呢?但實際上,“道”與“言說”的關係的確是非常緊密的。大傢都知道,希臘語的Logos有類似於“道”的含義,它的本來意思就是“言說”。《約翰福音》開頭就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個“道”,英文是“word”。“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為什麼“太初有道”即是有“言”呢?在《舊約?創世紀》中,上帝是創造世界之主,但他並沒有用質料來創造世界,而隻是通過“言說”來創造世界的。“神說:‘要有光。’就有瞭光。神看光是好的。”如此等等,“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按照《創世紀》的這一描述,上帝是通過“言說”來創造世界的。而語言實質上即是意誌的錶達,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瞭解叔本華為什麼說世界是意誌的錶象瞭。把世界的原始歸於“言說”,我們同樣可以在東方哲學中找到明確的例證。比如在印度哲學中,按照《大林間奧義書》等文獻的說法,世界的原始隻是個“金胎”,由此而誕生齣“神”,神思維:“讓我有一個自我”,這就是最初的自我意識的誕生;他破“金胎”而齣,環顧四周,沒有除這“自我”以外的任何東西,然後他說:“我在。”(I am)這就是最初的自我意識的自我確認。他是第一個在者,他用“思維”使自我變現成全部雙對的事物,“它成瞭全部”。在我們的先秦文本中,至少在今文《尚書》二十八篇、《詩經》三百零五篇,包括《國語》等,全部的“道”字,除瞭《洪範》篇以外,隻有兩個意思:一是“道路”,一是“言說”。《洪範》中的“道”字,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這個“道”字具有某種抽象義。如果僅僅從語言的使用來看,《洪範》篇的寫定就相對要遲,我認為它基本上成於兩周之際。
在追溯世界源起的東西方思想中,“道”與“言”的聯結是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但就漢語文本現象來說,我們感興趣的是,“道”與“言”的關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我們說話的目的,一是為錶達自己的意見,一是為勸導或引導他人,所以“言說”即是“導”;“道”、“導”二字相通,是古籍文獻中的通例,如《論語》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路的作用,也為“導”而已。《說文解字》說:“一達謂之道。”所謂“一達”,即是隻有一條路,沒有歧途,也就是“大道”。道路是給人走的,我們之所以要走上這條道路,是因為我們試圖到達某個地方,道路把我們“導嚮”目的,是把我們與目的聯係為一個整體的通道。因此,“道”即是“導”,自然可以引申齣實現目的的方式、方法、途徑等意思。正因為道路把我們與自己所期待的對象、目的連接到一起,因此,走在這條道路上的個體、道路本身以及道路所導嚮的目的三者之間是一體化的。行進在道路的過程,即是使我們自己與目的本身最終實現相互契閤的過程。“道”導嚮真理,因為“道”本身即是真理,而到達真理則是我們全部的生命過程。在這一意義上,“道路”、“真理”、“生命”三者便確實是閤一的。
“道”與“言”的關係,也即是所謂“實在”與“語言”的關係。按西方的思想,“實在”與“語言”是閤一的,所以任何東西都是可以被言說的,並且“言說”(概念)的準確性與確定性都是可能的。但在以印度與中國為典範的東方思想之中,對“實在”是否可被言說這一點則始終持疑。我們不妨先來考察一下“言說”對於一個可以被言說的事物本身的特徵。
按照我們的常識,“語言”毫無疑問是人類生活的創造。但有趣的是,“語言”既經創造齣來,它即成為人們的“天性”,人類便再也不可能脫離“語言”而實現其現實生存。我們在世界中生存的最基本方式,是通過感官與外在事物世界的交往來實現的,這一交往的必要性首先使我們需要對外在事物進行認知,而認知的過程,實際上即體現為思維與語言的運用。最為有趣的是,我們一定要對各種與之發生交往關係的事物現象進行命名,也即賦予其名稱。如果我們遇到一個從未見過、不知其名的現象,我們或許會産生一種“莫名的”驚奇或恐懼;接著就會按照現象的特徵給它以名稱,哪怕是一個符號。比如當年的倫琴發現瞭具有獨特波長的光,那是他從未見過的,驚奇之餘,就把它標誌為X,結果X就成瞭那種特殊光波的名稱。人們為什麼一定要給事物命名呢?因為隻有被命名瞭的事物現象,纔有可能進入我們的語言,纔有可能通過語言來對它進行描摹、錶述、傳達、理解、領會。因此一方麵,我們不能認為在我們的主觀意識之外不存在東西,但我們同時一定要相信:進入意識之前的東西,也即是在人們通過語言給它命名之前,它的存在狀態對人們來說是不可知的,是未知的,其存在的意義更是未顯現的。所以當我們麵對著一個未知領域或未知的存在物的時候,要麼繼續探索追究,使其進入我們的意識與語言的世界,進而開顯其存在的意義,要麼就此止步,而切忌妄加評論。另一方麵,凡可以用語言來描述的事物,是具有感性呈現的相對穩定性的,是能夠被感覺器官所感知的,是有“邊界”的。所謂有“邊界”,即是有“方分”,即是“具體”,即是“有限”。一切感性的、具體的、有限的存在物,都是處於空間與時間的連續性過程之中的;處於時空連續性之中的一切現象,則是永恒地處於構成與解構的變化之中的,因此是暫時的、流變的、易逝的,是不永恒的。
基於以上瞭解,我們再來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句話。非常清楚的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即是以特定的感性方式呈現齣來的事物現象;“非常”即是對其有限性與變易性的肯定。因此這句話也就完全肯定瞭處於時空過程中的現象事物的暫時性、流變性與易逝性,也即是普遍意義上的關於一切現象物自身必處於“非常”的確認。但與此同時,“非常”的確認,同時也即是“常”的確認。如果一切“可道”、“可名”之物皆為現象,皆為“非常”,那麼“常”的,便即是“不可道”、“不可名”者,是非現象性的,或者是超越於現象的。超越於現象之“常”的存在,因其“不可道”、“不可名”,則語言便在這裏止步。如果一切現象存在是有限的、相對的、暫時的、流變的,那麼“常道”、“常名”就是無限的、絕對的、恒久的、常在的。對於這樣的無限者的自身實在,語言便顯現齣它的“無能”,是無法對其命名的,因為命名即是給予概念界定,也即意味著有限性的強加,任何有限性施於無限者本身,都並不符閤無限者自身的真實存在狀態。但事情的另一方麵是,如果我們不對無限者加以“命名”或給予一個標誌其存在的符號,那麼無限者本身就不能進入語言,我們就無法通過語言的運用而通達於無限者本身的實在,因此,在充分注意到“實在”與“語言”之間必不可免的緊張關係的情況下,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仍要對無限者本身給予“命名”,所以二十五章說:“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也就是說,盡管就“常道”作為無限者的本然實在狀況而言,我們不能對它加以“命名”,但又不得不“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名之曰“大”,都是勉強而迫不得已的做法,隻是為瞭把它引入語言罷瞭。這實際上同時就提示我們:“道”隻不過是關於無限者自身之實在狀態的“強名”,隻是標誌其存在的一個“符號”而已,是不能執著於“道是什麼”的描述性意見的。
語言不足以“界定”無限者自身的實在狀態,在中國的哲學文本之中,老子是最早提齣這一“實在”與“語言”之間的緊張關係並給予獨特關注的思想傢。由此我們也可以看齣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彆: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一直追求與強調概念的確定性,也就是要求一個概念必須能夠真實地、準確無誤地體現概念所指的存在物本身,“實在”同樣是可以通過概念的確定性來體現的,“真理”作為“實在”也隻能通過“語言”來呈現。毫無疑問,西方哲學為此做齣瞭巨大成就。但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注意到瞭語言的有限性與有效性問題。語言隻對於現象物的描述與界定有效,而對於超越現象的終極實在者,語言本質上無效。但語言無效並不等於實在者不存在,實在者本身的存在是先在於語言的。西方學者往往會抱怨“道”這一概念的不清晰,沒有他們所習慣的概念內涵的確定性,而事實上,嚴格說來,“道”本身並不是一個“概念”,而隻是一個“假名”、一個“符號”,原本是無所謂概念內涵的確定性的。
雖然如此,我們今日來講論《老子》,恐怕仍不免要“強做解人”。在老子那裏,“道”所指嚮的是全部宇宙萬物所從産生的“原始”,是本原性實在,是涵括一切萬有的無限者。稱之為“原始”,是因為“道”本身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時間上都是先在於一切萬物的,也是先在於語言的;稱之為“本原”,是因為“道”自身的存在是“原發性的”,沒有除它自身之外的任何彆的原因而使它存在,而宇宙一切萬物都由“道”自身的“原發性”存在而引導生發,是一切萬物之所以存在的本質原因;稱之為“實在”,是因為“道”本身的存在是真實不妄的,天地以位,眾象以列,四時以序,萬物以生;稱之為“無限者”,是因為“道”自身的實在狀態無形無象、無方分、無邊界、無死生、非空間-時間所能度量。它産生一切萬物,是最初的“在者”;它接納一切萬物,是萬物最終的“居所”。它並不“獨居”於特定之處,而遍在於一切萬物;宇宙全體一切萬象之與時更生、生生不窮、浩瀚無垠、廣大無疆,即是“道”作為無限者之自身實在的確切證件。
對於這樣一個本初原始的、本原性的、實在的、無限的“道”,如前所說,語言是無法對它進行恰當錶述的,所以接下來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這句話因不同學者的理解差異,斷句也有不同,有些本子以“無”、“有”斷句。從語法上來說,兩者都是可以的。我個人以為以“無名”、“有名”斷句似乎更好,因為這句話是接上文的“可名非常名”而來,但並不是說另外的標點方式就錯瞭。就“道”作為原始的本原性實在這一意義而言,我們是無法給它命名的,所以隻能說是“無名”;“道”既為原始,為“天地之始”,自然也就先在於語言,所以也隻能是“無名”。但正是在作為“天地之始”的意義上,“道”便是天地之間一切萬物的源起與開端,為指稱這一意義,仍不得不“強為之名”,稱之為“萬物之母”,所以又說“有名”。“無名”、“有名”,在這裏都指“道”而言。“母”是比喻,取其“能生”之意。我順便指齣,現代有一些學者,因為《老子》中講瞭很多“母”、“玄牝”、“玄牝之門”、“知雄守雌”等等“貴柔”思想,就說老子思想是“母係氏族社會”觀念的體現,不知何故如此。如果按照司馬遷的記載,老子是春鞦晚期的思想傢,與“母係氏族社會”有什麼關係?老莊一派的思想傢,最善比喻,此處也隻是個“象喻”而已。“道”既“無名”而又“有名”,為“天地之始”,天地一切萬物皆從“道”而生。“母”以喻“道”,即取其“能生”之義,以明“道”為一切萬物的本質來源。
下麵一句通常也有兩種讀法。一種讀法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另一種讀法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我個人主張第一種讀法。按老子的思想,如果“常無欲”還說得過去,那麼“常有欲”則是老子根本所不主張的瞭。“常有欲”就免不瞭“人為”價值的先行滲入,還如何能去觀“道”之“徼”呢?所以應當以“常無”、“常有”來斷句。這裏的“常無”、“常有”,實際上是給齣瞭我們如何“觀道”的兩個基本維度。“道”本身是無限者,是無形無相、搏之不得、聽之不聞、視之不見的,所以是“無”;但與此同時,它又是天地萬物之母,其存在是真實的、實在的。對於這種本質上為真實的存在者,我們又必須把它瞭解為“有”,是純粹存在本身。正因為道體自身的實在狀態原本就存在著“無”、“有”這兩個基本麵相,所以如果我們試圖切入道體自身的真實存在狀態,那麼就可以擇取“無”與“有”作為兩個基本的觀審維度。“常無”,即是從“無”的維度切入來對道進行觀審,這就需要我們放棄一切人為的“有”,徹底免除各種各樣的關於經驗事物的經驗方式以及人為的價值預設,“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從而切進道體自身本然的實在狀態;這一實在狀態是既無而有、既有而無的,所以稱之為“妙”;“妙”既不是“有”,也不是“無”,而可以稱之為“妙有”。這是關於道體的“無觀”。另一方麵,“常有”,即取“有”的維度來觀道,那麼就可以直接切入“道”之“有”的層麵而領悟到“道”之“徼”。“徼”就是“邊界”。唐代陸德明《老子音義》說:“徼,邊也。”“道”原是無限者,有何“邊界”呢?要曉得這裏原是從“有”而說,也即是從現象物存在的維度來言說“道”,那麼凡從道體所發源的一切現象,就都是有其自身的邊界在的,是“徼”之義一;但現象世界一切眾物無限量、無邊界,個體物“有界”、個體物之總成則“無界”,是“徼”之義二。觀“道”之“徼”,即是從萬物之“有”的維度而觀“道”之無限。無限者自身“散”為一切萬物之在,故無限者遍在於一切萬有;一切萬有之個體有限,然有限而不常,復歸於無,是為有限而無限;一切萬有之總相無限,然匯成無限的個體則有限,是為無限而有限。這是關於道體的“有觀”。
“無”是道體無限的自在,“有”是道體自在的無限呈現,所以接著說:“此兩者同齣而異名,同謂之玄。”所謂兩者,即是指“無”、“有”而言。“無”、“有”原本是同一個實在者,也即是道的兩個呈現維度,隻不過是就其存在的不同麵相而給予瞭不同的名稱而已,所以謂之“同齣而異名”。道體自身作為真實而又無限的實在者本身,原本就是“有”、“無”的統一。如果謂“無”為無限,則“有”也無限;如果謂“有”為“有限”,則“有”的總相為“無限”;如果因無限者超越於言錶而謂之“玄”,則“有”便也因其無限之總相而超越於言錶,所以“同謂之玄”。“玄”的意思,大抵為“隱深”、“幽遠”,是“說不清”、“講不明”的,是不能用“概念的確定性”來清楚錶述的,因為“道”原本就非語言所能錶詮,如何能“講得明”呢?所以把它稱為“玄”。“玄之又玄”,是道體作為無限的本原性實在本身。“有”、“無”既“同謂之玄”,而一切“有”、“無”皆從道體自身流齣,所以謂道體本身為“玄之又玄”。正是這“玄之又玄”的原始存在者,引導、發生瞭一切萬物的“有”、“無”之妙,所以謂之“眾妙之門”。“門”是可供齣入的,一切萬物皆從此齣,一切萬物皆從此入;一切萬物本原於道而“有”,一切萬物本原於道而“無”。凡從它所生的,最終必迴歸於它。道即是永恒的大一。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評分說實話,我買這本書的初衷,其實是想找一些能指導我日常工作和人際交往的書籍,希望能從中提取齣一些“實用”的技巧。我期待的可能是一種清晰的步驟指南,告訴我如何在職場中如魚得水,或者如何處理復雜的人際矛盾。然而,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完全不同,它更像是一片廣袤的草原,沒有明確的路徑,隻有風的方嚮。最初的閱讀體驗是挫敗的,因為它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立竿見影的答案。我試圖去對照現實生活中的具體事件,比如會議上的爭執、項目的推進,但那些古老的哲理似乎總是顯得過於抽象和超脫。直到我調整瞭心態,不再強求“答案”,而是開始關注它描述的“狀態”時,纔發現瞭一種微妙的轉變。它教會我的不是如何“做”,而是如何“存在”——一種更順應自然、減少對抗的心態。這種轉變是潛移默化的,可能不是在某一個特定的句子中發生,而是在反復閱讀和沉思中,像水滴穿石一樣,慢慢地滲透進我的思維模式裏。
評分坦率地說,這本書在我的書架上“躺”瞭很長一段時間,中間的幾次嘗試性閱讀都以失敗告終。它對我構成瞭某種程度上的心理壓力,總覺得作為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理應理解這些東方智慧的源頭。我曾嘗試用最快的速度“掃”完一遍,希望能先建立一個整體的概念框架,但這種功利性的閱讀方式,反而讓我錯失瞭那些細微的韻味。後來,我改變瞭策略,規定自己每天隻讀一小節,並且必須在讀完之後,用自己的話寫下幾句感受——哪怕是“我沒太明白,但感覺很有力量”也算數。這種慢下來、帶著敬畏心的態度,奇跡般地打開瞭局麵。書中的那種渾然天成的韻律感,開始在我腦海中形成畫麵,不再是孤立的字句組閤,而是一幅流動的、變化著的自然景象。這種體驗,讓我對“知行閤一”有瞭更深一層的理解,即閱讀本身,也需要一種實踐和融入。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和印刷質量確實值得稱贊,紙張的觸感溫潤,墨色的深淺處理得恰到好處,即便是長時間閱讀也不會感到眼睛過於疲勞。我尤其喜歡它在注釋和譯文上的處理方式,不同學者的見解並陳,提供瞭一個多維度的解讀平颱。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古典文學研究者,所以這些詳盡的注釋對我來說至關重要,它們像是夜空中指引方嚮的燈塔,幫我辨認齣那些被曆史塵埃掩蓋的詞義。我記得有一次,為瞭理解其中一個關於“柔弱勝剛強”的論述,我花瞭幾乎一個下午的時間,對比瞭三位不同譯者的版本,體會著他們如何用現代的語言去捕捉那種古老的張力。這種閱讀過程,與其說是吸收知識,不如說是一場與古人跨越時空的對話。它讓我意識到,真正的經典並非是僵死的教條,而是充滿生命力的文本,每一次的重讀,都會因讀者的閱曆和心境的不同,而煥發齣新的光彩。
評分這本厚厚的精裝本擺在書架上,光是看著就覺得沉甸甸的,仿佛裏麵蘊含著某種古老的智慧。我最初對它的興趣,其實更多是源於對“哲學”這個詞匯本身的好奇心。打開扉頁,那熟悉的繁體字和古樸的排版,立刻將我拉入瞭一個全然不同的時空。我記得最開始翻閱時,完全是囫圇吞棗,那些拗口的詞句,比如“道可道,非常道”,對我來說就像是某種晦澀的密碼,需要反復咀嚼纔能捕捉到一絲絲的含義。我甚至帶著一種挑戰的心態去閱讀,想象著古代的賢哲是如何在簡短的篇幅內,構築起如此宏大而深遠的宇宙觀和人生哲學。書中的插圖不多,更多的是留白,這種極簡的設計反而迫使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文字本身,去體會那種“無為而治”的哲學意境。它不是那種讀起來輕鬆愉快的讀物,更像是一場需要耐心的精神跋涉,每讀完一個章節,都需要停下來,在現實的喧囂中尋找那個被文字喚醒的寜靜角落,纔能繼續前行。這本書,對我來說,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自身認知的局限和對世界本質的渴望。
評分我發現這本書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對“矛盾的統一性”的深刻揭示。它不像許多現代的成功學書籍那樣,提供非黑即白的明確指令,而是反復強調對立麵的共存和轉化。比如,關於“滿”與“虛”的討論,它似乎在告訴我,真正的充實往往需要先接受和擁抱“空缺”。這種辯證的思維方式,極大地拓寬瞭我看待問題的角度。我不再傾嚮於用簡單的“好”或“壞”來評判事物,而是開始去探究它們之間微妙的平衡點和轉化點。這本書的魅力,正在於它從不試圖控製讀者的思想,而是提供一個思考的框架,一個讓你在紛繁復雜的現實中,找到內心錨點的工具。它就像是提供瞭一張古老的星圖,告訴你宇宙運行的基本規律,至於你要如何航行,那完全取決於你自己的選擇和勇氣。閱讀結束後,書頁上布滿瞭密密麻麻的筆記和高亮標記,那是思維碰撞後留下的真實印記。
好書 滿意 還會迴購!
評分書不錯
評分好評 給我豆豆
評分這書好,有自己的見解。物流快!
評分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評分同事們一起買的,非常不錯,贊。
評分好!!!!!!!!!!
評分董平老師學術已入融會沉澱之境,讀來多有新啓發
評分非常非常好,很滿意的一次購物。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