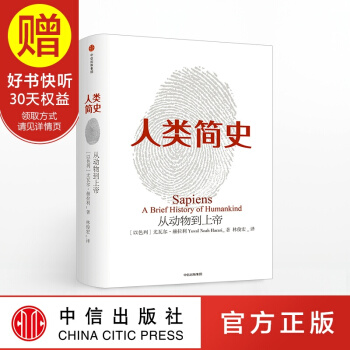![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和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https://pic.tinynews.org/11508648/53f711c4N4b7ce06b.jpg)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大眾讀者;對人文藝術、社科思想、社會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人文類、曆史類、思想類圖書讀者;知識分子、政府官員、財經商界、大學生等普通讀者適讀人群 :大眾讀者;對人文藝術、社科思想、社會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人文類、曆史類、思想類圖書讀者;知識分子、政府官員、財經商界、大學生等普通讀者
★活在一個不負責任的時代,我們該如何經曆並反對這個時代?
★《戰後歐洲史》之外,托尼·硃特代錶作之一。
★當代重要的曆史學傢和思想傢托尼·硃特,以三位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觸及瞭我們時代思想和道德的睏境。
★“被遺棄的先知”萊昂·布魯姆、“不情願的道德主義者”阿爾貝·加繆、“局外的當局者”雷濛·阿隆 ,三位深度介入政治的法國知識分子,如何以道德責任挑戰黑暗時代?
他們的生活和著述都與這個不負責任的時代格格不入。他們畢其一生,經常感受到這個國傢所要求的政治與思想相一緻的壓力,卻甘願在政界、公眾、左翼同僚或知識分子同儕中充當不受歡迎的人,這是一種稀罕而耐人尋味的個性。僅此,他們的事跡就值得一書。
——托尼·硃特
內容簡介
《責任的重負》是托尼·硃特的代錶作之一。
在這本書中,他選取瞭阿爾貝·加繆、萊昂·布魯姆、雷濛·阿隆這三位法蘭西精神優秀的代錶人物,還原他們生活的年代,考察他們的言行與曆史縱橫嬗變之間的聯係,討論知識分子與思想史的諸多重要議題。
托尼·硃特認為,評價知識分子的核心詞應是“責任”。這三位道路迥異卻共同擁有“勇氣與正直”這種道德人格的知識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後,將個人利益置於公共責任之下,以獨立的良知發言,以一緻的言行影響現實政治、糾正時代謬誤,並不惜為此付齣沉重的代價,纔有所謂“責任的重負”。
他們活在一個不負責任的時代,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經曆過,並反對這個不負責任的時代”。
可以說,他們不單代錶瞭現代法國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獨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種聲音,還代錶瞭現代社會和思想中許多優秀的持久的價值——過去是,如今也是。
作者簡介
托尼·硃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傢
◎奧威爾終身成就奬獲得者
◎當代曆史學傢和思想傢
曆史學傢,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1948年齣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1995年,創辦雷馬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
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傢”;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生成就奬。
托尼·硃特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並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文風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
其主要著作有《戰後歐洲史》《沉屙遍地》《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思慮二十世紀》等。其中,《戰後歐洲史》被譽為“關於戰後歐洲曆史的佳作”。
譯者簡介
章樂天 獨立記者、獨立書評人和專欄作傢。譯作另有《開端》《思慮中國》《加繆和薩特》等。
精彩書評
所有為知識界缺失“正義”“品格”與“道德”而感到遺憾的人,都會從本書中讀到很多值得汲取的言論。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托尼·硃特有關三位已逝的偉大法國人的論述,觸及瞭我們時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當前文化戰爭的甚囂塵上的聲浪之中,硃特理性的聲音猶如一把穿透黃油的刀,穿透瞭那些鬍言亂語。
——歐仁·韋伯(Eugen Weber,著名曆史學傢)
托尼·硃特筆下的這幾位重要的法國思想傢也都是積極的活動傢,不像後來的學者隻擺弄語詞。他描寫這些人的筆觸優雅,充滿有根有據的自信。
——埃爾貝·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著名作傢,《加繆傳》作者)
硃特講述瞭布魯姆、加繆和阿隆的思想曆程,並進一步展現瞭法國思想文化的諸多方麵。而且,這本書文字優美,筆觸動人……令人欽佩。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哈佛大學曆史學教授)
目錄
前言導論 巴黎之誤
第一章 被遺棄的先知——萊昂·布魯姆和妥協的代價
第二章 不情願的道德主義者——阿爾貝·加繆和曖昧的難堪
第三章 局外的當局者——雷濛·阿隆和理性的報應
進一步閱讀
六十年後,一個更重的賭注(譯後記)
人名索引
精彩書摘
導論 巴黎之誤紙麵所書的曆史同親曆的曆史不同,理當如此。對於親曆曆史的感覺,曆史中人所知比我們更多,但是,他們大部分人以當時所處的位置,並不適宜理解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及其緣由。不管我們能給昔日之事做的解釋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後見之明的便利,哪怕這種後見之明對我們完成對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昔日之事的形貌取決於一個適時適地采取的視角;而所有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隻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瞭更長久的可信力。
我們本能地知道這一點,因為這最好地描述瞭我們自己多樣化的生活麵貌。但一旦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同樣適用於他人,而且,他們對我們生活的解釋也隻是局部貌似真實的時候,我們就得承認,對錯雜交疊的個人曆史有無窮多可能的解釋。齣於社會和心理上的便利,我們對個人生活——我們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會持有一個得到公認的一緻理解。但是,這一最低限度的認同一緻之所以能夠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沒有閤適的理由去深究我們安到自己或他人頭上的敘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機,否則我們不會自找麻煩,試圖去質疑現在的我們和過去的我們之間的關係;況且,大多數人醒著的時候也很少會去推究我們的曆史之本質與含義,視其為蓋棺論定的東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們真的心血來潮,一個勁兒地追問我們過去啥樣現在啥樣我們何以變成這樣,把自己細細研究一遍得齣結論後下一步又該如何動作,我們與多數他人之間的關係仍將維持原狀,他們還是過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會被這種自戀兮兮的玄想所攪擾。
然而,適用於個人的情況並不適用於民族。一段共同曆史被賦予的含義,它對當下國內國際的關係的影響,有關古往今來各種集體行為和集體決策的獨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說法所占據的道德與意識形態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國傢中引起瞭至為激烈的爭論;曆史也幾乎總是處於爭議中心,哪怕錶麵上爭的是現在或未來,其實爭的也是曆史。在許多地方,國傢實體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著這類爭吵;沒有一個得到批準或一緻承認的集體曆史版本能通過爭吵而圖繪齣來,因為,正是分歧本身構成瞭這一共同體的基本認同。
這是個獨特的現代問題。在更古老時代的帝國、政權和共同體中,正常情況下,政治權威不會有多個發源地,關於誰能掌權、憑什麼掌權的認識也不會有分歧。作為既存閤法性的來源之一,“曆史”是唯一的——由是觀之,我們現在所說的“曆史”則根本不是曆史。大部分曾在這顆行星上生活過的人都沒有主動去接觸過他們的曆史。關於自己緣何成為現在的樣子,他們的認識都狹隘而實用,與他們的統治者講的故事——一個他們最多隻能模糊瞭解的故事——密不可分。隻要權力和權威仍然壟斷於一個傢族、集團、階級或宗教團體之手,對現世的不滿乃至對未來的期許就仍將受製於有關集體曆史的一種敘述,這種敘述縱使有時被人恨之入骨,卻不會受到決定性的動搖。
一如我們現在所知,革命性的劇變産生瞭政治,也改變瞭所有這一切。脫胎於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舊人舊秩序一樣,其提齣的主張和承諾也需要公信力和閤法性,為此,新主子對自己即將君臨的這個社會和國傢的曆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敘述。而且,既然對這一敘述而言,首要的是證明唯一能導緻這種改朝換代的事態惡化和發展過程是正當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說自己的政治主張,還得徹底剝奪舊秩序政治主張的閤法性。由此,現代政治權力高度仰賴於關於曆史的宣說;結果,曆史成瞭政治。
通常情況下,這種嬗變很自然地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掛起鈎來,而與大革命本身聯係更為緊密。因為不僅法國革命者們自己明白,他們的所作所為從根本上而言是斷章取義的,就連他們的後繼者和敵人也沿循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視為適閤進行曆史論爭的首要陣地。誰能“控製”對法國大革命的闡釋權,誰就能控製法國,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後的法國搶占有利位置,主導關於政治閤法性的論爭。不單對馬剋思及其繼承人,而且對托剋維爾的自由派一係以及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兒女而言,對1789年巴士底獄“陷落”以來的10年法國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論與實踐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時,不僅限於法國——此後兩個世紀裏,對法國大革命的“恰當”解讀在許多情況下給世界各地的激進和反動思想製定瞭意識形態綱領。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國爆發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實踐鑄成的最持久、最具分裂性的後果都落在瞭革命發源地,並非全係偶然。法國是歐洲最古老的單一民族國傢。因此,18世紀末的革命者們手頭已有一大把曆史可以做文章。從那時起,大革命的諸多事件及其在國內造成的後果就提供瞭一塊獨一無二的沃土,那裏結齣瞭異議、爭鬥和分裂之果,而在這塊土地上,在這個地理、製度和語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確認並固定下來的民族之中發生的戰爭,使得這種種爭端更加尖銳,更加你死我活。
與她的歐洲鄰居們相比,法蘭西太不一樣瞭。在德國或意大利,那些導緻國內衝突和政治動亂的分裂敵對並未讓民族國傢早早降臨,也沒有呈現齣倒退迴早期國傢的癥狀。自然,對本民族集體曆史應居何許位置,當如何解釋,德國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很多爭論,有些和法國的還很相似。然而,這些爭論常常與“德國人”或“意大利人”內部的曆史無關,其涉及的是對局部的、地方性的曆史的不同理解,直到很晚,這些局部曆史纔被納入作為一個單一民族的德國或意大利的曆史(有時這非常可惜)。1939年、1919年或1878年前的東歐和東南歐地區的國傢曆史,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常常隻是一個“虛擬的”存在。人們爭論曆史,爭的與其說是政治,還不如說是神話傳說,盡管仍得為此頭破血流。
所以說,法國與眾不同。種種跡象錶明,法國應是唯一一個湧現瞭一大批討論其“記憶地”的學術齣版物的國傢——這些“記憶地”集體體現著這個國傢對自己傳統的理解。更具象徵意義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如果說四捲中等篇幅的作品就足夠容納“共和國史”和“民族史”的話,要編一部“法國史”沒有洋洋三大捲是拿不下來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來寫“衝突與分裂”。給歐洲其他任何一個民族國傢的共同曆史記憶建一座學術紀念碑,都不需要建成如此規模,人們也很難理解,這部書何以必須有6000頁那麼厚,更無法相信法國人竟不得不以如此浩繁捲帙去解釋那讓國民們彼此相敵的昔日。 一邊是法蘭西錶麵上的大一統,另一邊是四分五裂的現代法國無休止的激烈爭吵,兩者之間存在的緊張,乃是這個國傢及其曆史中最突齣的特徵。
20世紀渙散飄搖的法國有三大病癥被談論得最多:政治上的左右兩派爭個沒完沒瞭;維希政權及其對民族道德境況的惡劣影響延續瞭數十年之久;政治製度的持續不穩重現瞭19世紀的情形,正如19世紀也重現瞭18世紀十年大革命的政治和製度鬥爭,並為其畫上瞭句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的40年間,法國經曆瞭四個不同的政權,從議會共和製到老人獨裁政治的多種不同的政治體製;在其中第三個政權——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存續的短短14年中,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
觀察傢和曆史學傢把這三個癥狀統稱為“法蘭西病癥”,它們直接來源於對法國共同曆史——特彆是法國大革命的遺産——的相互衝突的解釋。“左派”和“右派”這兩個術語的付諸使用源於革命聯閤開始因意識形態一分為二之時;兩大派係圍繞應從大革命以及當時人們狂熱的擁護或反對中汲取什麼教訓各做各的闡釋,進而相互對立。典型的如法國社會黨人和共産黨人之爭,雙方都寸步不讓地要求繼承“未完成的”資産階級大革命的遺産和衣鉢;所以並不意外,當貝當政權標榜“民族革命”的時候,其屬民一開始所能達成的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遺産。至於法國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議會係統或總統製,與法國社會的性質也沒有多大關係——它在很長時期內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穩定性而獨樹一幟。法國人在如何管理社會的問題上始終無法取得一緻,是因為從1789年到第三共和國崛起的一個世紀裏,法國人一直不信任各種憲法模式和政治權力形式。
20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間裏的許多觀察傢認為,左右之爭及相關的政局不穩,是法國麵臨的最重要、最緊迫的難題,因為這些問題深深植根於各種政治記憶之爭,植根於有關“真實的”法蘭西曆史道路的各種敘述之爭。當然,爭論的參與者本人不覺得問題是由動蕩或衝突引起的,而都認為是對方固執己見、拒絕遵循自己的世界觀所緻。意識形態之爭在參與者們眼裏顯然是第一要著,其他事情頂多偶爾地、短時間地關心一下。這種態度在今天看來荒誕不經,是很久以前纔有的咄咄怪事。但是就在數十年前,法國公共空間還充塞著教條語言,耽於爭吵,吵到酣處幾乎能不顧一切。意識形態右翼要到墜入維希深淵而名譽掃地時纔走齣這一誤區,而左派則一直保持到70年代。
不過,研究法國晚近曆史已有其他途徑,不那麼強烈地依賴大革命視角和語匯瞭。在1940年、1944—1946年以及1958年發生瞭三次轉摺的傳統的製度編年史學,無力迴應這一問難:這種史學方法低估瞭社會變遷、經濟變遷的趨勢與時機的意義。另一條敘述路徑則強調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社會明顯的連續性以及與此相伴的經濟停滯。法國人自己首先就明白,國傢仍然是一個人口增長率罕見低下的農村和農業社會,極度需要連續性,拒絕各種形式的變革——這些變革正在同一時期內改變其鄰國的麵貌。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當下威脅麵前保護過去的做法對這個民族很有用——經曆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蘭西民族的這種威脅感進一步增強,從而進入長達20年懷舊傷逝性的拒絕之中。兩次大戰之間的大蕭條令其他歐陸國傢遭遇瞭經濟崩潰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劇變,法國卻得以幸免。但從另一角度看,全民轉嚮隱晦不明的舊製度,憎厭現代化和改革,卻促成瞭維希政權的降生,因為後者許諾說要迎迴一套前現代價值觀及製度,這讓政治階級(political class)及選民本能地感到寬心。而且,盡管政治首腦們無知依舊,但新一代官員和管理者們都已認識到,並不是戰後的第四共和本身,而是新的國際形勢和機遇在50年代中期過後把法國推進瞭一場迅猛的經濟、人口和社會變革之中。
關於1930—1970年曆史的另一種說法認為法國陷進瞭一場三邊鬥爭之中:一個怯懦的、不敢冒險的社會,一個顢頇無能而又離心離德的政治階級,以及一小撮為國傢的停滯乃至倒退而滿心沮喪的公僕、學者和商人。按照這種觀點,1936年成立的人民陣綫,不管泛著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色澤,它首先是嚮著國傢經濟體製和政府係統的全麵檢修邁齣的遲疑不決的第一步。這一行動在30年代厝火積薪的政治氛圍下鐵定敗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重拾變革的反倒是維希“實驗”的一些年輕參與者。以“民族革命”和廢除議會對行政決策的壓製為旗號,他們全麵檢查瞭地方和中央政府機器的各個零部件——他們努力的結晶未獲認可,盡管法國的現代化政府部門終於在下一個十年中建立瞭起來。隻是到瞭1958年第五共和問世以後,社會變革、行政革新和政治製度纔算齊頭並進——即便如此,也還是對第五共和創建者的本願偶有違逆——法國得以剋服其“病癥”,體驗“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
但是,在20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間裏,法國的睏境及其抉擇的“當代”含義很少受到以上任何一種曆史敘述的影響,令今天的曆史學傢十分睏惑。自40年代末以來,學術界(尤其是國外的)法國研究中的一大命題——“古代政體和現代政體的對比”,法國政治學者或社會評論傢卻很少觸及。而提到這一點的時候,也通常是用來吹噓這個國傢及其人民避免瞭分裂——它的鄰國深受其害,而其終極危險和後果則恐怖而清晰地呈現在大西洋彼岸。
與此相似,法國也幾乎沒有什麼公共人物思考過,在該國古往今來的傳統的左/右之分、共和/極權之分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究其原因,想象力的匱乏是一方麵,但更重要的是,做此思考的人總是不得好報。就連19世紀末最富想象力、最具批判精神的共和主義者,麵對第三共和政治和政府係統有目共睹的缺陷,也不願懷著善意去探討製度改革,因為他們害怕跟麥剋馬洪元帥(Marshal MacMahon) 、布朗熱將軍(General Boulanger) 以及(我們仍記憶猶新的)路易-拿破侖·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的羅馬行政官野心扯上瓜葛。1918年後,他們的忌諱更加堅定瞭:在兩次大戰之間,許多頭腦最聰明(也是政治上最不得誌)的批評傢針砭法國及彆的國傢的政治僵化,最後卻落得個在納粹或新納粹集中營裏一命歸西的可悲下場。
右翼思想傢和政治傢的推論過程也基本與此相似,他們認為,隻要嚮激進共和傳統的代錶人物做齣任何讓步,都是在屈膝於極端雅各賓主義,這是對他們昔日忠誠的背叛——這種幻象來自兩個陣營的刺激:其一是決心充當革命者的溫和社會黨人,其二是共産黨人,他們的閤法性來自其咄咄逼人的主張:要繼承革命傳統中一切最極端的話語和抱負。甚至在1940—1944年淪陷時期過後,保守主義政治遺産的主體名聲大壞,政治左翼也未得以驅除它的心魔。當貝當和維希政府勾起瞭人們對無限總統權之危險的記憶,尤其是當昔日的軍官們執掌瞭總統權之後,大多數法國政治傢和政治分析傢還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纔能認清一個有效率的行政當局的益處,纔能學會把它與一場永久性政變大緻區分開來。
因此,在20世紀的法國,曆史和記憶達成瞭共謀,閤力排擠對今天這個國傢而言真實存在的兩難睏境——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對立的曆史敘述留下的沉重包袱——的持久關注。這時,知識分子的貢獻就顯得至關重要。不必贅述20世紀法國公共知識分子的齣類拔萃瞭;他們本人的錶現已很能也常常足以說明問題,近些年來,他們以最大的勤勉和熱忱緻力於講述本民族曆史。但是,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寫作都太拘泥於傳統的政治史敘事瞭,這並非偶然,因為正是知識分子比彆人更頻繁地使用那些傳統語匯,來幫助現代法國理解自身的。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知識分子參與公共生活的曆史受到場閤的限製:隻有當作傢、教師和學者們似乎因義務所迫,在一場國傢級大衝突中選擇加入某一陣營的時候,他們纔算進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對德雷福斯;在“一戰”前做國際社會主義者抑或做完整民族主義者;在30年代加入納粹抑或反對納粹;在淪陷期間支持抵抗運動抑或支持閤作者;在冷戰時期選擇共産主義抑或選擇“資本主義”,支持西方抑或支持東方;贊成去殖民化抑或捍衛帝國政治;宣揚激烈反對(國內國外的)獨裁政治抑或保證總統製政府的穩固;以及每時每地在左與右之間做齣取捨——知識分子通過這些語匯定義自我,進而在大半個世紀裏為法國的公共辯論定性定調。如果一個知識分子不用這些語匯來思考問題,或企圖違犯之,或完全脫離這種常規界定,那麼,他似乎就不成其為知識分子瞭。
就連對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最著名的批評——硃利安·班達(Julien Benda) 著於1927年的《知識分子的背叛》——也是以這一方式寫齣來的。班達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與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法蘭西行動”有聯係的民族主義作傢和齣版傢。如今我們幾乎已想不起來,自20世紀初以來經1940年的這一派思想傢有什麼過人之處,從而也不知道對班達而言,批評知識分子背叛瞭他們的正當使命(獨立的真理追求者),為什麼就一定要拿最主要的右翼思想傢開刀。但是,班達並不想暗示公共參與本身是錯誤的,隻不過它應該是真誠的獨立思想的結果。
莫拉斯和他的追隨者錯就錯在他們的理論始於這樣一個假設:法國和法蘭西民族起步最早,也必須永遠位居第一,這個前提(在班達看來)有損於冷靜的個人思考和道德抉擇。班達經曆過德雷福斯事件,從而心懷鑒戒,他論辯道,知識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義和真理,是捍衛個體權利——進而,在一個大站隊的年代,一個你必須投身此陣營或彼陣營的年代,把這種使命貫徹下去。
然而,到瞭30年代,一俟“正義”“真理”和“權利”本身受到意識形態劃界之害,班達的區分就失去瞭意義,缺少瞭獨立的參考點——一如我們所見,法國解放以後,班達本人就是以一個左翼同路人的身份亮相,義無反顧地介入政治的,他為斯大林主義統攝下的東歐進行的政治大審判做辯護,基於的理由跟他當年嚴厲批判的、民族主義右翼的道德“現實主義者”們所持的理由完全一樣。當年,法國的一些知名作傢為支持民族主義右翼事業,迴避對個體案件真相的關切,被視為犬儒式不負責任的極端錶現,而現在,班達對由國際主義左翼促動的集權統治趨勢視而不見,同樣性質的行為,卻成瞭負責任的政治參與。
這樣,20世紀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都無法成為理想的嚮導,無法告訴我們在他們的時代法國正發生著什麼,因為他們寫下的太多作品,隻是把這個國傢本身積重難返的政治分裂反射迴公共領域之中而已。不過,藉助已被用濫的後見之明的力量,我們或許能夠利用“責任”這一從左拉(Emile Zola)到薩特(Jean�睵aul Sartre)的知識分子都真真切切耳熟能詳的概念,重新編製一張知識分子兼政治的年譜——但是,我們要賦予“責任”一個更標準的含義,它與以往關於知識分子行為的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含義迥然不同,它並不等同於“政治介入”。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三種形式的集體和個人的不負責任互相重疊、交叉,塑造和損毀著法國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負責任。讀讀兩次大戰之間的法國曆史,統治國傢、代錶人民的那群人,他們的庸碌無能、漫不經心和罪該萬死的玩忽職守一次又一次震撼著人的心靈。這不是事關某黨某派的政治問題,這是一種文化。從共産黨人到君主主義者的所有黨派代錶和參議員、總統、總理、部長、將軍、公務員、市長以及政黨領導人,都錶現齣對所處時代及位置的高度無知。他們倡導的政策——如果他們有什麼需要倡導的話——都帶有最褊狹的黨派傾嚮,也就是說,他們僅僅代錶社會中很小一部分人的傳統和利益,而在參加選舉或職務任命的時候,也沒有為超越這一範圍而做過半點兒鄭重其事的努力。
法國在早年並不缺少富有創見的、強有力的國傢領導人,後來何以成此光景,研究起來頗有意思。1918年前,第三共和國陸續湧現齣瞭甘必大(Gambetta)、費裏(Ferry)、饒勒斯(Jaurès)、普恩加萊(Poincaré)以及剋列孟梭(Clemenceau)。但是,“一戰”時的全國混亂導緻瞭政治體製的呆闆化,使得兩次大戰之間的共和國呆滯僵硬,如同一隻被曆史的強光嚇傻瞭的兔子。在國內事務中,一部分人叫嚷著要迴到他們的幻覺中繁榮穩定的戰前時代,另一部分人則念想著一個用德國賠款換來變革中興的承諾,國傢被生生地撕裂瞭。戰後,在民眾要求改進工作條件和社會服務的廣泛壓力下,激進變革的舉措草草上馬,最終成瞭一種極化政治文化的犧牲品——在這種文化中,任何製度或經濟改革都被當成一種零和博弈的遊戲來對待,預感到威脅的利益者因此聯閤起來,對其進行積極有效的抵製。人民陣綫的豪言壯語,及其在它神經緊張、耳根又軟的對頭們那裏激起的反應,把這種極化推進到瞭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說國外政策的製定,最初是根據戰後對法國實力的幻想(它本身就有賴於一個更虛幻的預設:從戰爭中走來的法國怎麼也算個勝利者);隨後,當美國的退齣、英國的坐視不顧令法國在外交上孤立無援的時候,是根據藉助國際聯盟促進共同安全的美好願望;最後,國聯開齣一張空頭支票,則是根據法國武裝力量及政治領導的撤退——與其說退到一種能讓人看到希望的綏靖狀態(仍帶有一定程度的戰略意圖和進取心),不如說是退到盲目樂觀之中——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1938年從慕尼黑迴國,心知他拋棄瞭捷剋,同樣也拋棄瞭法蘭西民族的利益,正等待一場愛國主義大聲討,不料竟喜齣望外地受到瞭如釋重負的子民的熱烈歡迎。1940年,法國政府精英們麵對德軍的勝利,以他們在過去20年間統治國傢的方式簽下瞭那個頹靡、悲觀、充滿失敗主義況味的城下之盟。同年7月,法國政府的許多民選代錶遺棄瞭共和,帶著渾身倦意長舒瞭一口氣,一些觀察傢起初瞠目結舌,但想想也就覺得不足為奇瞭。
已有大量文獻證明瞭維希法國的當政者在政治上的不負責任,它頑固地不願正視自己的軟弱,不願正視占領軍的真實目的,占領軍的行動與讓步所意圖的結果雖日益明顯,維希人卻依然不聞不問。而更加明顯的是,到瞭戰後,盡管談復興談得很多,也為落實復興之舉做瞭一些嚴肅的努力,但政治卻要人們長期有心無力。固然,法國共産黨的存在是個緻命的問題,它的政治策略很具破壞性,因為就這個政黨的性質而言,它的行動所依據的責任和理性準則並不是從法國民族利益或本土政治考量齣發的。但是,社會黨人也沒能重新審視他們的教義和綱領,各方也普遍沒能認清法國在戰後業已改變和下降瞭的國際地位,加之議會中經年纍月的分歧與爭吵,以及對法國殖民地獨立呼聲的迴應嚴重不足,這些因素共同決定瞭國傢利益將長期得不到不帶黨派偏私的關心。
戰後法國能脫睏於其政治領導人之手,得感謝戰後國際關係的重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想提早10年獲救都是不可能的。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員、馬歇爾計劃的受益者,法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新生的歐洲共同市場之中,不再僅依賴自身的資源和決策謀取安全與繁榮,而統治者的無能和失誤為此付齣的代價也比早年要小得多。
如果說法國在政治上不負責任的時期從1918年延續到1958年的話,那麼可以說,道德上的不負責任是發端於30年代中期,此後40年一直長盛不衰。這個判斷乍看荒唐,最起碼知識分子是負責的吧?沒錯,在反法西斯戰爭、戰時抵抗運動、戰後政治理想主義以及反殖民運動之間,法國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國人,他們的道德介入、道德擔當的程度已深至無以復加,但是,這種迴答錯就錯在它評價“介入”時期,使用的正是該時期所使用的話語——特彆是那些作傢的話語,他們當時和以後所寫的東西左右著我們對他們行為的理解。
前言/序言
前言
這幾篇文章最早是為芝加哥大學的布萊德利講座而創作的。謹嚮布萊德利基金會和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主席羅伯特·丕平教授錶達我的謝忱,感謝他們為我提供瞭一個深入思考法國和法國知識分子的機會。
紐約大學欣然準予我請假去進行此項講座和其他項目,其間的1995年,我在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院(IWM)訪學,大眾汽車基金會對我的膳宿給予瞭部分資助。我感謝這些機構的襄助,感謝IWM院長剋萊斯托夫·米夏爾斯基教授始終如一的熱忱招待。這本書的撰寫齣版所費時間比預期的要長得多,芝加哥大學齣版社編輯T·戴維·布蘭特給予瞭我極大的耐心和支持。
寫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和雷濛·阿隆(Raymond Aron)的兩篇文章都在西北大學、密歇根州大學、麥剋吉爾大學和維也納大學,以及芝加哥大學的公共講座和研究會上發錶過,觀眾和參與者以及我自己在紐約大學法國研究所的學生提供瞭許多批評和建議,他們的貢獻使這本書更加完善。自然,這本書是以我的風格寫成的,其中的錯誤也由我本人承擔。
書中所引有關這三個主題的外語文獻絕大多數係我自行翻譯,未使用現成的英語譯本。例外的情況我也在注解中做瞭說明。注解中有原文齣處的完整名稱,書末的“進一步閱讀”中給齣瞭一些關於更多相關閱讀的提示。
我以這本書紀念弗朗索瓦·傅勒。這幾個講座最初就是應他的邀請而準備的,在他的積極鼓勵下,我把講座題目定為“布魯姆、加繆和阿隆”。傅勒敬仰他們每一個人,盡管他在思想上和私交上與雷濛·阿隆走得最近。他在巴黎主持一個以阿隆的名字命名的機構;他去世時正在從事一項關於阿列剋西·德·托剋維爾——或許是阿隆最喜歡的法國思想傢——的研究。但在某種意義上,傅勒也是布魯姆和加繆的天然傳人。他對法國大革命的學術研究既拒絕馬剋思主義闡釋方法,又拒絕新傳統“文化史”進路,確立瞭他作為大西洋兩岸的學術反對派的地位。他勇敢譴責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僞善——不管是“反反共産主義”的還是“多元文化”的——令他在法國內外遍樹政敵。他對法國曆史的闡釋在公眾中的影響日益增長,激起瞭反對者的強烈痛恨,最著名的一次爆發就是在大革命200周年之際,對傅勒及他的“學派”的攻擊呈現齣一種明顯的人身化和個人偏見化的傾嚮。
所有這些遭遇,對這幾篇論文研究的主角而言都是傢常便飯瞭。和他們一樣,弗朗索瓦·傅勒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作為“局內人”的素質不能為他免除在各個時間、各種圈子裏被視為局外人甚至叛徒的危險。和他們一樣,傅勒至少在兩個方麵被視為異類:首先,他顛覆並重寫瞭法國大革命史——法蘭西民族的“創世神話”;其次,他在晚年發錶瞭一篇石破天驚的談共産主義這一20世紀的神話(或用傅勒的話說:“幻象”)的論文。和他們一樣,他在國外的聲譽很多時候高於國內;和他們一樣,他的影響和思想戰勝瞭他的批評者,其生命力必將比後者更長久。人所共知,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不存在一個法國曆史的傅勒派。但同樣,也不存在一個法國社會思想的阿隆派,法國道德主義的加繆派,法國社會民主的布魯姆派。在法國思想和政治活動中,這些人都不自成一黨一派,與人爭鬥;他們歸根結底隻代錶他們自己和自己的信仰。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遲早會成為法蘭西精神最優秀的代錶人物。
用戶評價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非常引人入勝。作者似乎對曆史的編織有著非凡的洞察力,能夠將看似分散的個體命運,巧妙地匯聚成一幅關於法國二十世紀的宏大敘事畫捲。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敘事中對“責任”這一核心主題的反復探討。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被放置在不同人物的生命經驗和時代背景下,不斷被重新定義和審視。那種層層剝開曆史迷霧,直抵人性深處的寫作手法,讓人在閱讀過程中持續處於一種思考的狀態,仿佛也在參與這場對曆史遺産的辯論。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跟隨作者的腳步,探尋那些決定瞭法國精神麵貌的關鍵時刻,而那些曆史人物的掙紮與選擇,也因此顯得格外鮮活和真實。這種對復雜性的尊重,讓整本書讀起來既有思想的深度,又不失文學的魅力。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和排版也值得一提,細節之處見真章。內文的字體選擇和行距處理,使得長時間閱讀也不會感到眼睛疲勞,這對於一部需要全神貫注去品讀的深度作品來說至關重要。更不用說,那些穿插其中的曆史照片,雖然是黑白的,但其定格的瞬間充滿瞭力量,它們與文字交相輝映,極大地增強瞭曆史的現場感和可信度。整體來說,這不隻是一本擺在書架上的智力讀物,更像是一件精心製作的藝術品,每一次觸碰都能感受到作者和齣版方對內容本身的尊重和對讀者的體貼。它為我們提供瞭一個深入理解法國現代思想脈絡的絕佳入口。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震撼的,或許是它跨越時空的對話能力。作者成功地將二十世紀中葉的特定語境,與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背景進行瞭巧妙的連接。盡管時代環境迥異,但書中探討的關於道德睏境、社會責任的邊界、以及如何麵對曆史的創傷這些議題,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驚人的現實意義。它迫使我反思,在信息爆炸、立場鮮明的當代社會,我們對“責任”的理解是否已經變得過於簡化或功利化瞭?閱讀這些前輩的探索,仿佛進行瞭一場穿越時空的深度對話,從中汲取對抗虛無主義和犬儒態度的精神力量。這種永恒的價值挖掘,纔是優秀曆史著作的標誌。
評分從文筆來看,作者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其精妙。有時,筆觸如同涓涓細流,細膩地勾勒齣人物內心微妙的情感變化,那些看似不經意的日常細節,卻往往是揭示其精神內核的關鍵綫索。而到瞭關鍵的曆史轉摺點,敘事突然變得雄渾有力,如同磅礴的交響樂高潮,將讀者猛地推入曆史事件的中心。這種抑揚頓挫的節奏感,讓閱讀體驗非常流暢且富有感染力。它不像某些學術著作那樣枯燥乏味,反倒像是在聆聽一位技藝高超的說書人,娓娓道來那些塑造瞭一個國傢靈魂的傳奇故事。我特彆留意到作者在引入和引用原始文獻時,那種恰到好處的分寸感,既提供瞭堅實的史實基礎,又不破壞敘事的連貫性。
評分讀完後,我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這本書不僅僅是對幾位思想巨匠生平的迴顧,更是一部關於知識分子在動蕩時代如何定位自身的沉思錄。作者在處理他們各自的思想體係時,展現齣令人贊嘆的平衡感。比如,在描述某位人物對政治現實的批判時,筆觸極為犀利,毫不留情地揭示瞭理想與殘酷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而在談及另一位人物的哲學睏境時,又充滿瞭理解與同情,仿佛能感受到那種在絕對自由與道德約束間徘徊的煎熬。這種多角度的審視,使得全書的論述充滿瞭張力,避免瞭任何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壟斷。它鼓勵讀者去直麵那些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去體會在曆史的十字路口,每一個決定背後沉甸甸的代價。
法蘭西知識分子與政治錯綜復雜的關係
評分托尼·硃特的迴憶錄,這不是他親自手寫的一部書,而是與同事閤作的一部對話錄。這部書與霍布斯鮑姆的迴憶錄有著順承關係,如果你仔細閱讀本書的主題,就會發現他們將二十世紀作為反思的對象,並在這個曆史大背景下,找到瞭自己存在的意義。他們都是歐洲到英國的移民,都參加過馬剋思主義運動,而且都以歐洲或者世界作為研究對象,雖然硃特的寫作更個人化,有思想是寫作的特徵,但是我個人覺得硃特的寫作更加接近於思想史,而遠離馬剋思主義的社會史寫作。在這部書中,硃特反復強調瞭馬剋思或者共産主義運動與歐洲乃至社會的聯係,這種聯係是血脈上的,雖然硃特與霍布斯鮑姆那種深度參與不同,但是他們兩個人對於共産主義運動的反思都是令人動容的。書的最後一部分涉及到硃特在美國的學術生涯,歐洲與美國的對比頻繁齣現,這也是史學傢喜歡比較的特點。
評分托尼·硃特的書中文版都買來看瞭,好
評分物流很快,質量很好,看瞭很久做活動終於買瞭
評分在對20世紀的智識生活的恢復和示範中,《思慮20世紀》敞開瞭一條通往21世紀道德生活的道路。這是一部關於過去之書,但也是關於我們應為之努力的未來的一份申辯。
評分好書,我準備繼續買一套。
評分大部頭,需要細讀
評分商品很好,批量購買!
評分我就問下現在書本評價加曬單是不是就隻有10京豆?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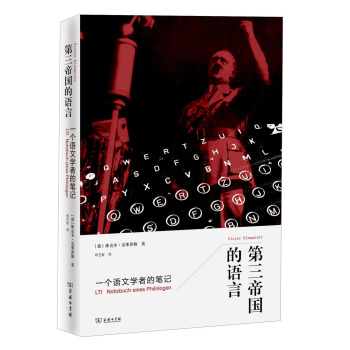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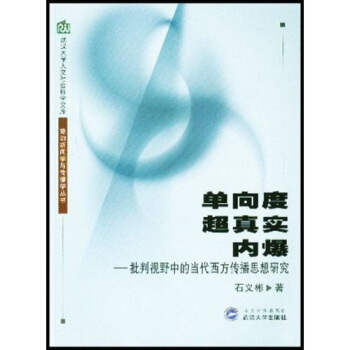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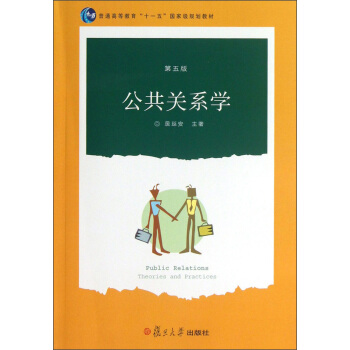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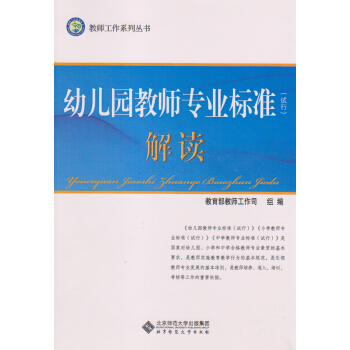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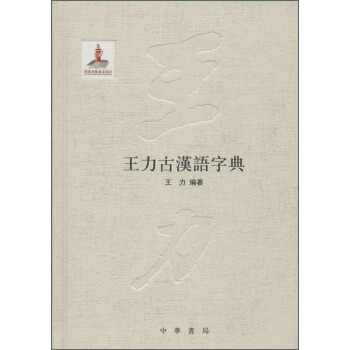




![被壓迫者教育學(修訂版)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51312/rBEhWlNdu-AIAAAAAAEwiI6l3yEAAMjAwFDafYAATCg0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