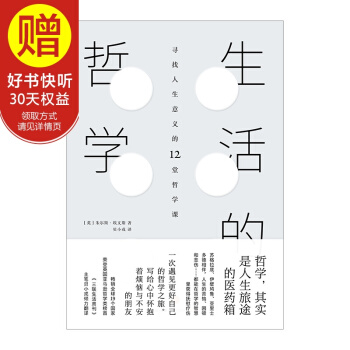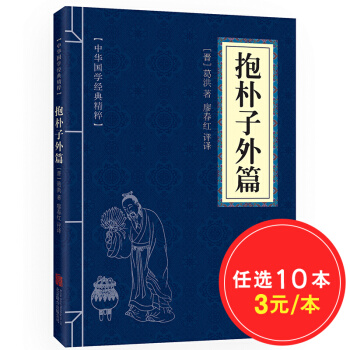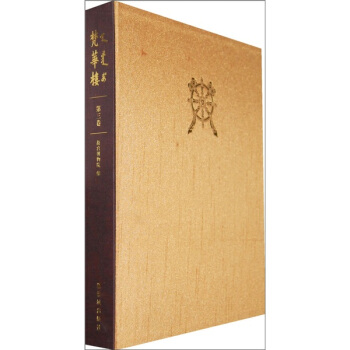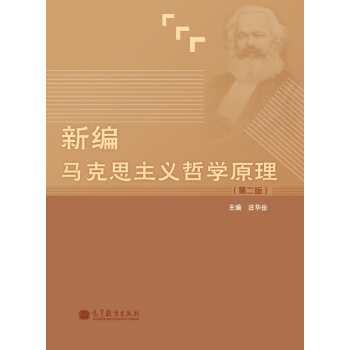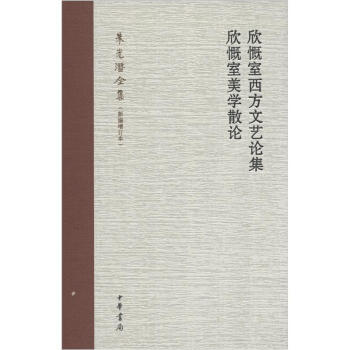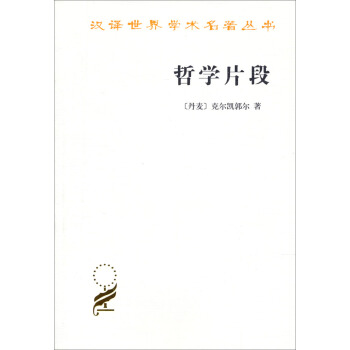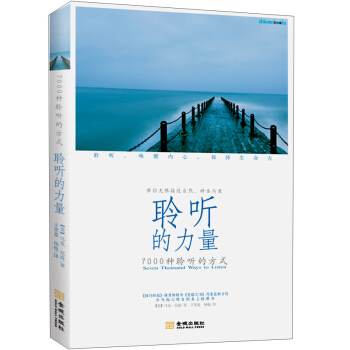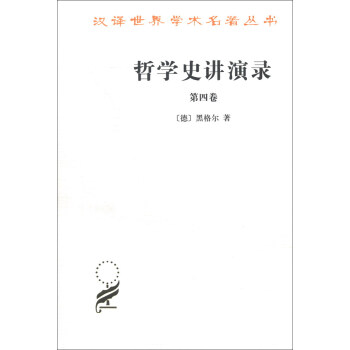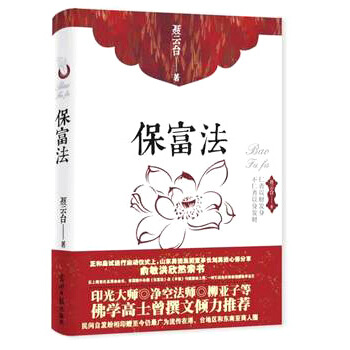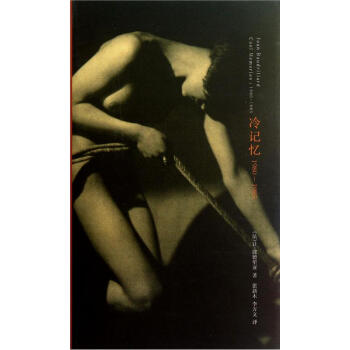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穿衣的女人:必须观看,但禁止抚摸。不穿衣的女人:必须抚摸,假禁止观看。不过,这些也许正在改变。《棱镜精装人文译丛:冷记忆(1980-1985)》则是关于女性、福柯、白血病、天主教、柏林墙、洛朗·法比尤斯、让-保罗二世、玫瑰、南极洲、莱赫·瓦文萨、泥地摔跤、季诺维也夫、色情电影、雪、女权主义、雅克·拉康、史蒂夫·旺德、迈克尔·杰克逊、DNA和恐怖主义。内容简介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冷记忆(1980-1985)》则是关于女性、福柯、白血病、天主教、柏林墙、洛朗·法比尤斯、让-保 罗二世、玫瑰、南极洲、莱赫·瓦文萨、泥地摔跤、季诺维也夫、色情电 影、雪、女权主义、雅克·拉康、史蒂夫·旺德、迈克尔·杰克逊、DNA和 恐怖主义。《棱镜精装人文译丛:冷记忆(1980-1985)》具有一种忧郁的气质,而忧郁正是 事物的特定状态。作者简介
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其代表作主要有《消费社会》、《物体系》、《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冷记忆》、《美国》、《完美的罪行》等。《论诱惑》是其中晚期的思想代表作。目录
1980年10月1981年10月
1982年lO月
1983年10月
1984年10月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一直觉得,对于一个特定年代的记录,最难捕捉的不是那些光芒万丈的成就,而是弥漫在空气中、难以名状的“气氛”。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成功地捕捉到了1980年至1985年间,那种介于希望与幻灭之间的暧昧地带。它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用大量未经修饰的访谈片段和个人手记,构建了一个多声部、甚至相互矛盾的叙事场域。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立体感和现场感。读到某个知识分子描述他们对未来抱持的近乎狂热的乐观,紧接着又看到普通民众在日常困境中的挣扎与犬儒主义,你瞬间就被拉入了那个充满张力的时间切片中。它没有提供一个整齐划一的“答案”,反而将难题抛还给读者,迫使我们去反思:我们今天所依赖的“记忆”,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如此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对记忆“不确定性”的坦诚,是其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评分这本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社会记忆的译作,简直是一扇通往那个特定时期的时光之门。作者以一种近乎病理学的细致,剖析了那些被集体无意识刻意遗忘或重构的片段。我特别欣赏它跳出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窠臼,没有陷入宏大叙事的泥潭,而是深入到微观个体的体验和情感肌理之中。那些关于政治气候变迁、文化思潮涌动时期,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庇护与意义的描写,读来令人心有戚戚焉。比如,书中对当时某些文学流派兴衰的侧写,那种微妙的权力更迭和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焦虑,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你会发现,所谓的“历史真相”,往往是由无数个被时间磨损、被记忆扭曲的碎片拼凑而成。阅读过程更像是一场考古发掘,你必须摒弃既有的框架,才能真正触碰到那些冰冷而坚硬的“记忆棱镜”下折射出的复杂人性。它不是一本读起来轻松愉快的书,但它提供了理解后世诸多文化现象的深刻语境,对任何关心记忆的社会学或文化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材料。
评分简直不敢相信,这本译作的语言处理能力达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它的文字密度和情感张力,让我仿佛在阅读一首长篇的意识流史诗,而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或非虚构作品。尤其是在描述特定社会事件如何渗透到个人心智结构时,那种句法的破碎与重组,那种对词语边缘意义的精准拿捏,体现了译者对原著精髓的深刻洞察力。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反复咀嚼一句话,因为它不仅仅是在陈述事实,更是在构建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对比起市面上那些平铺直叙、缺乏韵味的译本,这本书的文字本身就成了一种体验。它要求读者投入极大的专注力,但回报是惊人的——你不仅阅读了信息,更是在体验一种语言如何承载和变形历史的强大力量。这种对语言边界的不断试探和拓展,让整个阅读体验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和美学上的享受,是近年来接触到的最顶尖的译作典范之一。
评分从装帧设计和排版来看,出版社显然是下了大功夫的,这本“精装人文译丛”系列的定位确实非同一般。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质感,纸张的选择和油墨的饱和度,都为内容的严肃性提供了一种物理上的支撑。但更让我惊喜的是,内文的版式设计并没有流于传统学术书籍的刻板。在引述关键文本或展示时代照片(如果有的话,我指的是这种风格的典型特征)时,留白的处理、字号的微调,都体现出对阅读节奏的精心考量。这种对“阅读体验”整体性的关注,使得即便是面对枯燥或复杂的社会数据分析时,读者也不会感到心神涣散。它成功地将学术的严谨性,与人文读物的亲切感融合在了一起,让那些可能被普通读者忽略的时代细节,以一种更易于接受且更具仪式感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绝不是一本可以随手翻阅的书,它值得被郑重地对待,并被收藏起来。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迷宫的出口,回望里面那些错综复杂的墙壁和重复的死胡同。它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解构一种“集体叙事如何形成”的过程。作者展示了在特定历史转折点上,文化符号、官方话语和民间潜意识之间如何进行漫长而隐秘的博弈。我尤其关注书中对那些“非正式传播渠道”的关注,比如口头传说、地下出版物中的只言片语,这些才是构成底层记忆肌理的关键要素。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那个年代的认知,可能被主流历史叙事极大地简化或美化了。通过这种多层次的挖掘,读者被迫去质疑自己固有的认知图谱,去寻找那些被光线遗漏的阴影部分。这本书的深度不在于它揭露了什么惊天大秘,而在于它精准地测量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的那道微妙的、充满张力的边界线,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是如何被我们记住(或遗忘)”的全新方法论。
评分G4条
评分1
评分(100Q%好评)Q
评分G4条
评分186条
评分太棒啦!!!!!!!!!!!!!!!!!!!!!!!!!!!!!!!
评分¥23.10(8折)
评分0条
评分不过,这些也许正在改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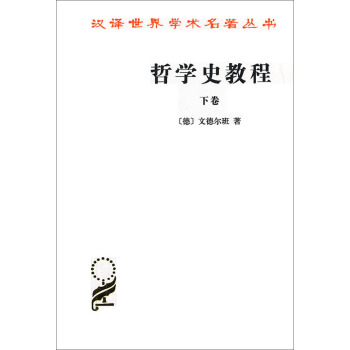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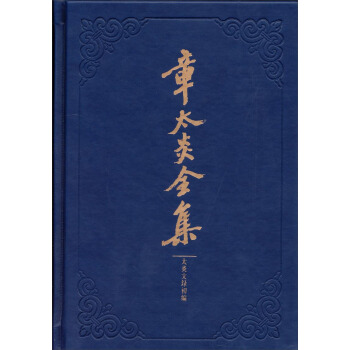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 千高原 [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 A Rea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77982/5848d501N9839df8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