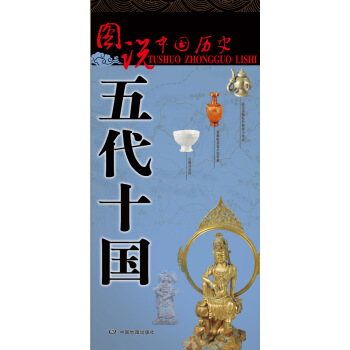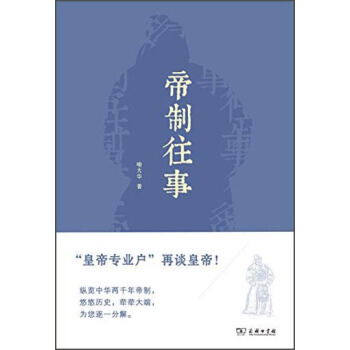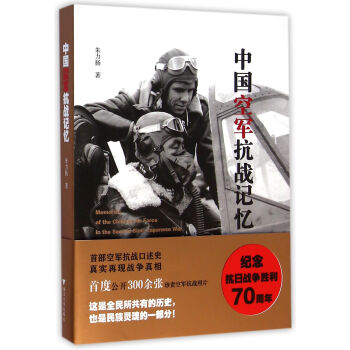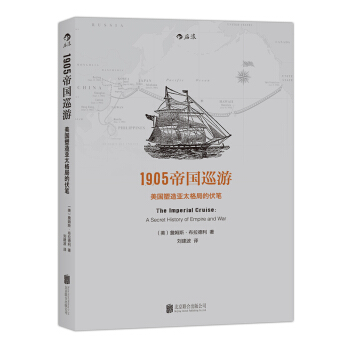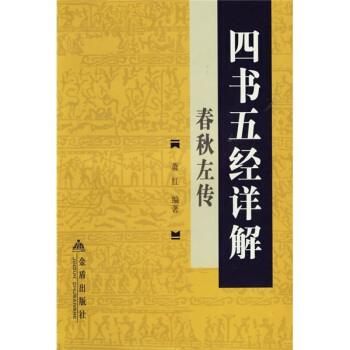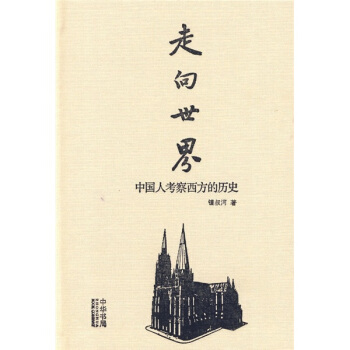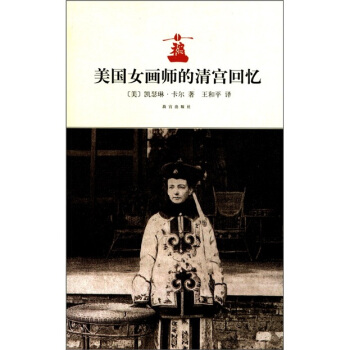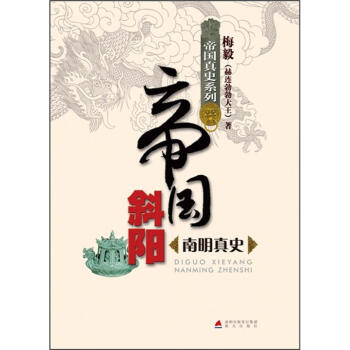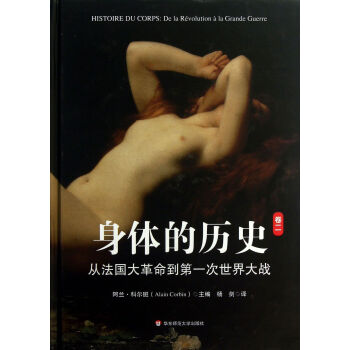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中的《周秦民族史》所述民族迁徙之迹、民族关系之状、民族融合之势,及对其他问题之分析考论,多有为世之学者所少道及者。《巴蜀史的问题》较全面论述古代巴蜀史问题,所论多是长期积累的成果,基本都是创新独到的见解,不少问题是通过二三十年的反复钻研思考才得到解决的,所以常能发人之所不能发,道人之所不敢道,令人读后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给人以莫大启发。内容简介
《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收录了先君子文通公的讲义二种:一、《周秦民族史》,二、《巴蜀史的问题》。《周秦民族史》是一部老讲义,讲用在十年以上,曾经多次修改。本次重印是以川大讲义作为底本,而保留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讲义的第一章,增加了为龙门书局出版《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时所写的《序》和另三篇附录。《巴蜀史的问题》是1959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补充。1961年在川大历史系讲授“巴蜀史”专题课时,曾作为讲义印发。后将两种修改本整合为一,收入先君《巴蜀古史论述》(巴蜀书社1981年出版),今据此重印。兹为便于读者,窃不自嫌浅陋撮取其鄙意以为纲要大旨者,略缀赘语,置于简端,至于能否有裨高明,则非所敢知也。作者简介
蒙文通先生(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字尔达,名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目录
前言 周秦民族史周秦民族史序
第一 周秦时代之地理形势
古代开化之东西线
周代沿东西线之南北开拓
南下开拓之一线
南下线之开拓及黄河南北沮洳地
黄河流域之湖浸
古代黄河流域之生物与气候
古无长江交通
古中江水道
古代之云梦、九江
秦汉浮江之道
古南江水道
古豫章水道存疑
古代长江流域之生物与气候
周时夷夏之分布与地理
周代封建与地理
第二 周民族之南移
西周末年之旱灾
江域雨泽独丰
宣幽继世南向移民
第三 西戎东侵
猃狁东侵
犬戎猃狁与太原
姜戎南侵
犬封古国
犬戎东侵周地
秦为戎族
秦即犬戎之一支
昆夷与羌族
非子邑秦与犬丘
秦取犬戎岐丰
秦取犬戎洛川
秦晋交逼群戎
犬戎侵入伊雒
齐晋霸业与群戎
晋楚灭伊雒诸戎
戎人汝汉江淮
第四 南方民族之移动
楚人北侵
百濮南徙
庸、巴、罗南徙
第五 赤狄东侵
古鬼亲与赤狄
狄来秦晋之北
狄南灭邢卫与齐桓御狄
狄西侵周郑与晋文创狄
狄东侵齐、鲁、宋、卫
狄人济兼并长狄
狄兼并代戎
黄河首次改道为狄祸
群狄建国拓地之广
晋灭赤狄
羌狄与晋民融合
第六 白狄东侵
白狄东徙太行
魏灭中山与中山复国
中山称王与赵灭中山
第七 东北貉族之移动
山戎东徙
骊戎狄柤东徙
涉貊、辰国、马韩东徙
林胡楼烦西还
第八 秦西诸族之移徙
秦西戎族之活动
义渠与匈奴
附录
东夷之盛衰与移徙
瓜州与三危
羌氐与叟赍及其北迁
巴蜀史的问题
一、巴蜀的区域
二、巴黔中
三、巴蜀分界
四、巴蜀境内的小诸侯
五、蜀的古代
六、巴蜀的史迹
七、蜀的经济
八、经济中心的转移
九、巴蜀的文化
十、巴蜀文化的特征
整理本讲义主要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古之治河利水缓,而后之治河利水急,由贾让言之,古以造湖为上策,引渠中而作堤下,今则惟知作堤一策耳,古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南北之堤,相去五十里而遥,今则迫河为堤,黄河之于中国,古今利害全相反,正由治河之术古今全相反耶?古代黄河流域之生物与气候
《禹贡》于冀州日:“岛夷皮服。”知北地之寒;于扬州日:“岛夷卉服。”知南地之燠。泰山之麓,徐、兖之境,服臬丝,宜桑麻,正以气候温和适中,知古时黄河流域之情形,大同于今日长江流域也。凡孟子所谓“汗池沛泽多而禽兽至”,“草木畅茂,禽兽繁殖”,“驱蛇龙而放之菹”,“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皆非今日北方之情势所宜然。《小雅》曰“如竹苞矣”,《卫风》日“籊籊竹竿”,又日“菉竹猗猗”,斯皆古代北地产竹之证。《东观汉记》言:郭伋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刘子玄日:“晋阳无竹,古今共知,假有传檄他方,盖亦事同大夏,况在童孺,弥复难求,群戏而乘,如何克办。”由子玄之诋《汉记》,可知晋阳汉多竹而唐无竹也。唐时晋阳童子寺有竹,日报平安,知于时晋阳植竹之难。在汉则不然,《沟洫志》言:瓠子之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后汉书》言:寇恂为河内太守,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是彼时北土之竹,多且贱也。《货殖列传》言:“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地理志》言:秦地“鄂杜竹林,南山檀柘,号为陆海。”其在周季,襄之十八年:晋帅诸侯之师围齐,焚申池之竹木。
前言/序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师讲义》丛书。从书名看,意思很清楚。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这些位名师,都是20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如闻一多、朱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师;再如游国恩、雷海宗、周祖谟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他们虽都已去世多年,但薪尽火传,其衣被学人,早非一代。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据我看,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
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十分高兴。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只写此短序,聊当前军旗鼓云耳。
用户评价
我个人特别欣赏的是,这本书在涉及对少数民族史料的引用和解读上,表现出的那种细致入微的学术态度。很多关键性的论述都建立在对传世文献中那些不易被注意到的细节、地方志的侧注,乃至碑刻拓片的重新审视之上。作者似乎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他能从看似零散甚至互相矛盾的材料中,抽丝剥茧地还原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这不仅仅是史料的堆砌,而是一种高超的史学解读艺术。每一次引用,都经过了审慎的权衡和注释,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操守。这对于希望进行更深层次研究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它提供了一个可供反复推敲、深入挖掘的坚实基座。
评分我接触过不少史学著作的导论部分,但这本书开篇的论述角度之新颖,实在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似乎没有急于跳入纷繁复杂的时间线或族群细目中去,而是先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地理与文化互动的大框架。他巧妙地引入了某种“流动性”和“渗透性”的视角来审视古代族群关系的演变,打破了传统史学中那种泾渭分明的“你是我者,我非你者”的刻板印象。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拓展了我对“民族”这一概念在古代语境下理解的深度与广度。读起来感觉就像是站在高处俯瞰,而非局限于某个特定部落的视角,历史的脉络因此变得更加立体和富有张力,不再是孤立事件的简单堆砌,而是相互影响、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这种开篇立论的格局,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到的史观。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是太让人眼前一亮了,封面采用了一种低调而富有质感的哑光纸张,触感温润细腻,拿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封面上那枚印章式的图腾,设计得古朴典雅,若隐若现的纹路仿佛诉说着悠远的历史故事,让人一瞥之下就心生探究的欲望。内页的排版布局也体现了出版方对阅读体验的极致追求,字体的选择清晰易读,行距和段落间距把握得恰到好处,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视觉疲劳。装订工艺更是无可挑剔,线装得结实牢靠,书页翻动间流畅自然,让人忍不住想一遍遍摩挲。整体而言,这本实体书的物理质感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教材范畴,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光是捧着它,就已经能感受到一股知识沉淀下来的宁静与力量,为接下来的深入研读做好了极佳的心理铺垫。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无疑是专业精神的最佳体现。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握得非常精妙,读起来完全没有一般学术专著那种枯燥乏味的拖沓感。作者似乎深谙如何“讲故事”,他总能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设置悬念或者提出引人深思的疑问,让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后续的发展和解释。举例来说,在描述某一重要迁徙事件时,他并没有采用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侧重于描绘当时社会环境的压力、决策者的心理博弈,甚至辅以一些考古发现的佐证,使得原本抽象的史实变得鲜活可感,仿佛穿越时空亲历其境。这种将严谨的学术考证与生动的文学叙事完美融合的技巧,使得即便是对某些偏冷门历史阶段不甚熟悉的读者,也能轻松跟上思路,并且沉浸其中。这无疑是教科书和严肃研究之间找到的一个绝佳平衡点。
评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处理涉及多方族群利益冲突与文化融合的敏感议题时,展现出的那种罕见的客观与克制。他没有采取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致力于还原当时的社会逻辑和生存策略。在分析那些可能被后世贴上“征服者”或“被同化者”标签的群体时,他细致地考察了权力结构的变化、资源分配的调整以及身份认同的模糊地带。这种深入骨髓的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维,使得书中的每一个论断都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预设立场的价值判断。这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理解多元文化共存的复杂性,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历史镜鉴。阅读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真相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复杂人性幽微之处的精准捕捉。
评分以现代民族的观念看待先秦时代的人不免有失偏颇偏颇,然蒙先生对古集考据整理的水平今世无人可及了
评分名师讲义: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不错
评分不愧是大师啊很好的书。。。。。。。
评分名师讲义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和描述的一样,好评!上周周六,闲来无事,上午上了一个上午网,想起好久没买书了,似乎我买书有点上瘾,一段时间不逛书店就周身不爽,难道男人逛书店就象女人逛商场似的上瘾于是下楼吃了碗面,这段时间非常冷,还下这雨,到书店主要目的是买一大堆书,上次专程去买却被告知缺货,这次应该可以买到了吧。可是到一楼的查询处问,小姐却说昨天刚到的一批又卖完了!晕!为什么不多进点货,于是上京东挑选书。好了,废话不说。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它是一个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工具不这么说,不这么写,就会别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腔调有时候就是器,有时候又是事,对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说,器就是事,事就是器。这本书,的确是用他特有的腔调表达了对腔调本身的赞美。|发货真是出乎意料的快,昨天下午订的货,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赞一个,书质量很好,正版。独立包装,每一本有购物清单,让人放心。帮人家买的书,周五买的书,周天就收到了,快递很好也很快,包装很完整,跟同学一起买的两本,我们都很喜欢,谢谢!了解京东2013年3月30日晚间,京东商城正式将原域名360更换为,并同步推出名为的吉祥物形象,其首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改版。此外,用户在输入域名后,网页也自动跳转至。对于更换域名,京东方面表示,相对于原域名360,新切换的域名更符合中国用户语言习惯,简洁明了,使全球消费者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访问京东。同时,作为京东二字的拼音首字母拼写,也更易于和京东品牌产生联想,有利于京东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提升。京东在进步,京东越做越大。||||好了,现在给大家介绍两本本好书谢谢你离开我是张小娴在想念后时隔两年推出的新散文集。从拿到文稿到把它送到读者面前,几个月的时间,欣喜与不舍交杂。这是张小娴最美的散文。美在每个充满灵性的文字,美在细细道来的倾诉话语。美在作者书写时真实饱满的情绪,更美在打动人心的厚重情感。从装祯到设计前所未有的突破,每个精致跳动的文字,不再只是黑白配,而是有了鲜艳的色彩,首次全彩印刷,法国著名唯美派插画大师,亲绘插图。|两年的等待加最美的文字,就是你面前这本最值得期待的新作。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白宫智囊团、美国、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当今世界最高明的思想控制与精神绑架,政治、宗教、信仰给我们的终
评分蒙文通民族史学代表作,值得收藏!
评分名师讲义: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
评分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评分挺喜欢吴思的。他看历史,有点儿像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读史做研究,需要这点“小人之心”,才看得透彻。站得太高,指点江山,或是正人君子状,激扬文字,其实都打不着中国历史的要害。像吴思这般冷冰冰,在浩瀚史籍的犄角旮旯里挖出些活生生的事例,条分缕析,反倒塌实。有时又挺恨吴思的,嫌他把中国历史看得太透,且看着得没一样好东西。想起李嘉和我说过的一个故事:说是北京市为解决08奥运的交通问题,请来外国专家团实地考察,给出报告。外国专家站在我们立交桥上凝神看了半小时,摇摇头:“死循环,没得治。”把吴思看到的中国历史的所有症结综合起来,也是个循环,死循环。就像病菌顺着块腐处不断孳生,不断孳生,最后烂到面目全非。海瑞罢官后,气呼呼地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朱元璋听多了报告,感叹:“呜呼!为了方便生民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呜呼,治国难呀。” 看来不是没人想改变,可连皇帝老子都没辙的事,又能如何?真有点让人灰心丧气了。 我原先知道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来约束可能“恶”的王权,而儒家的信念又要求他们在“恶”的时代挺身而出,几近于赤手空拳。被小人进了谗言,流放千里,也没几个能真正忘情山水,还得心系朝廷,无法安身立命的精神困境想必苦不堪言。现在我又发现百姓面对官吏皇帝的侵犯,缺乏应手的反击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式的迂阔和耿直。这未免过于软弱淡薄了。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可百姓也不那么无辜,也非善类。黑泽明的《七武士》虽是个外国货,却把这点说了个透:七武士多NB啊,义务帮农民打退了山贼,结果呢,走得时候冷冷清清,没人搭理。岛田最后无奈地感叹“这次也算是一个败仗。胜利的不是我们,是农民”。就像吴思分析的“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说白了,就是牺牲英雄)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挟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我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这可能是冰冷的《血酬定律》中最有温情,也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了。当时在我脑中浮现出的人物,不是中国人,而是华盛顿。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最有力量的人无疑是掌控整支军队的乔治华盛顿将军。当时的美国政府一穷二白,欠着一大笔士兵的军饷和伤亡者抚恤。出生入死的军官们对文官政府很不满意,有人主张立统帅华盛顿为君主,被他严词拒绝。于是一些军官决议绕开华盛顿,私自谋反。华盛顿得悉后,火速冲入谋反者的会场,要给他们念一封议员的信。他手持信纸,却读不出来,在口袋里摸摸索索,找着老花眼镜。华盛顿轻声地说:“先生们,请等我戴上眼镜。这么些年,我的头发白了,眼神也不济了。”军官们的满腔怨愤在这一刻突然崩溃:八年共同生生死死的将军,如今老了。他站在大家面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个他信奉的原则祈求自己的部下:不要用武力威胁文官政府的议员。一场可能的兵变,化解了。华盛顿替新生的美国做出了第一个选择:不要国王的专制,也不要以枪杆子维持的军政权。我在这里所感慨的,不是华盛顿将军的大公无私,我所哀悼的,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如华盛顿般大公无私的英雄们,他们都成了民众给予统治者的祭品。 今天,华盛顿纪念塔宁静地高耸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方的广场上,可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呢?恕我无知,我还在努力寻找你们的名字。
评分蒙先生出版的书不多,有许多已经绝版,这本书和他的古代史讲义都还不错,便于我们一窥蒙先生的治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18670/rBEhWlMhI34IAAAAAACzl7uu9jwAAJ9ggJN5G8AALOv33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