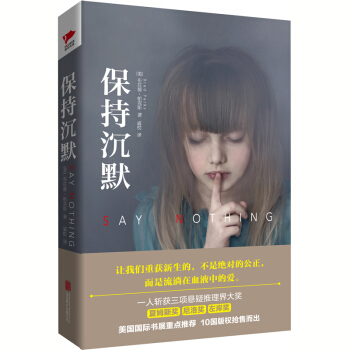![马人(厄普代克作品) [The Centaur]](https://pic.tinynews.org/12109817/59defe76N08cd6718.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马人》是厄普代克确立其大师声誉的重要作品,厄普代克凭借《马人》而获得国家图书奖,也是他所有作品中颇具艺术性的代表作之一。
内容简介
《马人》是厄普代克确立其大师声誉的重要作品,他因此而首次拿到国家图书奖,也是他所有作品中颇具艺术性的代表作之一。《马人》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但这是一部极富情感力度的作品,在小说中将这份父爱写得沉蕴有致,富有悲剧的深度。这本书几乎是在提醒我们注意两点:其一是怪异的马人形象中所蕴含的非凡主题,其二是主题与表现形式所达到的珠联壁合的效果。它将神话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既有象征的寓意与美感,又兼具现实的尖锐与残酷,以超现实主义与立体主义绘画的方式将一个父与子、爱与牺牲的故事讲述得优美、深刻、感人肺腑,一部不折不扣的“杰作”。
作者简介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3.18—2009.1.27),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于一身的美国当代文学大师,作品两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获得欧·亨利奖等其他众多奖项多达十数次。“性爱、宗教和艺术”是厄普代克毕生追求的创作标的,“美国人、基督徒、小城镇和中产阶级”则是厄普代克独擅胜场的创作主题,他由此成为当之无愧的美国当代中产阶级的灵魂画师,被誉为“美国的巴尔扎克”。
精彩书评
“厄普代克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文学家——不但是优秀的长篇短篇小说家,也是同样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他将和他的前辈、19世纪的霍桑一样永远成为美国文学的国宝。他的辞世是美国文学不可估量的损失。”——菲利普·罗斯
“厄普代克的文学体系和巧妙构思直逼莎士比亚……他的逝世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美国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的终结。”
——伊恩·麦克尤恩
“《马人》无可企及,无法逾越……自然、贴切、新鲜、微妙,而且极为优美。”
——《新闻周刊》
“与D·H·劳伦斯之后的任何作家相比,约翰·厄普代克肯定有着一种更纯粹的能量。”
——马丁·艾米斯
“一部光彩照人的杰作……而且厄普代克毫无疑义是一位语言的大师,只有优美的诗歌能够跟他对语言的驾御相匹敌。”
——《星期六评论》
“(对许多年轻作家来说,厄普代克)几乎像圣经中的一位族长,一位亚伯拉罕或摩西那样的人物,他赫然耸立,而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他的影子里”。
——一位加拿大文化记者
“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欣赏的书是约翰·厄普代克的《马人》。”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精彩书摘
卡德威尔一转身,他的踝部中了一箭。学生们哄堂大笑。疼痛的感觉,从他胫部的狭长经络往上蹿,在他的膝部复杂组织中转悠,往外扩展,再蹿到他的肠子,疼得更凶了。他疼得眼睛往上一翻,目光射到黑板上他曾用粉笔写过的数字上,5,000,000,000(宇宙的大致年龄)。学生的哄笑,从吃惊的第一声尖叫升级到集体故意起哄,这声浪像是在向他压过来似的,粉碎了他想单独待一会儿的愿望。让他单独待一会儿,独自面对这疼痛,揣摸其疼痛度、估计其时间、检查其机理。疼痛已把触角伸到头上,展开湿漉漉的羽翼,沿着他的胸腔四壁扩展,只疼得他,在一阵双目昏花之中,感到自己仿佛是一只梦中惊醒的大鸟。那留有昨夜擦洗痕迹的混浊的黑板像薄膜一样粘在他的意识中。疼痛似乎以毛茸茸的分量取代了他的心肺;当疼痛的袭击在他的喉咙里猛的一涨时,他觉得他仿佛把自己的脑子像一块肉一样高高地托在一个想够也够不着的盘子上了。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衬衫的学生已经从书桌后站了起来,向他们的老师呼叫嘲笑,还把泥鞋蹬折叠椅上。这混乱实在难以忍受了。卡德威尔跛行到门口,把那狂闹声关在他的身后。走到大厅里,每走一步,带羽的箭梢就在地板上划一下。那金属擦地声和羽毛僵硬的瑟瑟声难听地混在一起。他的胃开始翻腾、恶心起来。那赭色大厅昏暗的长壁在摇晃;嵌着带号码的方形磨砂玻璃的几扇门像是实验板,浸在充了电的活性液体里,而电流就是孩子们朗读法语、高唱各国国歌、讨论社会科学的声浪。你有一所漂亮的房子吗?是,我有一所很漂亮的房子,琥珀色的谷浪,巍峨的高山俯瞰着富饶的平原,通观我国历史,男女同学们(这是福罗斯的声音),联邦政府的威望、权力和权威已增长,但我们不能忘记,男女同学们,我们原本是许多主权共和国的联合体,那合众的上帝赐福于你,在诸多美德之上赐你以兄弟友情——这首美丽的歌美国国歌。莫名其妙地久久盘旋在卡德威尔的脑子里。到灿烂的海。老狐禅。他是在帕塞伊克新泽西的一个地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从那以后他长成多么奇怪的样子啊!他的上半身像是漂浮在理想的星空和年轻人的歌声里;下半身却沉重地陷入一片沼泽里迟早要淹死。每一次箭羽擦着地板,箭杆就刺他的伤口。他尽量不使他的腿碰上地板,但是剩下来的三个蹄子的杂乱的啷当声很大,他怕会有一扇门被推开,闪出另外一个教员来挡住他的去路。在这危机之中,他的同事像是一些放牧恐怖的牧人,有把他挤回到学生们的课室的危险。他的肚肠有些抽搐;他没有停步就在那有上百只银眼睛在闪烁的奖杯盒前锃亮的油漆地板上投下了一个扩散的椎形阴影。他那件灰花呢上衣的下摆难看地扇动着,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船头雕,他的脑袋和肌体一起向前方冲去。
边门上面模糊的水渍在吸引着他前进。在大厅的尽头,光线穿过加了防盗纱窗的窗口从门外射到学校里,在这黏乎乎的、油亮的气氛中散不开,像油中之水滞留在入口处的上空。卡德威尔脑子里的飞蛾驱使着他的高大、优美、复杂的身体向这青蓝色的光团奔去。他的五脏直翻腾;一支牙碜的触角在划他的上牙膛。可他也在急切地品味着即将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期待感。空气明朗了。他冲出了用铁丝加固、玻璃肮脏的双重门。在箭杆撞击钢栏杆引发的一阵剧痛中,他跌跌撞撞地跑下了通往水泥地面的低台阶。一个孩子在走上这些台阶时在那暗淡的墙壁上匆忙地写了一个“FUCK”。卡德威尔握住了铜把手,在他那酸痛、恐怖的眼底下,嘴唇抿成一条线,坚决地推开门冲到校外。
他的鼻孔冒出两道霜烟。这是一月份。湛蓝的高空既似逼人,又使人难以捉摸。校园旁的芳草地广阔舒展,角落上种的松树虽值隆冬依然翠绿;但这颜色是凝滞、呆板、病态、不自然的。在校界之外,一辆电车发出清脆的当当声从马路上出现,往伊利方向驶去。车厢几乎是空的——因为时间是十一点;买东西的人在向相反方向走,去阿尔腾——在轨道上轻微地摇晃着,草垫椅通过车窗洒出点点金光。他来到室外,在开阔的街道上,疼痛似乎羞涩地减弱,收缩到踝部,凝固,麻木,可以漠视了。卡德威尔端正他的异样的身架;挺起那与他的大骨架相比有些偏窄的双肩,这姿态即使还不到昂首阔步的程度,那么,他那顽强的克制的步伐至少遮掩了那一瘸一拐的模样。他走上位于封冻的草地和挤得满满的停车场之间的便道。在他的腹部以下,奇形怪状的汽车前挡板在冬天的白日中闪耀着;电镀上的划痕像宝石似的闪烁着。寒冷开始使他呼吸变得短促。他身后那红砖砌的中学校舍里的蜂音器响了,解散了他所遗弃的那班学生。随着一片缓慢移动的吵闹声,学生们轮换了课室。
亨迈修车厂和奥林格中学校园毗邻,中间只隔着一条不规则的小沥青道。厂校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地域相接。亨迈过去曾任校董多年,现在不当了。他的年轻的红发妻子薇拉是女生们的体育教员。修车厂做着许多学校的生意。男孩子把他们的破汽车送到这里修理,再小些的男孩子用这里的免费气筒给篮球打气。厂房前部有一个大房间,亨迈在这里放他的账本和已经摸黑了的成套的零件价目本。并排的两个木桌上都放着一沓残角单据和便条本,插得厚厚的粉色收据一直串到插签的锈迹斑斑的签头上。桌上放着一个磨砂玻璃匣子,匣盖上有一道用车胎胶布补上的闪电形裂纹,里边放着用花纹纸包着的糖果,等着孩子们的分币。一个底面与外边街道等高的五英尺深的洋灰坑边疏落地放着一排油污的折叠椅,午间时常有一些男教员(过去多,最近少了)坐在这里把扎紧鞋带的擦亮的皮鞋蹬在栏杆上吸烟、吃巧克力棒糖、里斯牌巧克力花生碗糕、埃希克薄荷糖,舒展一下他们紧张的神经。这时,亨迈的那些膀大腰圆的工人便在那有三面围墙的洋灰坑里冲洗像一块大铝砖似的汽车。
通往这汽车修配厂的主要和大部分厂房的沥青拱坡地面百孔千疮,到处掉皮起泡,像一片火山岩浆流的遗迹。在汽车进厂的绿色大门上开了一个一人大的小门。小门门闩下边用蓝色的调和漆歪歪扭扭地写着“随手关门”。卡德威尔拉开门闩走进去。他那疼痛的脚诅咒着关门时不得不回身。
电火花照亮了温暖黑暗的车间。这间阴暗厂房的地板被滴下的机油染成了黑色。两个戴着防护镜的模糊人影在长长的工作台的远端拥簇着向下喷射的扇形大火柱,化成四射的寒星。另外一人,黑魆魆的脸上翻着刷白的圆眼,翻身仰卧下去,消失在一辆汽车车身下面。卡德威尔的眼睛适应了房里的暗度,看见在他周围堆放着的是翻转过来的零件,一些残破、失灵的部件:乌龟壳似的前挡板、像从肚膛里掏出来的心脏似的引擎。在这杂乱的气氛中,接连不断地响起嘶嘶的、砰砰的怒吼声。在卡德威尔站着的位置近旁,有一座鼓肚煤炉冒着粉色的火光。尽管他踝部的创口在化冻、胃里在翻腾,他还是不太情愿离开这温暖的辐射圈。
亨迈本人在车间门口出现了。当他俩互相走近时,卡德威尔有一个滑稽的想法:感到自己在向一面镜子走去。亨迈也跛着脚。由于幼时摔伤,他一只脚比另一只短。他有些苍老、苍白、驼着背,近年来这位机械师衰老了。埃索和摩比尔汽油连锁公司在高速公路旁距这里仅几条街的位置上建立了服务站,现在大战结束了,谁都能用战时工作的钱买新车,修理汽车的活少多了。
“乔治!都到你吃午饭的时间了?”亨迈的声音虽然轻,却颇有经验地使用一种能盖过车间杂音的高调门。
在卡德威尔回答的时候,一连串难听的金属撞击声响了起来,把他的话盖住了;他那轻飘、艰涩的声音似乎喑哑地在自己的耳边回旋。“不,上帝,我正在上课。”
“那么是怎么啦?”亨迈那由几撮银发辉映得发灰的面容怯懦地警惕起来,好像怕发生了什么伤害到他自己的意外事情似的。他的妻子曾经干过这类事,卡德威尔是知道的。
“你瞧,”卡德威尔说,“那群倒霉孩子当中的一个是怎么整我的。”他把他那只受伤的脚蹬在一个拆下来的前挡板上,拉起他的裤腿。
机械师弯下腰查看那支箭,用手摸了摸箭羽。他的指关节缝里满是油污,触到皮肤时有一种滑腻腻的感觉。“钢扦子,”他说。“你真走运,箭头整个都进去了。”他做了一个手势,一个带轮子的三脚架哐啷啷地在凸凹不平的黑地面上滚了过来。亨迈从那上面取下一副铁丝钳子,是一把钳齿上带螺丝扣以加强轧断力的那种。像一个氢气球的拉线从一个心不在焉的孩子手里滑脱一样,卡德威尔一害怕,便浮想联翩起来了。在昏沉沉神不守舍的状态中,他把这把钳子当成一个几何图形,这么分析着:机械能等于物体除以动力减去摩擦力,杠杆AF的长度(支点=螺顶)除以FB长度,B是光亮的半月形钳齿,乘以第二机械效能副支点——杠杆组合,再乘以亨迈的镇定、那双油污的手的技术,那曲骨收缩和指骨硬挺形成的力的五倍,MA×MA×5MA=泰坦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大力神。的巨大力量。亨迈弯下腰为了让卡德威尔扶着他的肩。卡德威尔拿不准这意思,也不愿假定他是这意思,便仍然直立着,眼睛往上翻着。修配厂的凸圆线条的天花板被煤烟和蜘蛛网迹染得毛茸茸的。卡德威尔通过膝盖的感觉知道亨迈的背部在移动,是在下钳子;他感到一个金属物穿过他的袜子接触到皮肤。脚下的汽车前挡板不稳定地颤动着。亨迈的肩头用力一挺,卡德威尔一咬牙没喊出声来,似乎那钳子啃的不是那金属箭杆,而是他躯体上露出的一根神经。那半月形的钳口一咬;卡德威尔的痛感风驰电掣般刷地一下就蹿到头顶上了;随之亨迈的肩头放松了。“不行,”机械师说。“我以为箭杆子或许是空心的,可它不是。乔治,你得到工作台那边。”
卡德威尔的两条腿像自行车辐条那么单薄,从上到下都在抖动着,跟随亨迈走了过去。机械师从那长长的工作台下边那布满尘土的杂物中找到一个可口可乐箱子,卡德威尔顺从地把脚蹬在箱上。为了不去理会那在他下视余光中像一个赘瘤一样到处跟随着他的箭杆子,卡德威尔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盛满丢掉不用的汽油泵的大篮筐上。亨迈拉开了一个没有灯罩的电灯泡。车间的窗户都被从外面溅上的油漆挡住了光线;窗户之间的墙面上挂着按大小尺寸排列的工具钳,把子用胶布缠着的圆头锤、电钻、足有一码长的大螺丝刀、非常复杂的装着齿轮的连环套结的工具,它们的名称和用途他一辈子也弄不明白,卷好的旧钢丝、卡钳、扳子。在工具空隙间、空白面上还钉着、粘着破旧熏黑的各种广告。一幅画上有一只抬起前爪的猫,另一幅上画着一条大汉使着牛劲也扯不断一条带专利注册商标的风扇带条。一张纸卡上写着安全第一,另一张粘在窗上的纸卡上写着:
保护你的没人再
赋予你另一双
像一首歌颂物质创造的歌,那工作台上七零八落地铺陈着橡皮圈、铜管子、炭精棒、套丝铁弯头、油脂罐、木头块、破布头、润滑剂,沾满灰尘、无奇不有的破东西。工作台那头两个工人的强烈的电闪光在这杂乱的工具台上翻滚着。他们正在为一个细腰身肥屁股的女人加工一条类似雕花铜腰带的东西。亨迈把一个石棉手套戴在他的左手上,从料堆里拣出一块马口铁。他用剪钳在它中间急速灵巧地一翻,窝成了一个凹形挡板,在卡德威尔踝部后把箭杆圈起来。“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太烫了,”他解释着,又用没有戴手套的那只手打了一个榧子。“阿齐,能把焊枪给我使一下吗?”
那助手小心着脚底下,怕让地上的铁丝绊着,把乙炔枪送了过来。那是一盏喷出带蓝边的白色光焰的黑色喷枪。在火焰从枪口喷出的地方有一块透明的空隙。卡德威尔咬住了牙,按捺着他的恐惧。那箭杆在他眼里像是一条活神经。他准备着迎接那必需忍受的疼痛。
没有疼。他梦幻般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感觉的巨大光轮的中心。光线突然变成了三角形的黑影,散布在他周围:在工作台上,在墙上。亨迈用戴手套的那只手握住那块马口铁,没戴防护眼镜,睨视着卡德威尔踝部的突突的、燃烧着的中心点。他那死灰的、从俯视角度变得特别短的脸上两只眼奇怪地闪烁着。在卡德威尔往下看的时候,亨迈的一缕疲惫的灰发掉到前边,在一缕青烟之中蜷缩、消失了。那个助手默默地看着。似乎认为时间用得太长了。这时卡德威尔感到烤了;那马口铁接触的地方有些烧腿了。但他闭上眼,从亨迈的头上可以幻视到那支箭在弯曲、熔化,它的分子在分解。一个小金属块哐啷掉在地上。围绕在他脚周围的压力解除了。他睁开了眼,焊枪熄火了。那黄色的电灯光好像变为暗褐色的了。
“罗尼,能给我拿一块沾湿的布头吗?”
亨迈对卡德威尔解释道:“我不想这么热的时候把它拔出来。”
“你真是把高手,”卡德威尔说。他没想到他的声音会这么小,他的恭维话说得那么苍白无力。他看着那两个肩膀像两座小山、独眼的年轻人罗尼手拿油污的布头到那头电灯下盛污水的小桶蘸蘸,被搅动的水的反光翻滚着,像要流出来。罗尼把布头递给亨迈,亨迈蹲下来往伤口上贴。冷水滴到卡德威尔鞋里,一股淡淡的香味嘶嘶地升到他的鼻孔。“现在咱们等一会儿,”亨迈说。他仍然蹲着,小心地扶着卡德威尔的裤脚,不让它罩上伤口。
卡德威尔的目光和瞪眼瞧着的三个工人的目光对上了(第三个工人已从车身下面爬了出来),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现在就要松口气了,他有了一刻感到不好意思的空儿。他这一笑引得那三个助手咧了咧嘴。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汽车要说话似的。卡德威尔让自己的目光散开,海阔天空地想着碧绿的原野,想着谷物女神卡里克罗现身为一个妖娆的女郎,想着彼得孩提时代的样子,想着他怎么在七叶树下的便道上把他放在那长叉把的婴儿车上推着走的情景。他们太穷了,买不起篷式婴儿车;那孩子会开车了,太早吧?他一有空便对那孩子有点担心。
……
前言/序言
永远的厄普代克及其《马人》一
约翰·厄普代克属于那种特别受宠于缪斯女神的作家。他出道早,年仅32岁即入选为美国国家艺术文学院院士,是获得这种殊荣的美国作家中最年轻的。无疑,他有着令人艳羡的文学天分,不仅擅写小说,还在诗歌、随笔、文学评论、戏剧和传记等诸多文学样式上各有造诣,在文坛上有“奇才”(prodigy)之美誉。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马丁·艾米斯(MaritnAmis)这样赞叹道:“他[厄普代克]说自己家有四间书房,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早餐前到其中一间写首诗,之后在另一间写上一百页小说,下午换到第三间为《纽约客》写一篇精彩的长文,最后在第四间书房里脱口背上几首诗。与D·H·劳伦斯之后的任何作家相比,约翰·厄普代克肯定有着一种更纯粹的能量。”不过,厄普代克本人似乎更愿意别人了解他才气之外的另一面。在回忆录中,他形容自己的文学事业好比骑上双轮车,只有不停地蹬才不会从车上掉下来。
照此看,有位评论者将他比作“文学蜘蛛”的话在他也许更有会心默契之意。不管是在蹬车还是结网的比喻中,厄普代克都展现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成熟品质:勤奋、执着、不懈。他在5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林林总总出版了近60部作品,成为当代文坛最高产的文学多面手。他所获的文学奖项和荣誉之多足以确立他当代经典作家的地位,有文学评论者称他为“美国的巴尔扎克”。2009年1月27日,他因肺癌病逝于美国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随后我们看到,厄普代克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被无数热爱他的读者温暖地怀念着。一位加拿大文化记者撰文说,对许多年轻作家来说,厄普代克“几乎像圣经中的一位族长,一位亚伯拉罕或摩西那样的人物,他赫然耸立,而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他的影子里”。
厄普代克1932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个三代同堂之家,养家的是厄普代克的父亲,他在一所中学当了30年的数学教员。在厄普代克1964年出版的小说《马人》(TheCentaur)中,主人公乔治·卡德威尔身上就有这位父亲的影子。这部小说中的部分故事素材也取自于这段早年的大家庭生活。
对厄普代克有文学启蒙影响的是他的母亲。她喜欢阅读,自己也时常写作。在母亲的熏陶下,厄普代克的文学兴趣得到了鼓舞和培养。少年时的他曾梦想有朝一日当个职业漫画家,能在《纽约客》杂志里发表作品。迷恋绘画的同时,他也开始尝试着写一些诗歌和文章,但屡遭退稿。这些最初的文学习作,厄普代克却敝帚自珍地保留了下来。
1950年厄普代克进入哈佛大学读文学,4年后以优等生荣誉毕业。哈佛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生涯有着重要影响。据他回忆录中所说,当时的哈佛曾经有一批诸如T·S·艾略特、罗伯特·弗罗斯特、狄兰·托马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样的文学名流亲临讲坛。可以想象,得以亲炙大师,这对怀抱一腔文学激情的学生来说是何等弥足珍贵的经验。厄普代克曾在为《哈佛学报》(TheHavardGazette)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回忆过那段美妙的时光:“文学成为时髦,流行音乐听帕蒂·佩奇和佩里·科莫,电影看多丽斯·戴和约翰·韦恩,青年文化是那种发生在夏令营的事——如果要说什么地方的话。”TomVerde,pp.150—151.从哈佛毕业的这一年,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篇名为“来自费城的朋友”的短篇小说。
1954年至1955年,厄普代克靠一笔奖学金在英国牛津大学拉斯金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在此期间,《纽约客》的资深主编、著名作家E·B·怀特曾会过他一面,邀他加入《纽约客》的作家班子。厄普代克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携家返回美国,并在纽约定居下来。从1955年至1957年,他主要为《纽约客》撰写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写得机智优雅,显示出他驾轻就熟的文字功夫。然而,一段时间下来,他逐渐对纽约浮躁的文学圈感到失望。他开始担心自己怀抱远大的文学事业就此搁浅,于是毅然辞去了杂志的工作。他离开了纽约,迁往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僻静小镇,在那里潜心创作,一呆便是17年之久。在旁人看来,对于当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厄普代克来说,离开热闹时髦的纽约文学界至少是个得失难测的举措,但他本人相信这是明智之举,而他后来的发展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最能代表厄普代克文学成就的是他的长篇小说。他的第一部作品《贫民院集市》(ThePoorhouseFair,1959)出手不俗,得到了当时著名小说家兼评论家玛丽·麦卡锡(MaryMcCarthy)等文坛名人的好评。厄普代克将小说中的时间背景推到20世纪末,描写了一个州立贫民院里的老人与贫民院的管理者康纳之间的冲突。康纳在小说中被刻画成一种“未来人”,他认为现代的人类生活混乱无序,犹如“被困在一间封闭屋子里的疯子”。他相信代表理性的科学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完美的新秩序。贫民院中的一位老人曾对康纳说过这样的话:“要是由你和像你这样的人来安排天上的星星,你们会把星星照着几何图形分布出来,或者把它们排出一个令人深思的句子。”康纳这一人物体现的是一种约束自由个性的机构化统治力量。贫民院的一位老人抱怨康纳在他们每个人的椅子上贴了姓名标签,这令人想起在监狱里给囚徒每人规定一个囚号的做法。小说中的贫民院也确实像座监狱,老人们的生活在秩序的管治下变得死气沉沉。但他们也有反抗,那就是他们每年举办一次的集市。康纳从他那高高的办公室的窗子向下看到的集市是这样一幅场景:“一群群的人看上去像嗡嗡嘤嘤、没头没脑的虫子,彼此碰碰撞撞,胡乱而匆忙地在草地上过来过去。”集市热闹而混乱,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但正是在这种气氛中老人们体验到了无拘无束的生命自由。狂欢焕发了他们抵抗衰老的生命本能。这部小说是对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的讽刺,指出建立在非人性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完善秩序难免使人类付出牺牲人性自由的代价。厄普代克因这部小说获得了国家艺术院的罗森瑟尔奖。
真正使厄普代克文名鹊起的是他出版于1960年的第二部小说《兔子,跑吧》(Rabbit,Run),这是他后来发展为“兔子系列”中的第一部。小说主人公哈利·安斯特朗绰号为“兔子”,中学时曾是一位风头十足的篮球明星。到了26岁,已有了老婆孩子的“兔子”感到自己的生活无聊乏味,家庭日渐成为使他厌倦的责任,推销厨具的工作毫无成就感可言,单调的日常琐事在消耗他的精力,教会也给不了他精神安慰。总之,他觉得身边周围的一切都在“挤压”他(小说中多次以“crowded”一词来描写他的感受),窒息他的内心冲动和愿望。当这种压抑令他不堪忍受时,他便开始选择了逃跑。然而,他并非一跑了之,而是跑了又回来,回来后又跑,如是反复。“跑”是这部小说中的核心隐喻,它体现的是“兔子”无法自已的内心冲突。这种冲突的实际内涵,笼而统之地讲,是个人精神需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兔子的“跑”在小说中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行为。一方面,他逃离家庭,实际上是逃离社会要求于个人的正当责任;另一方面,他的“跑”也意味着精神上的活跃,含有一种探索的积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跑”也可以看作是要摆脱世俗生活里束缚个性及精神自由的种种条规,包括婚姻、家庭的压力、机构化的宗教、问题百结的经济生活、中产阶级社会的道德价值和时尚文化的影响等。当然,“兔子”本人对其“跑”的深层心理动机不会具有如此的自觉意识。小说中的他不擅表达,多凭直觉来感受事物。对于来自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秘召唤,他只能以含混不明的直觉性语言来表达:“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某个地方有某种东西在引我去找到它。”有评论家通过对小说全部采用现在时叙述的分析,指出了“兔子”这一人物“感而不思”的特征。DonaldJ.Greiner,JohnUpdike’sNovels(Athens,Ohio:OhioUniversityPress,1984),p.49.但正是这一特征才使“兔子”保持了兔子跳脱的活跃,而没有陷入“跑,还是不跑”的哈姆雷特式的行动麻痹症。
兔子的“跑”既令人同情又使人憎恶。从小说标题中的“跑”所含的祈使语气看,厄普代克的态度是偏于同情的,但他同时也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兔子”不负责任的逃离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有些评论者因此而批评厄普代克在这一人物的塑造上缺乏一致的情感和道德视角。参见DonaldJ.Greiner,第51页。这种批评实际上是要求作者对其笔下人物的行为作出公开的道德评判。厄普代克显然不想肩负说教家的责任,他认为文学中需要有“某种必要的含糊”,并且声称“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比生活更清晰”。转引自DonaldJ.Greiner,第48页。他非但不愿消除这种“必要的含糊”,而且还力图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含糊。事实上,他的作品多带有一种“是的,但是”这样的调子。HaroldBloom,ed,Twentieth�睠enturyAmericanLiteratureVol.7(NewYork:ChelseaHousePublishers,1988),p.4005.厄普代克的真正意图也许在于表现人物在冲突中的两难困境以及展现困境的复杂性。他在塑造“兔子”这一人物上的思想便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做一个人意味着要处于一种紧张情形,处于一种辩证的情形。一个完全适应环境的人根本就算不上人——不过是穿了衣服的动物罢了。”转引自DilvoI.Ristoff,Updike’sAmerica:ThePresenceofContemporaryAmericanHistoryinJohnUpdike’sRabbitTrilogy(NewYork:PeterLang,1988),p.4。
“兔子”的困境反映了美国小镇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矛盾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兔子”的“跑”实际上并非厄普代克所鼓励的走出困境的办法,否则他就不会让“兔子”反反复复地跑了又回来。如果把“跑”看作是力图摆脱困境的一种努力,那么这种努力实际上是失败的:“兔子”屡屡逃跑,但却没有方向和归宿。厄普代克的“含糊”里是否含有这样一种意味,即所谓走出困境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终归徒劳的幻念,因为在困境中无论怎样选择都将导致代价的付出(这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在困境的前提下,这种代价的大小往往难以估算),从而消解了选择的功利意义?如此,“兔子”的“跑”便有了一层存在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厄普代克也确实受到过存在主义,尤其是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影响。见JudieNewman,MacmillanModernNovelists:JohnUpdike(MacmillanPublishersLtd.,1988),p.80。若将这部小说置于其写作及出版的时间背景中看,“兔子”不安分的“跑”对于艾森豪威尔治下的50年代的平和保守社会则是颇具刺激性的,这也是小说在当时造成震动的一方面原因。
这部小说中的性描写是其震动效应的另一方面的原因。美国《时代》周刊当时曾指责书中的性描写“过于露骨”,“趣味低俗”。文学中对性的描写的确是个敏感问题,且争议由来已久,其复杂性非三言两语可以道明。总的说来,文学既是以探究人性为己任的,对性也就没必要讳莫如深。仅以性描写之程度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低级的色情文学,似乎更多是道德批判而非文学批评。以历史的态度看,读者对一部作品中的性描写的反应也受时代及观念变化的影响。因而文学批评的眼光在此问题上有必要多一些宽容。归根到底,要看性描写是否伤害了作品。就《兔子,跑吧》这部小说而言,性描写是表现小说主题的重要内容。性,除了满足感官愉悦的需求外,还有缓解紧张、消释焦虑的功能,“兔子”对性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属于后者之情形。对他来说,婚姻以外的性是一种安慰,或多或少地补偿了他的失败感。在他不擅思考而敏于直觉的头脑中,其隐约混沌的精神追求——“它”(it),只有诉诸感官时才显得较为清晰。性体验中的流动润畅在他心理上唤起的是一种挣脱束缚的自由感。然而,性最终并不能将他引渡到精神得以慰藉的境界,相反,它加深了他内心的负罪感、堕落感和失败感。性,强化了“兔子”的困境。厄普代克通过性描写展现了非出于情爱的性之空虚和无谓耗费,暗示性之于精神追求其实是一种荒唐的途径。随着这部小说不断增加的声誉,大多数评论者将厄普代克看作是一位以开放态度描写性的严肃文学作家。在他后来出版的《夫妇们》(Couples,1968)和《兔子富了》(RabbitIsRich,1981)中,性描写更是狂放无忌,但这些描写依然是他对美国中产阶级婚姻及性道德所作的细微观察。
《兔子,跑吧》的结尾是开放式的,此后,厄普代克几乎每隔10年推出一部“兔子”小说,分别是《兔子归来》(RabbitRedux,1971)、《兔子富了》和《兔子歇了》(RabbitatRest,1990)。厄普代克在“兔子系列”小说中将“兔子”的个人及其家庭生活置于包罗万象的社会辐射之下,以细腻写实的笔调描绘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图景,展示了灵与肉、个人与社会以及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探讨了婚姻、家庭、性道德、宗教、种族意识、时间、死亡、吸毒、科技发展、能源消耗等诸多问题。“兔子系列”的丰富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自50年代以来的40年历史变迁。厄普代克曾说过:“在我的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中有着比历史书更多的历史。”转引自Greiner,第50页。除本文以上提到的之外,厄普代克的主要长篇小说还有《一个月的星期天》(AMonthofSundays,1975)、《政变》(TheCoup,1978)、《伊斯特威克的女巫》(TheWitchesofEastwick,1984)、《巴西》(Brazil,1994)、《圣洁百合》(IntheBeautyoftheLilies,1996)和《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等。
大多数评论者认为厄普代克是一位艺术风格卓越的小说家,但也有人认为厄普代克的作品缺乏深刻的主题,思想内涵肤浅。有位评论者曾这样评说:“他〔厄普代克〕常常以一种表面的东西令人目眩,让人想起7月4日的国庆焰花——有火花但没有热力,有光但不能照明;是一种奇妙的娱乐,但其本身却非奇妙之物。”引自PhilipCorwin,“Oh,WhattheHex”,见HaroldBloom,第4010页。如此评语虽然说得巧妙,但却有失中肯。厄普代克的小说固然并非尽皆深刻之作,但他那些被认为写得好的作品不但在风格上卓尔不群,而且在题材上也显示了对人生及现实社会中重大问题的热切关注。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马人》就是这样一部杰作(tourdeforce)。
二
《马人》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但这是一部极富情感力度的作品,厄普代克在小说中将这份父爱写得沉蕴有致,富有悲剧的深度。
小说主人公乔治·卡德威尔在家乡小镇的一所中学教生物。过了中年之后,他身心疲惫,觉得自己的生活碌碌无为。教书对他来说已不能成为精神寄托,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在他的学生身上不留痕迹,徒然消耗着他的生命。靠着微薄的薪水他要维持一个三代之家,供养他的岳父、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儿子彼得,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颇为窘迫。更糟的是,他因偶然撞见一位女同事头发零乱、衣衫不整地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情形而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比起《兔子,跑吧》中的“兔子”哈利,卡德威尔的失败感更为强烈,他甚至把自己看作是行走的废物。我们可以看出,他承受的生活压力和责任比兔子要沉重得多,但他却没有像兔子那样逃避责任。从一个方面看,卡德威尔与兔子形成了一种对比。事实上,厄普代克在构思《马人》时的确是想把这部小说写成《兔子,跑吧》的对照篇,也就是说,他想通过这两部小说来体现对待生活的两种不同态度和方式。在1990年的一期《纽约时代书评》中厄普代克作过这样的解释:“一种是兔子的逃避方式——本能的、不假思索的、恐惧的……另一种是以马的方式对待生活,上套拉车,直到倒下为止。于是便有了《马人》。”转引自TomVerde,第154页。
“兔子”之于安斯特朗是一种隐喻,而在这部小说中,“马”的意象则实实在在地与主人公的现实形象合二为一了;卡德威尔在小说中同时也是半马半人的客戎(Chiron)。客戎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形象,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马,他博学多智,是希腊年轻英雄们的导师。据神话所载,客戎在一群马人(Centaur)的一次混战中被一枝毒箭射中,箭伤使他痛苦难忍,生不如死。但由于是神,他无法死去,于是他请求主神宙斯,允许他以自己的死亡换取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宙斯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将他变为一颗星星。厄普代克在《马人》这部小说里运用了客戎的神话故事,并将它融于现实生活的叙述之中。小说第一章中,主人公是以卡德威尔和客戎混为一体的重合形象出现的。一开始的情形是,卡德威尔在他的生物课上被学生的一枝用钢钎制成的箭射中脚踝。这段场景虽然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但情节本身实质上是客戎故事的翻版。卡德威尔所受的箭伤在这里是一个暗喻,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实际是他在生活中的痛苦。小说中对他的痛苦感受的描写暗示了这一点:“他希望私下独自体验他的痛苦,测出它的力度,估算它的持续时间,审视它的结构。”JohnUpdike,TheCentaur(FawcettPublications,Inc.,1962),p.9.后面出自该作品的引文均据此版本,并注页码于文内。
伴随痛苦而来的是死亡冲动意识。像受伤的客戎一样,卡德威尔也想摆脱痛苦的折磨,因而死亡的念头常常缠绕着他。当他给学生讲解宇宙的形成时,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带一长串零的数字,随后对学生说“它们让我想起死亡”(第34页)。痛苦和死亡意识的心理暗示使卡德威尔怀疑自己得了癌症。这种疑病症与其说是恐惧所致,不如说是他的死亡希求心理的折射。当他在X光检查后得知自己并无绝症时,他待死的心理不仅没有释然反而更添了一层痛苦。痛苦在于他无法在想象的自然死亡中得到解脱,而只有继续活着履行他的责任,忍受他那失败生活的痛苦。
小说的结尾一句是“客戎接受了死亡”(第222页)。这句话容易给人留下卡德威尔最终选择了自杀的印象。表面看,这种推断似乎符合逻辑:既然客戎是自愿受死,卡德威尔(同时也是客戎)的结局自然也应如此。然而,这样理解便取消了厄普代克在其刻意经营的模糊中所要表现的内涵深度。客戎求死的确是从根本上为了解除自身不堪忍受的痛苦,但客戎神话的意义却在于客戎的死换取了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卡德威尔与客戎重叠的形象的意义也在于此。卡德威尔若是自杀便意味着放弃责任,他的死不会有益于儿子彼得将来的发展。而小说告诉我们的是,彼得长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儿时的艺术梦想,他终于从偏僻小镇到了曼哈顿,成为一个二流的抽象派画家。小说结尾描写的这段情形发生于1947年,当时彼得才13岁,正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深以儿子为自豪的卡德威尔不可能就此自杀而撇下彼得不管。从客戎神话意义上理解,卡德威尔所接受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死亡,它意味的是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在第一章里描写的生物课情景中,卡德威尔对学生说:“虽然每个细胞都具有潜在的永恒生命,但由于个体细胞自愿在一个有序的细胞群组织里担当某个专门功能,它于是进入了一个有损害性的环境,过度的劳损最终使它衰竭而死。它的死是一种牺牲,是为了整体的利益。”(第37页)这番话也可以说是卡德威尔的生活写照。自我牺牲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放弃解脱痛苦的愿望,继续像老马拉车那样承受生活的重负,“直至倒下为止”。彼得在回忆中说:“他(卡德威尔)的上半身我看不见,我最熟悉的是他的腿”(第201页)。小说将近结尾时,客戎独自在大雪中走向抛锚的别克车。这里的描写像小说第一章一样,仍然是神话与现实交融在一起,人物是神话中的,但大雪和别克车却是现实中的景和物。这种叙述里既有事实描述又有隐喻。事实是卡德威尔试图重新发动别克车,以便返回学校(很难将这一举动与自杀联系起来);含有隐喻的是那辆老别克。这辆1936年的旧别克在小说中屡出故障,弄得卡德威尔父子在回家的路上困顿了三天,它所象征的是卡德威尔失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客戎形象中的卡德威尔走向那辆老别克便意味着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自我牺牲使卡德威尔带有悲剧英雄的色彩,在他身上似乎有着基督的影子。英文原文中客戎Chiron与基督Christ在词形上的相似也许多少带有这样一点暗示意味。
基督教思想背景下的人生观是小说故事层面下所要表现的深层主题。厄普代克在小说卷首引了一段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Barth)的话:“天之于人是不可感知的创造,地之于人是可感知的创造,人便是天与地分界之间的造物。”在象征意义上说,客戎半人半马的双重属性代表了人性中的两端。人既是世俗的,受时空制约,但又向往和追求无限和永恒的境界,人类对神的崇拜即是这种向往和追求的体现。人创造了神话,试图使“可感知的”与“不可感知的”得以相接。厄普代克通过将神话与现实的融合,表现了世俗生活背后的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人类犯下原罪前(prelapsarian)的天真未染的世界,是一个处处回响着隐喻的世界。然而,这一世界正在失落。有论者指出,这部小说是一曲缅怀奥林匹斯众神时代的抒情挽歌。参见JamesM.Mellard,“TheNovelasLyricElegy:TheModeofUpdike’sTheCentaur”。见HaroldBloom所编ModernCriticalViews:JohnUpdike(NewYork:ChealseaHousePublishers,1987),第101页。奥林匹斯神庙在小说中成了小镇奥林格,宙斯成了卡德威尔所在中学的校长吉摩尔曼。神性的衰落与堕落有关。在小说中,“堕落”是通过三代卡德威尔的职业变化来暗示的:从牧师(卡德威尔的父亲)、教师(卡德威尔)到艺术家(彼得),用彼得的话来说,是一种“经典性的堕落”(第201页)。随着上帝受到怀疑,神学被理性的科学取代,而科学并不能最终使人的灵与肉归于统一。人失去了上帝,又无法在理性中找到生存的安慰,于是便求助于自由的想象力去重建精神家园。艺术象征着对永恒的关怀。少年时代的彼得是荷兰画家弗美尔(Vermeer)的崇拜者,他一直梦想在美术馆亲眼一睹画家的原作,因为最令他神往的是画布上颜料的裂隙中凝固的时光。然而,成年后的艺术家彼得并没有在自己的抽象画艺术中得到精神超越的满足。在曼哈顿的一个小阁楼里,彼得面对躺在身边半睡半醒的黑种情人自言自语道:“我父亲献出自己的一生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切吗?”(第201页)。彼得的问题在于他以艺术否定世俗世界,他在艺术家的精神优越感中失落了他的少年时代。他的生活出现了断裂,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他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怅惘和失落使他转向记忆去寻找慰藉,在追忆的过程中,他开始认识到父亲为他所作的自我牺牲。小说中发生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彼得的回忆来展现的。作为艺术家,彼得试图在记忆中凝固1947年冬天他和父亲共同经历的三天时光。在回忆中,他产生了负疚感,同时也发现了爱,而追忆便成了他的“赎罪”方式,从这里他开始找到了他个人生活的意义。在他追忆的眼光中,故乡奥林格显出了奥林匹斯永恒的神性光芒。
......
侯毅凌
用户评价
这本书真正击中我的,是它对“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熔炉中如何被缓慢消磨和异化的描绘。它没有采用煽情的手法去控诉外部世界的压力,而是通过一系列极其生活化、却又处处透露着不安和失序的场景,展现了内在信念如何一步步被日常琐碎和人性弱点所侵蚀的过程。那种缓慢的、渐进式的精神坍塌,比突如其来的崩溃更令人心寒。特别是对于主人公在特定群体中试图保持“纯粹性”的努力,那种近乎徒劳的挣扎,让人感同身受。作者似乎在探讨一个核心悖论:当一个人试图以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和度过生活时,他与世界的摩擦力会变得有多大?这种对个体精神洁癖的细致描摹,让我想起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遗忘的、试图坚守原则却最终被时代洪流裹挟的知识分子。文字的节奏感很奇特,有时平稳得像催眠曲,突然间又会因为一个突兀的、极具冲击力的场景而猛然惊醒。这是一种老派的、对文学形式本身极度尊重的写作方式,它不迎合快节奏的时代,而是要求你沉浸其中,与之共同呼吸。
评分我欣赏这部作品中对“家庭”和“传承”这一母题近乎哥特式的处理。它不是对传统家庭温馨画面的歌颂,反而将其描绘成一个充满着未言明协议、世代相传的心理负担和隐秘欲望的迷宫。那种空气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关于上一代人未竟事业和未被解决的矛盾,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下一代,迫使他们重复着相似的错误或进行着徒劳的反抗。书中的许多对话,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藏着巨大的张力,是那种只有在极度亲密的关系中才会出现的、不需言明的理解与伤害。它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氛围,让人感到无论角色如何挣扎,似乎都无法真正逃离他们所出生的那个文化与阶级的轨道。这种宿命感,在作者冷静的叙述下显得尤为有力,丝毫没有流于俗套的感伤。这本小说探讨了“成为谁”的负担,以及如何在既定的框架内,试图雕刻出属于自己的真实轮廓,即使那轮廓注定是残缺不全的。
评分初次接触这部作品时,我被它那种近乎巴洛克式的繁复和对细节的近乎偏执的描摹所吸引。文字的密度极高,每一句话都仿佛经过了反复的锤炼,蕴含着多重含义,需要你放慢呼吸,逐字逐句地去咀嚼、去体会那种潜藏在表层对话和场景描写之下的暗流涌动。那种描绘的质感,让我仿佛能触摸到书中的每一个物件,闻到空气中弥漫的尘土和旧皮革的气味。作者对于特定社会阶层和知识精英群体内部微妙的权力动态和情感张力的刻画,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那些看似礼貌疏离的互动背后,隐藏着多么复杂而微妙的嫉妒、渴望和自我欺骗,一切都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这种对内在世界的深度挖掘,也带来了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比他们的行为更引人注目,以至于故事的主线有时显得松散而晦涩。这本书更像是一部心理学的案例研究,被包裹在精美绝伦的文学外衣之下,它要求读者具备相当的耐心和对人类心理复杂性的接受度,才能真正领会到其艺术价值所在。它不是为了迎合大众的阅读习惯而生的,它存在于一个更孤独、更内省的文学维度中。
评分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的“距离感”,它营造了一种既清晰可见又无法触及的叙事空间。作者似乎站在一个极高的维度上审视着他笔下的人物,用一种近乎人类学家般的冷静和好奇心去解剖他们的行为逻辑和情感模式。这种超然的视角,使得原本可能沦为肥皂剧的情节,获得了哲学思辨的深度。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在处理时间线上的手法,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并不构成严格的线性关系,而是以一种更接近记忆和潜意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象征意义。它不是在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在构建一个关于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精神图谱的复杂模型。阅读时,我常常需要停下来,不是因为我没看懂情节,而是因为我需要时间去消化其中蕴含的文化典故和微妙的反讽意味。它考验的不是读者的理解力,而是读者的“文化耐心”——愿意投入时间去解码一个精心构建的、拒绝轻易示人的复杂世界。它是一部需要被反复阅读才能逐步揭开其多层意蕴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简直是一场对现代社会虚伪面具的无情揭露,它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剖开了那些我们习惯性回避的、深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道德困境与人性挣扎。作者的笔触如同手术刀般精准而冰冷,毫不留情地将人物置于极端的情境中,逼迫他们面对那些关于信仰、欲望和责任的终极拷问。我尤其欣赏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知识分子式的焦虑感,它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悲观,而是源于对真理的执着探寻后,所感受到的世界本身的荒谬与失衡。阅读的过程就像是一场漫长的、令人疲惫的内心对话,你不断地被书中角色的选择所挑战,质疑自己平日里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价值观。叙事结构上的精妙设计,使得信息的碎片化处理反而增强了整体的张力,迫使读者必须主动参与到意义的构建中去,而不是被动接受一个既定的结论。这种叙事上的“不友好”,恰恰是其高明之处,它拒绝了任何形式的廉价安慰,留给我们的,是久久不能散去的、关于“人究竟为何为人”的沉重回响。读完之后,我发现自己看待周围事物的眼光都变得锐利而审慎了许多,这绝不是一本可以轻松翻阅的消遣读物,而是一次深刻的智识洗礼。
评分人人都爱看末日后的故事,因为我们暗暗盼望成为幸存者,盼望一切能重头再来。
评分早上有了一堆放书,本本马人行。
评分书很好,京东快递一如既往的好。
评分精装书轻型纸,还掉纸屑,定价偏高,慎入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叙事学是文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本成果所开展的“空间叙事研究”则是此领域中新的理论方向,是目前叙事学研究中最有发展前景、最具学术潜力的领域之一。其研究目的,是对传统叙事学重视不够甚至严重忽视的叙事的空间维度或叙事作品的空间元素进行系统考察,进而对叙事与空间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属于文艺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对于叙事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对于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具有较为重大的价值。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评分书很好,京东快递一如既往的好。
评分购物首选京东,宅男不用出户!
评分非常习惯在京东购物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夫妇们(厄普代克作品) [Coupl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9819/59def93bN98ebc420.jpg)
![厄普代克作品:兔子,跑吧 [Rabbit,Ru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9827/59ba4c55Nd2817548.jpg)
![兔子歇了(厄普代克作品) [Rabbit at Res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9841/59def0e2N4670eed8.jpg)

![毛姆文集:面纱 [The Painted Veil]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1621/59a53832N6e43a1b1.jpg)
![秒速5厘米(10周年纪念版)(套装共2册) [秒速5センチメートル]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2385/59bf62a0N815b13e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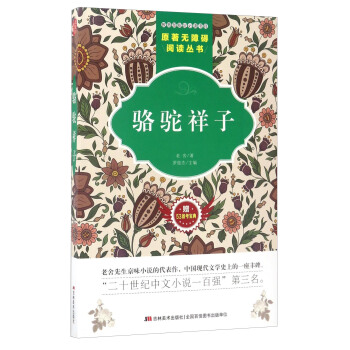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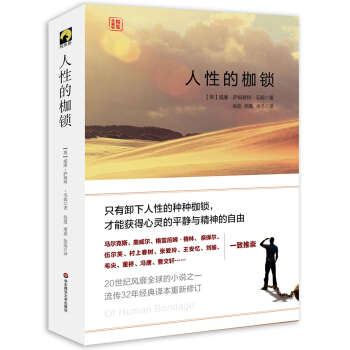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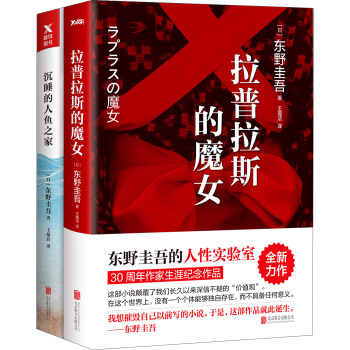


![所有明亮的地方 [ALL THE BRIGHT PLAC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4983/5955a87dN689495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