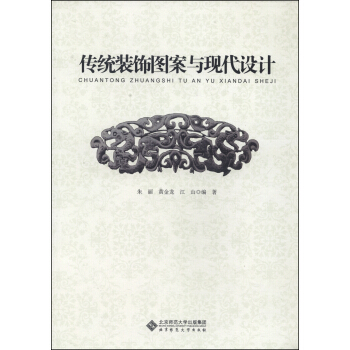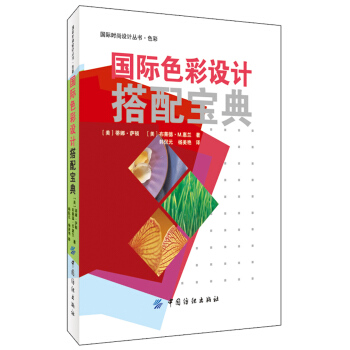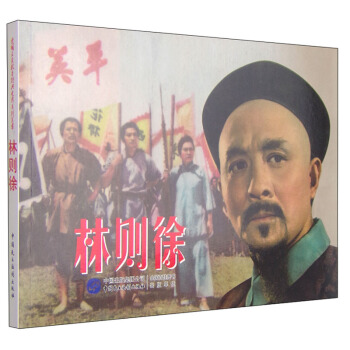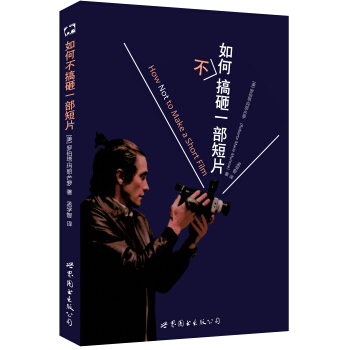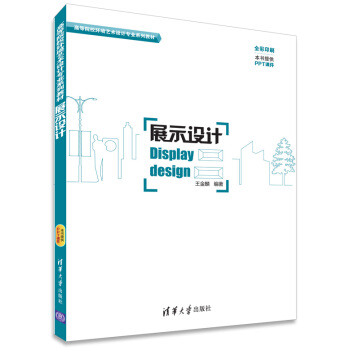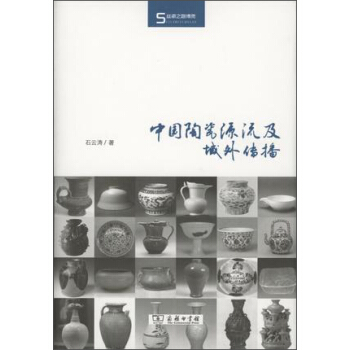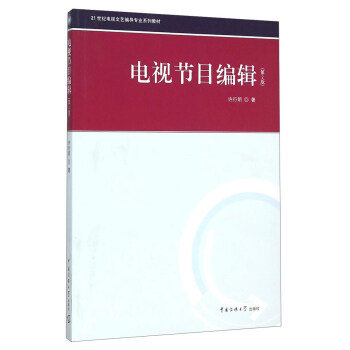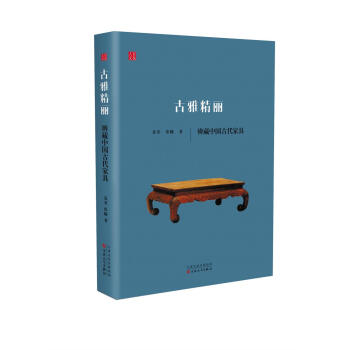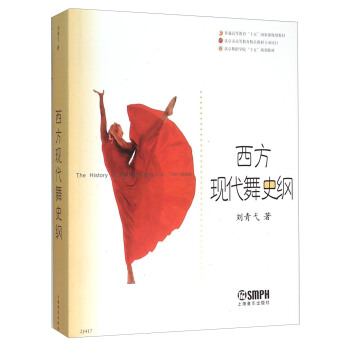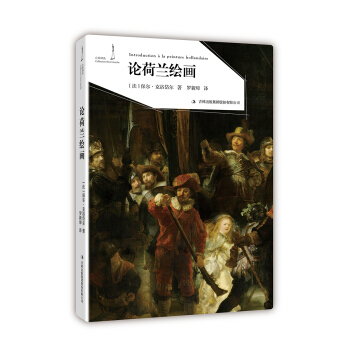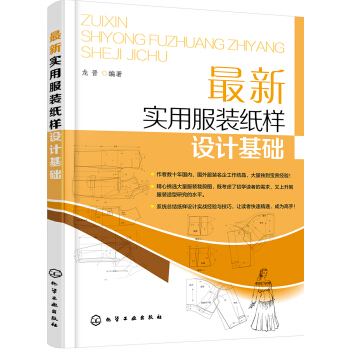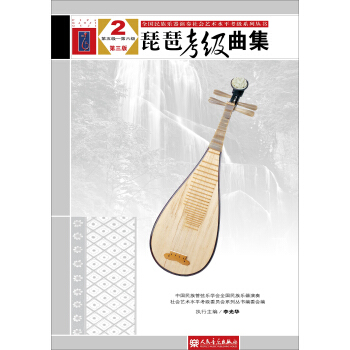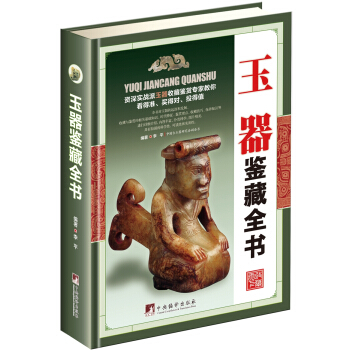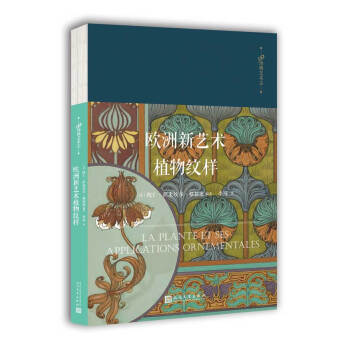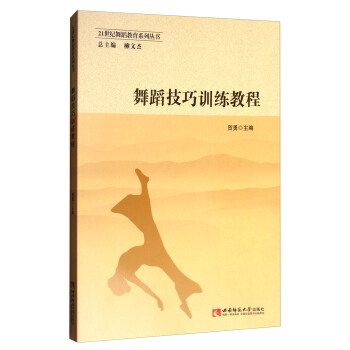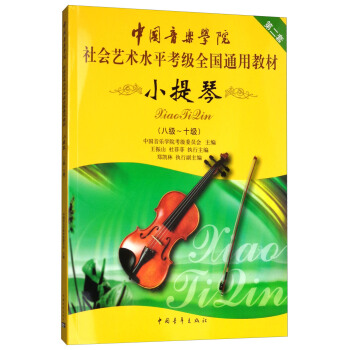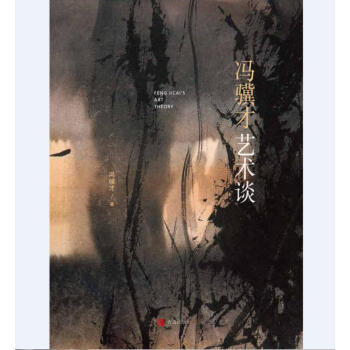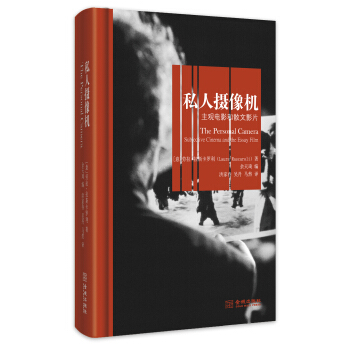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私人摄像机》的贡献在于全面地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的主观视角非虚构电影,是一次较为系统的美学整理。作者谈及的主观视角非虚构电影,涉及实验纪录片、艺术电影和前卫录像,既梳理了这类电影的哲学背景和社会历史环境,也分析了理论根基,同时为这个范围划分了子类别。
内容简介
《私人摄像机》关注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领域:散文电影。第一部分从理论、实践、美学的角度分析散文电影;第二部分关注同源主观第一人称非虚构电影:日记电影、游记、札记和自画像。这些是关于思考、调查以及自我反思的电影形式。导演从镜头后面走到了镜头前,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陈述、分享自我。这种作者式、实验、激进式的散文电影属于先锋政治电影家族,并且呼应了我们今天需要的更即兴的自传式私人表达形式。本书涉及的导演包括戈达尔、克利斯·马克,哈伦·法罗基、帕索里尼、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乔纳斯·米克斯,阿涅斯·瓦尔达等。作者试图对电影体验、作者电影和观众、电影与真实以及主体性给予更新锐的解读。
作者简介
劳拉·拉斯卡罗利(Laura Rascarol),意大利裔,作家,目前任职于爱尔兰国立大学。主要电影论着有:《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美丽人生〉之前,罗伯·贝尼尼电影里的喜剧和悲剧》等。
Laura Rascaroli is Senior Lecturer and co-director of Film and Screen Media at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Ireland. With Ewa Mazierska, she authored From Moscow to Madrid: European Cities, Postmodern Cinema (2003), The Cinema of Nanni Moretti: Dreams and Diaries (2004), and Crossing New Europe: Postmodern Travel and the European Road Movie (2006). She also edited the volumes The Cause of Cosmopolitanism: Dispositions, Models, Transformations (2010), with Patrick O’Donovan, and Antonioni: Centenary Essays (2011), with John David Rhodes. She is general editor of Alphaville: Journal of Film and Screen Media. Her monograph The Personal Camera: Subjective Cinema and the Essay Film was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9.
余天琦,纪录片制作人、学者。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校区电影与媒体研究讲师,剑桥大学社会学硕士、西敏寺大学电影研究博士 。研究纪录片、第一人称非虚构影像、家庭影像、中国电影,并发表国际期刊文章。编有《China’s iGeneration: Cinema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英Bloomsbury出版,2014) 。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编委成员。影像作品包括《梦寻深圳》《关于家的记忆》。
洪家春,北京大学学士,香港传播学硕士,美国传媒博士在读,研究新媒体、纪录片创作和纪录片产业。原中央电视台编导、纪录片导演,代表作《在别处》《迷失798》《爱戏如梦》。
马然,女,目前任教于日本国立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的Global-30英文课程,授课范围以电影研究和文化研究为主。个人研究兴趣包括电影节研究和亚洲独立电影。
吴丹, 1985年出生,在英国获得电影研究硕士学位,专攻香港“后九七”怀旧电影。2012年至今就读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电影研究专业。博士课题关注中国独立电影的流通以及中国独立电影节在独立电影流通中承担的角色及作用。
目录
1 概论:主观电影和镜头的我/眼睛
37 第一部分|散文电影
38 第一章 散文电影:问题、定义和文本承诺
82 第二章 散文电影中的元批判画外音:哈伦?法罗基,资料影片和作为观者的散文家
122 第三章 经验的博物馆化:克利斯?马克存在于档案馆、博物馆与数据库之间的数字化主体
164 第四章 表演与商议:让-吕克?戈达尔饰演让-吕克?戈达尔
209 第二部分|第一人称电影
210 第五章 第一人称电影:历史、理论与实践
227 第六章 日记电影: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灵魂之声》与时间之感
294 第七章 笔记本电影: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与无法被制作的电影
350 第八章 自画像电影: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凝视
388 编后记
394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概论:主观电影和镜头的我/眼睛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介于纪录片、艺术电影和先锋电影之间的一种电影实践,最适宜的定义是主观的、第一人称的散文式电影。但此貌似简单的定义牵涉一系列理论和术语问题。无疑,“散文电影”这一表述越来越通用,常见于关于非虚构电影的影评和学术文章。这个词尽管广为使用,涵义却有诸多含混之处,常用来指代令人困惑的各种影片和电影形式:可以用来描述以下任何一部影片,从克利斯·马克(ChrisMarker)《久美子的秘密》(LeMystèreKoumiko,1965)到迈克尔·摩尔(MichaelMoore)的《华氏911》(Fahrenheit9/11,2004),从吉加?维尔托夫(DzigaVertov)《持摄影机的人》[Chelovekskino-apparatom(ManwithaMovieCamera),1929]到埃罗尔·莫里斯(ErrolMorris)《细细的蓝线》[LasHurdes(TheThinBlueLine),1988],从刘易斯?布努埃尔(LuisBu·uel)《无粮的土地》(LandWithoutBread,1933)到阿涅斯?瓦尔达(AgnèsVarda)《我与拾穗者》[LesGlaneursetlaglaneuse(TheGleanersandI),2000],从奥逊?威尔斯(OrsonWelles)《赝品》[Véritésetmensonges(FForFake),1974]到摩根·斯普尔洛克(MorganSpurlock)《超码的我》(SuperSizeMe,2004)。从这种扩大化使用中,可以得出一个印象,散文几乎是纪录片的代名词。在日渐复杂的非虚构影片领域,纪录片和剧情片正以富有挑战的方式进行融合,沟通的信源(sourceofthecommunication)也日渐明显,很难找到一个词来指认这个领域。关于散文电影概念的批判性实践可能正是受了这种困难的鼓励。但它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它指出一个事实,即所有纪录片,甚至那些看起来最客观公正的片子,也是建立在特定观点之上,并且宣称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换句话说,所有的非虚构影片都是“有观点”的影片。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要定义影片中的散文式表达的话,这种批判性实践则未必有帮助,因为这种表达既毋庸置疑又模糊不清难以定位。
与这种批判性实践相反,本书使用一个窄义的定义,来探讨为什么我们在观看某些影片时会冒出这样的问题,比如阿伦·雷乃(AlainResnais)的《夜与雾》[Nuitetbrouillard(NightandFog),1955],克利斯·马克的《西伯利亚来信》[LettredeSibérie(LetterfromSiberia),1957],维尔托夫小组(高兰和戈达尔等人成立的)的《此处和彼处》[Icietailleurs(HereandElsewhere),1976],哈伦·法罗基《工人离开工厂》[ArbeiterverlassendieFabrik(WorkersLeavingtheFactory),1995],亚历山大·索科洛夫(AleksandrSokurov)的《休伯特?罗伯特的幸福一生》[HubertRobert.Schastlivanyazhizn(HubertRobert,AFortunateLife),1996],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Godard)的《电影史》[Histoire(s)ducinéma,1997—1998]和汤姆·安德森(ThomAndersen)的《洛杉矶自动放映》(LosAngelesPlaysItself,2003),只要想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这些相关片名,作为观众我们感觉像在看一篇篇散文,电影版的文学散文,它不同于纪录片、电影诗歌、自传电影、音画书信或实验电影。
“散文电影”这一说法的另一常用方式,是作为投入的公开政治电影的直接代名词。既可以指主流批判性纪录片,如迈克尔?摩尔的作品,也可以指认同少数族裔,流散人群或边缘主体的另类电影和视频制作。这似乎也不出乎意料,传统上表达个人意见的影片基本局隅于政治电影——毕竟说到第一人称“我”,首先是一种自我觉醒和自我肯定的政治行动。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成为现代散文电影的重要元素。不过,我相信对散文电影的准确考虑包含比严格意义的政治更多的东西。因此,考虑到现在的批判性实践,我对此词使用更广义。此外,在本书中我不仅谈论散文电影,还谈论其他同源但形式不同的主观电影:日记电影、游记、笔记本和自画像。
这些被归为一类的电影制作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约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要么是随兴暂时的视频,要么是为影院上映或电视播出而做,是一批特别的形式多样的互相矛盾的异端电影。将这些电影和视频归为一类,富有挑战且有问题——想想那些导演的名字就知道:让-吕克·戈达尔、克利斯·马克、哈伦·法罗基、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PaoloPasolini)、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Antonioni)、德里克·贾曼(DerekJarman)、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Fellini)、维姆·文德斯(WimWenders)、乔纳斯?米克斯(JonasMekas)、让·玛里·斯特劳布(Jean-MarieStraub)和达妮埃尔·于埃(DanièleHuillet)、依冯·瑞娜(YvonneRainer)、尚塔尔·阿克曼(ChantalAkerman)、埃德·平卡斯(EdPincus)、帕特里克·基勒(PatrickKeiller)、阿涅斯·瓦尔达、沃纳·赫尔佐格(WernerHerzog)、米歇尔·西特伦(MichelleCitron)和罗斯·麦克艾维(RossMcElwee)。看起来,只有离经叛道(在技术形式、主题内容、美学价值、叙述结构和制作发行上)是本文探讨的所有影片以及其他类似影片的唯一共通之处。但一方面我们应该拒绝把散文电影过分理论化并定型为一种电影类型,而另一方面,把这些电影归置在一起也是一种分类行为,即使不能成为一致的类型,也至少表明存在一个领域,一个范畴。
尽管这些电影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属于同一类型,但它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元语言,自传式和反思式,它们都确立了一个文本之外的明确的作者形象作为源点和恒定的参照;都表达了强烈的主观的个人意见;都通过对观众的直接演讲或质询(interpellation)建立了特别的传播结构。虽然,它们在演讲、清晰地表达作者身份、叙述和沟通的方式上彼此差别很大,但是我坚信,找到散文电影借以表达主观观点和打造观众身份的普遍性修辞结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理解它们内在的动力以及如何吸引观众也必不可少。
纪录片和沟通的主观性
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让-吕克·戈达尔,1985:181—182)
尽管这些电影共属于电影制作的同一阈限区域(liminalzone)(但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关),在那里虚构和非虚构,实验性和主流电影混杂交融,但它们都是纪录片,或者倾向于纪录片——至少在这个词最广义和较少限制的涵义上。在过去十年,由于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概念的演变,以及越来越模糊的非虚构实践的出现和在发行和观众反映上的成功,学者们开始质疑之前认为纪录片是绝对客观的定见。正如比尔·尼科尔斯(BillNichols)所说:“传统上,纪录片这个词代表圆满,完成和关于社会世界及其机制的知识、事实和解释。但是最近,纪录片已经开始代表未完成和不确定,记忆和印象,个人影像及其主观建构。”(尼科尔斯,1994:1)这种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趋势,至少在个人的散文式纪录片上是确定无疑的(可能不适用于所有非虚构制作,它们当中很多依然保持传统方式)。这种趋势至少可以从历史和理论两种方式来理解,彼此并不一定矛盾:一方面,它是社会和艺术领域后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是欧洲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电影实践的延续和演变。
很明显,主观性和自传走上前台是今天的大势所趋:只要想想个人叙述、回忆录和日记在文学和其他艺术上的流行:“出版商和批评家都同意,不论好坏,生命书写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当代作者生活细节的兴趣,正在经历一个显着的繁荣。”[凯特·道格拉斯(KateDouglas),2001:806]主体性和自传正成为那些在全球广受好评和获得商业成功的书的根源,比如弗兰克?迈考特(FrankMcCourt)的《安杰拉的灰烬》(Angela’sAshes),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McBride)《水的颜色》(TheColorofWater)或海伦·菲尔丁(HelenFielding)的《BJ单身日记》(BridgetJones’Diary)。
主观性和自传也是当代大众媒体的一个显着方面:我主要指互联网、蓬勃发展的第一人称博客、网上日记,以及制作“忏悔视频,电子散文和个人网页”[瑞诺夫(Renov),2004a:xi];还有电视的日益个人化,像以“老大哥”(BigBrother)开始的真人秀节目,就让观众感觉在实时观看某人的真实生活。事实上,斯特拉?布鲁兹(StellaBruzzi)提醒我们,在现在的英国电视节目里,真人秀不再被归类为娱乐,而是“事实”。他从观察式纪录片演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类型的产生说明了对传统式观察的透明度和被动性,作者声音的缺席,以及无法公开展示制作者存在的不满日益增长。”(2006:121)
这一现象在电影界也是如此。过去四十年见证了国际电影界主观非虚构影片制作的显着增加,包括迈克尔?瑞诺夫(MichaelRenov)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自传片的爆发”。(2004:xxii)这一爆发可以部分归结于新技术的扩散,尤其是数字视频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此外,还有一些更抽象的原因。在主题和哲学层面,我认为现在非虚构电影中的主观性,是人类经验在后现代和全球化的世界里日益碎片化的反映和后果,以及我们设法反映和应对这一碎片化的需求和欲望。当然,我指的是那一派认为不安全感和流动性是后现代社会普遍状况的理论。在很多当代思想家看来,在后现代性里不可能找到任何坚固的东西,我们都注定被去中心化、碎片化和“液化”。自传式叙述满足了一种希望,那就是在日益脱节、流离和分散的生活中寻找或创造团结。在后现代首次亮相之后的几年间,文学、叙事学和语言学理论都对第一人称叙述产生巨大的兴趣并非偶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自传和自我反思的叙事结构的繁荣;只要看看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Blanchot)、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Genette)、西摩?查特曼(SeymourChatman)和菲利普·勒热纳(PhilippeLejeune)的作品就知道了。
主观非虚构电影形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Lyotard)于1979年提出的元叙述的终结(利奥塔,1984),以及随之而来的后现代话语中权威的减弱,还有“客观性作为一种令人信服的社会叙事的衰落”(瑞诺夫,2004a:xvii)。客观性和权威的社会说服力的下降,在纪录电影里有着明显的后果。在这个质疑一切的时代,宏大叙述不再可信,客观性赖以存在的假设——一个恒定不变的外部视角——也变得很有问题。边缘比中心更有吸引力,随机意外替代必需和不可更改。因此,传统纪录片的权威被削弱;客观性的光环不再站得住脚;它的貌似公正和制作真实话语的能力被认为只是语言和修辞形式,要么被嘲弄(在恶搞纪录片中),要么被公开展示沟通行为信源(sourceoftheactofcommunication)的片子所取代。我会深入分析的第二种现象,其中一些导演崭露头角,使用第一人称的代名词“我”,承认自己的偏向好恶,并有意通过随机的个人意见来削弱自己的权威。很明显,这是另一种修辞手法,意在建立一种诚恳真实的话语,至少对他自己而言是如此。
前言/序言
致中国读者
《私人摄像机》最初于2009年出版于英国。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本书会获得什么样的反响,更别谈会影响多深远。这不仅仅因为我感觉这本书是为我自己而写的——关于我喜欢的主题,关于我喜欢的电影,关于为什么电影对我如此重要。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够得到一些关注,因为这是关于散文电影的第一本英文书;同时,我也知道和其他更宽泛更主流的主题、流派和电影形式相比,这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然而,由于人们可以轻松接触到新数字技术和发布平台,这个领域也处于快速的扩展中。今天,这些技术鼓励人们更个人、更主观地参与到电影中,也使得实验电影、第一人称电影和独立电影等多种电影形式有了发展的可能并在全球范围内欣赏。
这本书出版之后,阅读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幸运地收到来自于各方关于《私人摄像机》的赞扬,有讲师、学者、学生、批评家和电影人。对于这些,我深表感激。每次,我都又惊又喜:惊的是我没有预料到这本书的阅读范围如此之广,对于人们来说如此意义重大;喜的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主题有着非同一般的个人意义。因此,当我知道这本书即将出版中文版时,我感到了新的惊喜。想到这本书将要漂洋过海,离我最初写作的地方如此遥远,我就非常激动,这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设想。我非常感谢余天琦博士,她策划并促成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我也要感谢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我还要感谢你们,我的读者,感谢你们打开这本《私人摄像机》。散文电影是一种关于对话的电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也是在共享的思维领域里不同观念之间的对话。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独特的体验,为共同的反思提供一个类似聚会的地方。
劳拉·拉斯卡罗利
2013年9月16日,于科克
致谢
在此,我想对这本书做出慷慨帮助以及无私奉献的朋友、同事和学生表示衷心的感谢。读者也许并不能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贡献,但是对我来说,他们的帮助都是十分重要显着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为本书所做的一切在此无法一一赘述。我对我们之间的友谊不胜感激。
我的学生斯特凡诺·巴诗埃拉(Stefano Baschiera)、玛利亚·赫尔利(Marian Hurley)、斯特凡诺·奥德利克(Stefano Odorico)和爱丹·鲍尔(Aidan Power)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吉安卢卡·席妮丽(Gianluca Cinelli)将自己的文学自传笔记借阅于我,成为此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莎拉·库珀(Sarah Cooper)和凯瑟琳·勒普顿(Catherine Lupton)提供给我未发表的材料,帕特里克·克罗利(Patrick Crowley)帮助检查我的部分翻译,他智慧博学的回复充盈了此书语言的呈现。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电影制作公司的安捷·艾曼(Antje Ehmann)总是及时耐心地回复我各种的疑问和要求。哈伦·法罗基愿意提供他的电影剧照,雅各布布·本奇(Jacopo Benci)、萨宾·克利贝尔(Sabine Kriebel)、费得利卡·玛佐琪(Federica Mazzocchi)、卢卡·摩斯(Luca Mosso)、斯特凡诺·奥德利克和安妮塔·特里维莉(Anita Trivelli)对于选定梳理繁复的一手和二手资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卫·蒙特罗(David Montero)和我分享他的参考书目和他对于散文电影的思考。帕特里克·欧多诺曼(Patrick O’Donovan)、约翰·大卫·罗德兹(John David Rhodes)、安妮塔·特里维莉和迈克尔·威特(Michael Witt)欣然同意阅读手稿部分,并给予极其珍贵、深刻和值得借鉴的反馈。
感谢弗朗西斯科·卡塞蒂(Francesco Casetti)、温弗里德·鲍雷特(Winfried Pauleit)、约翰·大卫·罗德兹和波琳·斯莫尔(Pauline Small)邀请我阶段性地展示我的研究成果,让我在大众面前有机会不断地去构思,我十分享受他们的陪伴。我会永远感激弗朗西斯科·卡塞蒂,是他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教会我什么是电影并在二十年后重新启发我。他对于我在电影认知上的影响难以估量。
我还要感谢桂竹香出版社(Wallflower Press)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约拉姆·阿隆(Yoram Allon)为此付出的经历、热忱和他优秀的工作能力以及对此书的信任。还有此系列丛书的编辑布莱恩温斯顿,谢谢他慷慨地审阅我的手稿。
第一章节的一个版本《散文电影:问题、定义和文本承诺》(The essay film:problems,definitions,textual commitments)已经在期刊《结构》(Framework)四十九卷第二期发表。德雷克·斯图特玛(Drake Stutesma)和已故的保罗·阿瑟(Paul Arthur)对于此文极具洞察力的观察,促使我进一步精炼锐化我的论点。第四章的一部分以《散文电影(中)的表演:〈我们的音乐〉戈达尔扮演戈达尔》(Performance in and of the essay film:Jean-Luc Godard plays Jean-Luc Godard in Notre musique)为题发表在期刊《法国电影研究》 (French Cinema)第九卷第一期,我在此特别想对菲尔·帕里(Phil Powrie)和 迈克尔·威特致谢,谢谢他们的鼓励。对于此书,我得到了科克大学社会科学凯尔特研究艺术学院的研究出版基金(Research Publication Fund of the College of Arts,Celtic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College Cork)的慷慨相助。
我还要将一个特别充满爱意的感谢给我的家人,特别是一直支持我的汤姆和爱丽丝,感谢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我孤注于此书的那段时间。还有我的父母,感谢他们一直信任我,胜过我对于我自己的信任。还有诺拉(Norah,1928—2008),接受我,尊重我,并且我想,爱我。
此书最好的那些章节献给让-吕克,并且缅怀米开朗基罗:非常感谢,无限敬意。谢谢你那令世人震惊的幻象《致命的美丽》(fatale beauté)。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简直是一场智力上的探险。它涉及的概念和理论非常扎实,但作者的叙事功力极高,总能用一种既学术又充满个人魅力的语言把复杂的观点阐述清楚。我记得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了早期实验电影如何试图颠覆传统的观看习惯,那段描述简直是电影史的微缩景观。作者引用了大量不太为人知的影评和艺术宣言,将这些零散的碎片巧妙地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理论网。我必须承认,有些地方我需要放慢速度,反复咀嚼那些句子,因为它们信息密度实在太高了。但这种挑战感恰恰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它不喂给你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你去主动思考和构建自己的理解框架。对于那些已经有一定电影知识储备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提升认知边界的利器,它拓宽了我对“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认知边界。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启发在于,它挑战了我们对“记录”和“真实”的固有观念。作者以一种极其狡黠和多义的方式,解构了影像的客观性神话。我以前总觉得,影像要么是纪录,要么是虚构,界限分明,但这本书清晰地展示了在这两者之间那片广阔而迷人的灰色地带。他讨论的那些手法,比如自我指涉、碎片化叙事或者对观众注意力的故意分散,都是为了达到一种超越传统再现的目的。读完后,我开始警惕那些看起来过于“流畅”和“完整”的叙事,总会去寻找其中隐藏的“断裂”和“异化”。这本书就像是一个高明的魔术师,揭示了影像是如何被建构的,而一旦你看到了背后的机关,你就再也无法以从前的眼光看待任何一部影片了。它教会我的,是如何在观看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评分天哪,我最近读完了一本关于电影的书,简直是打开了我看电影的新世界大门。这本书不像那些枯燥的教科书,它充满了作者个人的思考和洞察力,读起来就像是和一位很有学识的朋友在咖啡馆里聊天一样。作者对电影的某些特定流派的分析非常深入,他不仅仅是罗列事实,而是真正地在挖掘这些电影形式背后的哲学意图和情感张力。特别是他探讨那些游走在传统叙事边缘的作品时,那种细腻的笔触让人拍案叫绝。我尤其喜欢他对于“观看”这个行为本身的重新定义,仿佛他把我们从被动的观众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看完这本书,我再去回看那些我以前觉得晦涩难懂的电影,突然间就豁然开朗了。它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工具箱,让我可以更批判性、更有层次感地去欣赏那些不走寻常路的影像艺术。我感觉我的电影品味被这本书“升级”了,再看那些爆米花电影,总会下意识地去寻找潜藏的作者声音和结构上的巧思。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排版和设计感出乎意料地好,这让阅读体验增色不少。虽然内容非常深刻,但拿在手里却是一种享受。作者在行文中穿插的一些个人回忆和观影片段,让原本可能显得疏离的学术讨论变得异常亲切和人性化。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近乎“迷恋”的态度,他对所讨论的那些小众或边缘化的影像形式,展现出一种近乎虔诚的热情。这种热情是会传染的,读着读着,我就开始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去寻找并观看书中提到的那些作品,哪怕它们极其难寻。这本书成功地做到了“导览”的功能,它不仅仅是理论阐述,更像是一份精心绘制的地图,指引我们深入到电影艺术中那些尚未被完全开发的区域。看完之后,我感觉自己掌握了一把“暗门钥匙”,可以进入电影世界更私密、更具实验性的角落。
评分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很“硬”的艺术理论书,结果发现它的情感内核异常丰富。作者在探讨某些影像片段时,那种近乎诗意的文字表达,常常让我热泪盈眶。他似乎对“记忆”、“在场感”以及时间在影像中的扭曲有着特殊的执念,并且将这些抽象的情感体验,精准地转化为了可供分析的文本。这种将主观感受与严谨分析完美结合的能力,是这本书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它让我意识到,那些看似前卫的电影手法,背后往往蕴含着最深层的人类情感困境和表达欲望。我不是一个研究电影的专业人士,但我完全能感受到作者文字中流淌出的真挚和热情,这使得这本书在学术深度之余,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观看电影时的那种“私密性”体验。
评分关于纪录片的新看法,好书!新观点!
评分经典推荐,京东的图书,价格和物流还是很给力的。
评分老公说书不错,值得一看,推荐
评分好书,可惜填错地址寄到我妈家去了~~
评分关于纪录片的新看法,好书!新观点!
评分老公说书不错,值得一看,推荐
评分纸张质量很差、有点怀疑是盗版
评分老公说书不错,值得一看,推荐
评分老公说书不错,值得一看,推荐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