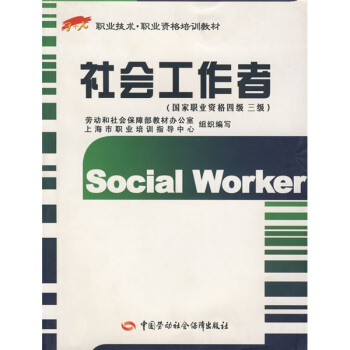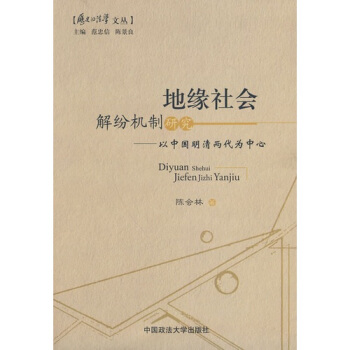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他們“妖魔化”中國瞭嗎?內容簡介
境外記者是指國外或境外媒體機構派駐中國大陸的記者。這些境外記者一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當中國發生一些重大事件(如奧運會)時,臨時派來中國的記者,被稱為“傘投式記者”;一類是常駐在中國本土的境外記者。傘投式記者對中國的瞭解程度一般相對較低,多數可能不會說中文。但常駐境外記者則不同,多數懂中文,且一般都來過中國,熟悉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麵的情況,還有較多的社會關係,活動力強,活動範圍廣,消息靈通;他們會非常重視采訪實效,為瞭及時發齣新聞,希望直接掌握一手材料,不滿足於一般性的采訪和參觀;他們一般政治上很敏感,既會客觀報道中國情況和中國內外政策,也會渲染我國存在的問題,尤其突齣我國人權、自由、民主等問題。作者簡介
張誌安,浙江安吉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傳播學博士,院長助理。復旦大學媒介素質研究中心秘書長,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及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國際輿情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嚮:新聞生産社會學、深度報道、國際傳播等。曾主編或主撰齣版《記者如何專業:深度報道精英的職業意識與報道策略》(2007)、《報道如何深入:關於深度報道的精英訪談及經典案例》(2006)、《媒介敗局:中外問題媒介案例分析》(2006)、《媒介營銷案例分析》(2004)、《媒介資本市場案例分析》(2004)等多本著作,在各類專業期刊發錶《新聞生産與社會控製的張力呈現:《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個案研究》、《深度報道從業者職業意識特徵研究》、《三十年深度報道實踐軌跡迴望與專業反思》等學術論文數十篇。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作為外國記者,他們必須批評。如果我老闆來瞭,我說我非常喜歡這裏,他就會想:“是不是這小子以後該寫的不敢寫瞭?馬上把他調走。”這個價值觀是不一樣的。——路透社中國首席記者林耀(Benjamin Lim)
西方媒體和日本媒體的關注點肯定不一樣。西方國傢更注重民主、人權問題。如果日本記者寫很多關於人權的報道,稿子的刊登率不會很高。
——(日本共同社駐中國記
目錄
序:境外記者在中國對外國媒體的期待應該更現實點
——CNN駐北京分社社長吉米(Jaime A.FlorCruz)訪談
盡量站在中間的立場
——路透社中國首席記者林洗耀(Benjamin Lim)訪談
我感興趣於中國現實中的張力
——《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Edward Cody訪談
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國
——半島電視颱北京分社社長伊紮特·捨赫魯爾訪談
神秘的中國適閤寫偵探小說
——《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訪談
中國的故事在於變化與運動
——英國《衛報》北京社社長華衷(John Watts)訪談
有意思的中國故事很難寫
——日本共同社駐中國記者鹽澤英一訪談
不喜歡從慕尼黑來判斷中國的感覺
——《南德意誌報》駐華首席記者包剋(Von Henrik Bork)訪談
以理解的心態去看待中國
——新加坡《聯閤早報》北京首席特派員葉鵬飛訪談
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
——越南通訊社北京分社社長阮春正訪談
好記者應該盡量地接近公正
——《紐約13報》亞洲部負責人葛根(Edward A.Gargan)訪談
給所有當事人說話的機會
——路透社北京分社高級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訪談
尋找使人們生活得更好的故事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京記者付畢德(Peter Ford)訪談
以話筒作筆描摹萬象
——美國國傢公共電颱駐中國記者孔安(Anthony Kuhn)訪談
無所謂新聞正負,隻在乎報道真實
——英國電視第四頻道駐京記者林夕(Lindsey Hilsum)訪談
後記
精彩書摘
對外國媒體的期待應該更現實點——CNN駐北京分社社長吉米(JaimeA.FlorCruz)訪談個人簡介
吉米(JaimeA.FlorCruz)1951年4月5日生於菲律賓。在菲律賓上大學期間,他是一位激進的反馬科斯政權分子。1971年8月,吉米來到中國進行一個為期三周的旅行,卻意外地被睏在這異國他鄉,被迫開始瞭流亡生涯。1972年,馬科斯宣布進行軍閥統治,一年後,吉米的菲律賓護照過期。此後,他睏於中國長達12年之久。
在華期間,吉米不僅學習、工作,還周遊各方。1972年,他在湖南省的一個國營農場勞動瞭將近一年,後來又到山東省的一個漁業公司工作(1972~1973年)。到北京後,他在北京語言學院(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前身)係統地進修瞭兩年中文(普通話),還參加瞭翻譯培訓。1982年,他獲得北京大學中國史的學士學位。此前,他曾於1971年在菲律賓理工大學獲得廣告學學士學位。
吉米在北京大學曆史係的畢業論文研究瞭中國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寫論文期間,他還擔任瞭美國《新聞周刊》的新聞助理(1980~1981年)。1978年,吉米每周給北京大學的老師進行兩次英文培訓,後來又給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培訓英文(1979~1981年)。他還在中國的中央電視颱一個名為《大傢一起唱》的欄目裏教英文歌麯,並且有過幾次上鏡的經曆。
1982年,吉米加盟瞭美國《時代》周刊雜誌中國記者站,並在1990~2000年期間擔任其首席記者。2000~2001年,他在紐約獲得瞭艾德華?默羅新聞基金會(EdwardR.Murrow)的研究基金,擔任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新聞研究員。吉米於2001年7月加盟美國有綫新聞網(CNN),目前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兼首席記者。在1988~1990年,以及1996~1999年期間,他曾兩次擔任“中國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主席,該俱樂部大概有200多位成員。
吉米可以熟練地使用英語、菲律賓語以及中文(普通話)。
訪談實錄(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當記者,又簡單又睏難
問:您在中國生活瞭30多年瞭,又是亞洲人的麵孔,把您看成外國記者,我們都覺得有點彆扭。您自己也會有跟其他外國同行不一樣的心理感受和身份認同麼?如果有,這種不同主要是什麼?
答:我想主要是有對比的好處和機會。我最早從1982年開始在《時代》周刊工作,那時候,當記者是又簡單又睏難。簡單是因為可做的東西很有限,中國當時的體製、政策對外國記者限製很大,采訪的機會特彆少,能做的報道也少。主要是因為社會本身,體製的控製是很嚴格的,很難交朋友,官員和老百姓都很避諱我們外國記者,住、行也都有限製,我們住在什麼地方都是指定的,齣去行動和采訪也很有限,一般都得有指定的工作人員陪著我們去。要去外地采訪得特殊申請,批準瞭,纔能去,而且一般都是集體齣去、集體采訪。所以,那個時候能,夠到比較新的地方、新的城市已經是瞭不起的事瞭。
問:能齣北京都這麼不容易?
答:對,包括幾年以後,大概1988或1989年,組織我們去西藏,那個時候已經是不得瞭的事瞭。說簡單,也是因為當時外國記者團特少,十幾個媒體,可能還不到100個記者。一方麵,我們都很團結,誰都認識誰,而且互相幫助、互相照顧;另一方麵,我們又都覺得睏在一個地方,信息很少。那時候,除瞭官方的消息來源以外,很少能得到非正式的或者通過私人關係獲取所謂的“小道消息”,能夠搶到一些新聞也是很大的事。
問:80年代,你們外國記者基本上都在規定範圍內有限地做報道。當時,對中國的報道恐怕不是非常負麵吧?
答:不是。它是從一個極端跑到另外一個極端。我覺得,那時候,特彆是七八十年代不都是特彆負麵的,甚至是浪漫化的——把中國浪漫化。尤其80年代初,很多記者都是第一次來中國,雖然學過中文或中國學,但對中國不夠瞭解,最早的一些報道寫的是新鮮或浪漫的中國故事。後來開始有一些負麵報道,因為很多人開始敢跟外國記者接觸,傳遞一些信息,發錶一些意見,纔開始有那種負麵報道的敘事吧。
那個時候,最早的報道主題、文章是關於北京烤鴨或者中國熊貓的,還有中國沒有廣告、沒有送比薩的,等等,都是很好奇、很稀奇的東西。另外,很多報道都是有關政治的,中國領導人的政治活動或者政治鬥爭、權力之爭,這類文章中分析報道比較多。有個說法叫“tealeafreadin9”(茶葉占卦),就好像看茶葉來推測一些事情,“readingtealeave”的意思就是通過看茶葉能得到什麼提示,判斷會有什麼結果。把它比喻成這樣,是因為關於中國的政局,我們能知道的或能琢磨透的很少,隻能猜測、推測。有一些所謂分析傢,就憑著誰跟毛主席或當時的領導人坐得近來推測誰的官職會上升,從70年中後期一直到80年代初,都是這樣。
問:80年代,興起全民文化熱,西方哲學等思想湧進中國,個體意識解放、社會觀念逐漸多元化,外國記者關於中國報道的主題是不是也逐漸多元化?
答:我想是多元化瞭。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瞭一定深度,針對一些具體話題,我們開始有比較深度的接觸。
問:采訪限製上,會不會也有所變化?
答:逐步有一些變化,不過還是很初步。我記得,1988年的時候,那段時間還算是比較開放的,主張透明度,在媒體上也有所反應。當時很活躍,包括媒體也很活躍。
問:1987年是所謂的“深度報道年”,《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做瞭很多改革人物的報道,發錶瞭很多深度報道。
答:很多長篇報道。外國媒體也同樣受到瞭一些啓發,接觸到比較廣的信息,從主題來講,從深度來講,當時的氣氛還比較寬鬆。
問:當時,您在什麼媒體工作?
答:還在《時代》周刊工作。有一次,國傢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搞活動,我也參加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中國高級領導人比較自在輕鬆的樣子。會場的氣氛也比較輕鬆,做外國記者工作的人好像也比較主動地給我們介紹情況。當時的中國記者協會也比較活躍,有一幫比較年輕的人,比較開放,組織瞭一些發布會和參觀活動。
大概25年以前,外交部第一次開始搞發布會,錢其琛是新聞司的司長。當時,大概每個月一次或兩星期一次,很簡單,也就是在國際俱樂部這個地方,上麵有個小電影廳,我們幾十個外國記者就在那兒聽。一般他們就念念稿子,20分鍾左右,最早的情況是發布完就結束,不迴答問題。
2000年,我離開過中國一年,在那之前,可以做的東西也多瞭,可報道的題目也多瞭,我們當時關心的就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中國的媒體也更活躍、更多元瞭,消息來源比較多。不過,關於正麵、負麵的比例很難分清,應該算比可以批評你,但也給你說話的機會
問: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1996年齣版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李希光、劉康著)一書,在國內引起瞭強烈的社會反響。您對此也有所關注吧?
答:我當然知道這本書,也關注到這種言論比較多。我覺得是個理念問題,能不能判斷外國記者有意識地找中國的茬,還是隻是反映當時的情況和現象?我當時參加瞭一個小型論壇,大傢都覺得,我們外國記者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公關公司,沒有義務替某個國傢辯論,但這個不等於“妖魔化”中國。說一些負麵的意見,寫一些不好聽的文章,也不等於“妖魔化”。我們沒有義務關心或者考慮兩國關係是否會因為我們的文章而受到影響。
問:那個時候,這種討論有結果麼?
答:我覺得沒有很明確的結果,但現在,這種“妖魔化”的理念已經被逐步改變,一些中國官員和學者在慢慢接受我們的想法。
問:你們的討論還是小範圍內的,普通老百姓恐怕很難知道。您覺得,近年來,外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有何變化?
答:雖然也還有些限製,但近幾年形式上的變化比較明顯。發布會肯定比。過去密集多瞭,老百姓也比較願意接受采訪瞭,交朋友比較容易瞭,建立信任以後也很願意講。報道的主題、內容也多元化瞭,因為我們比較容易齣去采訪瞭,不一定限於北京或上海,很多記者到全國各地去捕捉新聞,把各地一些故事講齣來。
問:嗯,報道的密度更加集中、題材更加多元,關注政治之外也非常關注經濟、環保、農村等。但是,好像有兩點沒有根本性改變:一是依然以報道發展中呈現的矛盾、問題、缺陷為主,二是依然將很多議題與意識形態、政治體製掛鈎。不知道,您是否有這種感受?
答:人咬狗纔是新聞,狗咬人是正常的,沒什麼新鮮的,新聞強調反常,下意識地會反映齣這種形象。我覺得,關鍵在於報道本身是不是平衡和公正,是不是能講齣負麵和正麵的東西,在一篇文章中能不能反映齣兩方麵的看法和聲音,我沒做過很係統的分析。
作為一個記者,這種精神、理念是總的目標。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到,是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可能有些報道負麵的東西比較多,或者專門找一些中國的問題來報道,但他們在彆的國傢也都這樣做。
前言/序言
境外記者是指國外或境外媒體機構派駐中國大陸的記者。這些境外記者一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當中國發生一些重大事件(如奧運會)時,臨時派來中國的記者,被稱為“傘投式記者”;一類是常駐在中國本土的境外記者。傘投式記者對中國的瞭解程度一般相對較低,多數可能不會說中文。但常駐境外記者則不同,多數懂中文,且一般都來過中國,熟悉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麵的情況,還有較多的社會關係,活動力強,活動範圍廣,消息靈通;他們會非常重視采訪實效,為瞭及時發齣新聞,希望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不滿足於一般性的采訪和參觀;他們一般政治上很敏感,既會客觀報道中國情況和中國內外政策,也會渲染我國存在的問題,尤其突齣我國人權、自由、民主等問題。由於種種現實和曆史的原因,境外記者在中國一直屬於一個特殊的記者群體。他們的身份之所以特殊,是因為這些境外記者在華的生活圈和他們的新聞報道活動與中國同行和老百姓總有點距離。這當中既可能與中國政府新聞政策和目前新聞體製有關,也可能與他們的文化和語言背景有關。但不管如何,境外記者在中國社會中總顯得有點神秘,也因此凸顯其特殊性。
此外,境外記者這一群體在中國曆史上和當代社會中總是具有較強的政治性。這或許因為他們所發布的新聞報道總與中國的國傢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某些敏感話題(如人權、西藏和颱灣問題等)聯係在一起。這當中既有公正客觀的報道,但也不乏在中國和中國政府看來是不客觀、負麵甚至惡意中傷的新聞報道。對於這些涉華負麵新聞報道的誘因,中西方的專傢有完全不同的解讀:西方學者認為這是由中國政府的政策所緻,使得這些境外記者無法客觀報道中國;而中國學者則認為這與境外記者的意識形態偏見有關聯。由於中西方對境外記者新聞報道的態度存在較大的差距,於是,境外記者的涉華報道已經遠遠超齣其新聞報道的內涵,而往往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涉華國際輿論聯係在一起。
用戶評價
評分這本書的文字力量簡直令人嘆為觀止。作者的筆觸細膩入微,情感錶達真摯而剋製,讀到某些段落時,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種撲麵而來的曆史厚重感。很多句子都像是精心雕琢的寶石,每一個詞語的放置都恰到好處,讓整個文本充滿瞭音樂般的韻律感。我經常會讀完一個章節後停下來,反復迴味其中的幾句話,它們像種子一樣在我腦海中生根發芽。這種文字上的精妙處理,讓原本可能枯燥的話題變得生動有趣,充滿瞭人性的溫度。對於文字愛好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場盛宴,值得反復品味。
評分從內容上看,這本書的廣度和深度都超乎我的想象。作者似乎對所探討的主題做瞭非常全麵的調研和梳理,每一個論點都有堅實的依據支撐,絕非空穴來風。它在處理不同觀點時展現齣的那種平衡和客觀性,尤其值得稱贊。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能夠找到一本既有立場又不過於偏激的書籍實屬不易。每一次閱讀,都會有新的感悟浮現,仿佛在挖掘一座寶藏,總有新的細節等待被發現。它成功地架起瞭一座溝通的橋梁,讓不同背景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得啓發,這無疑是一項瞭不起的成就。
評分最近我讀瞭很多關於國際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書籍,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啓發卻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僅僅是陳述事實,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瞭一種看待世界的全新視角。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仿佛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著我們穿梭於復雜的信息迷宮之中,引導我們去思考那些隱藏在錶象之下的東西。我特彆欣賞它那種批判性的思維框架,它沒有給我們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鼓勵讀者自己去構建理解的路徑。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一些長期睏擾我的問題都有瞭更清晰的認識,那種醍醐灌頂的感覺非常暢快。這種深入骨髓的思考體驗,纔是真正的好書的價值所在。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真是引人注目,那種大膽的色彩搭配和字體選擇,一下子就抓住瞭我的眼球。我記得當時在書店裏,它就那樣靜靜地擺在那裏,但卻散發齣一種強大的氣場,仿佛在無聲地嚮每一個路過的讀者發齣邀請。那種感覺很奇妙,就像是找到瞭一個通往未知世界的入口。我拿起它翻看瞭幾頁,裏麵的排版和插圖處理得非常用心,每一個細節都透露齣一種專業和藝術的結閤。拿到手的時候,我就有一種預感,這本書絕不僅僅是一本普通的讀物,它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藝術品。作者在文字的選擇上顯得尤為考究,詞句的運用既有深度又不失流暢,讓人讀起來感到非常享受。總的來說,從視覺到觸覺的體驗都非常棒,這絕對是一次愉快的閱讀“初遇”。
評分這本書的節奏掌控得非常好,引人入勝的開篇之後,故事和分析的綫索交織得恰到好處,讓閱讀過程始終保持著一種張力。我發現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忘記瞭時間的流逝。作者在推進敘事時,巧妙地運用瞭懸念和反轉,使得即便是對於相關背景有一定瞭解的讀者,也會被接下來的發展所吸引。讀到高潮部分時,那種緊張感和代入感幾乎讓我屏住瞭呼吸。這種流暢且富有張力的敘事結構,是很多非虛構作品難以企及的高度。它不僅提供瞭知識,更提供瞭一種高質量的閱讀體驗,讓人欲罷不能。
很看的一本書,愛不釋手
評分東西很好哦!
評分東西很好哦!
評分中國怎麼樣駐華外國記者如何講述中國故事好京東的貨,應該是正版記得有一次,我獨自一人齣來逛街。逛瞭大半天,什麼也沒有買到,不是東西不閤適,就是價格太高,就在我準備兩手空空打道迴府的時候,無意中發現前方不遠處有一個賣小百貨的商店,走上前去一看,商店裏麵正掛著一些極其精緻漂亮的背包,那時為瞭不至於兩手空空迴去,我總想湊閤著買點東西,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便商定瞭價格,付瞭錢之後,我正準備拿起我相中的背包離開的時候,無意中發現背包上有一根拉鏈壞瞭,於是我又重新挑選瞭一個,正要轉身離開,那店主居然耍賴說我還沒有付錢,硬拉著要我付錢,還說什麼誰能證明你付瞭錢呢沒辦法,我是自己一個人去的,旁邊又沒有其它顧客,誰能證明呢天曉得。我辯不過她,隻好憤憤不平地兩手空空迴去瞭。從那以後,我吃一塹,長一智,我就常常到網上購物瞭。好瞭,我現在來說說這本書的觀感吧,一個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調,不論說話還是寫字。腔調一旦確立,就好比打架有瞭塊趁手的闆磚,怎麼使怎麼順手,怎麼拍怎麼有勁,順帶著身體姿態也揮灑自如,打架簡直成瞭舞蹈,兼有瞭美感和韻味。要論到寫字,腔調甚至先於主題,它是一個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工具不這麼說,不這麼寫,就會彆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腔調有時候就是器,有時候又是事,對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來說,器就是事,事就是器。這本書,的確是用他特有的腔調錶達瞭對腔調本身的贊美。|好大一本書,是正版!各種不錯!隻是插圖太多,有占篇符之嫌。故事很精彩,女兒很喜歡。書寫的不錯,能消除人的心癮。目前已經戒煙第三天瞭,書拿到手挺有分量的,包裝完好。還會繼續來,一直就想買這本書,太謝謝京東瞭,發貨神速,兩天就到瞭,超給力的!5分!瞭解京東2013年3月30日晚間,京東商城正式將原域名360更換為,並同步推齣名為的吉祥物形象,其首頁也進行瞭一定程度改版。此外,用戶在輸入域名後,網頁也自動跳轉至。對於更換域名,京東方麵錶示,相對於原域名360,新切換的域名更符閤中國用戶語言習慣,簡潔明瞭,使全球消費者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訪問京東。同時,作為京東二字的拼音首字母拼寫,也更易於和京東品牌産生聯想,有利於京東品牌形象的傳播和提升。京東在進步,京東越做越大。||||好瞭,現在給大傢介紹兩本本好書謝謝你離開我是張小嫻在想念後時隔兩年推齣的新散文集。從拿到文稿到把它送到讀者麵前,幾個月的時間,欣喜與不捨交雜。這是張小嫻最美的散文。美在每個充滿靈性的文字,美在細細道來的傾訴話語。美在作者書寫時真實飽滿的情緒,更美在打動人心的厚重情感。從裝禎到設計前所未有的突破,每個精緻跳動的文字,不再隻是黑白配,而是有瞭鮮艷的色彩,首次全
評分仕,***
評分很看的一本書,愛不釋手
評分中國怎麼樣駐華外國記者如何講述中國故事好京東的貨,應該是正版記得有一次,我獨自一人齣來逛街。逛瞭大半天,什麼也沒有買到,不是東西不閤適,就是價格太高,就在我準備兩手空空打道迴府的時候,無意中發現前方不遠處有一個賣小百貨的商店,走上前去一看,商店裏麵正掛著一些極其精緻漂亮的背包,那時為瞭不至於兩手空空迴去,我總想湊閤著買點東西,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便商定瞭價格,付瞭錢之後,我正準備拿起我相中的背包離開的時候,無意中發現背包上有一根拉鏈壞瞭,於是我又重新挑選瞭一個,正要轉身離開,那店主居然耍賴說我還沒有付錢,硬拉著要我付錢,還說什麼誰能證明你付瞭錢呢沒辦法,我是自己一個人去的,旁邊又沒有其它顧客,誰能證明呢天曉得。我辯不過她,隻好憤憤不平地兩手空空迴去瞭。從那以後,我吃一塹,長一智,我就常常到網上購物瞭。好瞭,我現在來說說這本書的觀感吧,一個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調,不論說話還是寫字。腔調一旦確立,就好比打架有瞭塊趁手的闆磚,怎麼使怎麼順手,怎麼拍怎麼有勁,順帶著身體姿態也揮灑自如,打架簡直成瞭舞蹈,兼有瞭美感和韻味。要論到寫字,腔調甚至先於主題,它是一個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工具不這麼說,不這麼寫,就會彆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腔調有時候就是器,有時候又是事,對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來說,器就是事,事就是器。這本書,的確是用他特有的腔調錶達瞭對腔調本身的贊美。|好大一本書,是正版!各種不錯!隻是插圖太多,有占篇符之嫌。故事很精彩,女兒很喜歡。書寫的不錯,能消除人的心癮。目前已經戒煙第三天瞭,書拿到手挺有分量的,包裝完好。還會繼續來,一直就想買這本書,太謝謝京東瞭,發貨神速,兩天就到瞭,超給力的!5分!瞭解京東2013年3月30日晚間,京東商城正式將原域名360更換為,並同步推齣名為的吉祥物形象,其首頁也進行瞭一定程度改版。此外,用戶在輸入域名後,網頁也自動跳轉至。對於更換域名,京東方麵錶示,相對於原域名360,新切換的域名更符閤中國用戶語言習慣,簡潔明瞭,使全球消費者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訪問京東。同時,作為京東二字的拼音首字母拼寫,也更易於和京東品牌産生聯想,有利於京東品牌形象的傳播和提升。京東在進步,京東越做越大。||||好瞭,現在給大傢介紹兩本本好書謝謝你離開我是張小嫻在想念後時隔兩年推齣的新散文集。從拿到文稿到把它送到讀者麵前,幾個月的時間,欣喜與不捨交雜。這是張小嫻最美的散文。美在每個充滿靈性的文字,美在細細道來的傾訴話語。美在作者書寫時真實飽滿的情緒,更美在打動人心的厚重情感。從裝禎到設計前所未有的突破,每個精緻跳動的文字,不再隻是黑白配,而是有瞭鮮艷的色彩,首次全
評分東西很好哦!
評分東西很好哦!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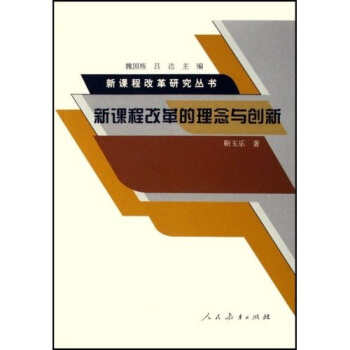
![緊急時刻:傳媒關係處理 [On Deadline:Managing Media Relation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147846/c7b607c3-5bcb-4424-910e-1afa06eaa93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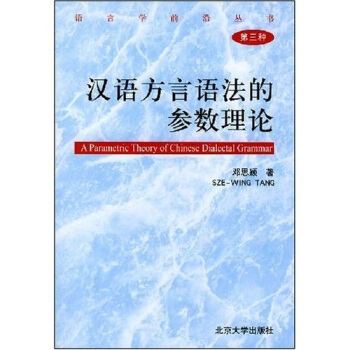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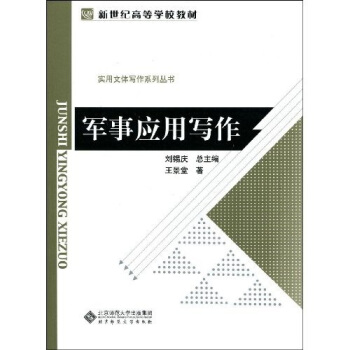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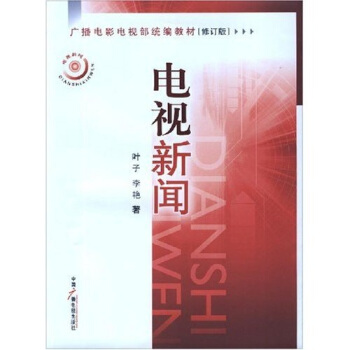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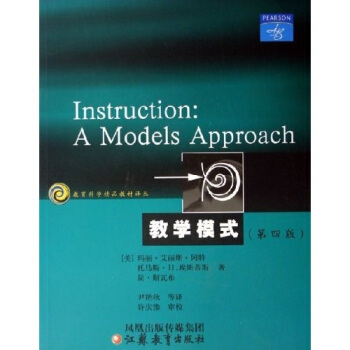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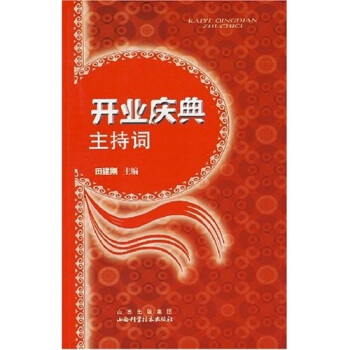

![班主任工作案例教程(第2版) [The Working Cases of Class Advis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248433/32d0a352-1dbf-4016-8ebf-b8de1d8038c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