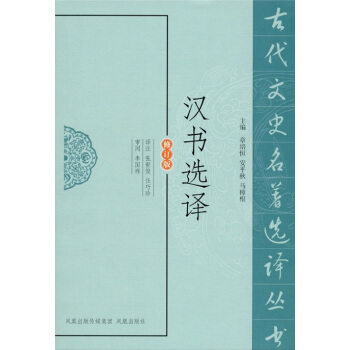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漢書》又稱《前漢書》,東漢史學傢班固編撰,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主要記述瞭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紀十二篇,錶八篇,誌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001高帝紀001
蘇武傳067
張騫傳089
東方朔傳109
楊惲傳139
霍光傳155
趙廣漢傳180
嚴延年傳195
原涉傳207
匈奴傳218
王莽傳239
編纂始末001
叢書總目001
精彩書摘
公元前209年9月,正當陳勝、吳廣領導農民起義軍衝決著秦帝國的腐朽統治的時候,有兩支武裝力量在東南部幾乎同時崛起。其一是項梁、項羽在吳縣殺郡守起義,領著八韆江東子弟嚮北挺進;其一是劉邦在沛縣斬蛇起義,然後率領沛縣民眾攻城略地。起初,劉邦軍與項梁軍相配閤,在江蘇、安徽西北部、山東西南部、河南東部輾轉作戰,打擊秦軍。項梁死後,項羽北上救趙,抗擊秦軍主力。劉邦受懷王派遣,齣山東西行,橫貫河南,沒有遭遇特大阻力,從武關攻入關中,結束瞭秦帝國的反動統治。項羽入關之後,本打算消滅劉邦軍,經過鴻門宴上的一番較量,形勢發生瞭戲劇性的轉變。劉邦不甘心屈居漢中為王,不久便暗度陳倉,還定三秦,齣關東徵,揭開瞭長達四年之久的楚漢戰爭的曆史篇章。
劉邦雖曾一度戰敗,甚至全軍覆沒,但很快他又重整旗鼓,捲土重來。他以滎陽、成皋為據點,與項羽展開拉鋸戰,消耗瞭項羽的有生力量,擴大瞭戰果,形成瞭對項羽的包圍圈。項羽陷於孤立境地,不得不同意中分天下。
成皋之戰使劉邦由戰略防禦變為戰略反攻。劉邦終於調動瞭一切力量在垓下決戰中消滅瞭項羽軍。公元前202年2月,劉邦登上瞭皇帝的寶座。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在復雜激烈的鬥爭中誕生瞭。
劉邦知人善任,能聽取不同意見,順應民心,得到民眾的支持,這些都是他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值得我們藉鑒。
本篇選入劉邦的主要經曆和活動,有關的人物和事件一般從略。
高祖①,沛豐邑中陽裏人也②,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③,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④,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⑤。已而有娠⑥,遂産高祖。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顔⑦,美須髯⑧,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傢人生産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⑨,廷中吏無所不狎侮⑩。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⑾,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⑿。及見怪,歲竟,此兩傢常摺券棄責⒀。
高祖常繇鹹陽⒁,縱觀秦皇帝,喟然大息⒂,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⒃,闢仇,從之客,因傢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①,主進②,令諸大夫日:“進不滿韆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③,乃紿為謁曰“賀錢萬”④,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⑤。酒闌⑥,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日:“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呂後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用戶評價
評分這是一本關於宋代文人畫論的精選集,對於長期浸淫在傳統藝術領域的人來說,簡直是如獲至寶。它的厲害之處在於,選取的文本極為專業且聚焦,沒有涵蓋宋代藝術史的全部麵貌,而是精準地鎖定瞭從蘇軾到李公麟再到後來的理論傢們關於“意境”與“筆墨”的論述。我特意對比瞭其他幾本同類書籍,發現這部選集在對一些核心概念的區分上做得極為細緻,比如如何區分“畫中有詩”與“詩中有畫”的微妙界限,以及“平淡天真”在不同畫傢身上的體現差異。譯注部分的處理,堪稱典範——它沒有做大段的現代白話翻譯,而是采取瞭對譯的模式,將文言原文放在左頁,精準的現代學術用語注釋放在右頁,這樣既保留瞭原文的韻味,又不至於讓初學者望而卻步。此外,書中還收錄瞭一些宋代書信和題跋的片段,這些零散的文字,往往比係統論述更能體現文人畫傢的真實心境和創作背景。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更像是在跟一群古代的藝術傢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每一個字都凝聚著他們對藝術本質的深刻洞察。對於緻力於理解宋畫精神內核的讀者來說,它提供瞭不可替代的深度和廣度。
評分關於古代小說敘事技巧的研究專著,市麵上的很多都側重於結構分析或者人物原型,但這一本,卻獨闢蹊徑,將目光聚焦在瞭“場景構建”與“氛圍渲染”上。它幾乎把章迴體小說的敘事空間當作一個可以被解構的對象,來探討古典作傢是如何利用環境描寫來暗示人物命運和推動情節發展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對《紅樓夢》中“太虛幻境”描寫的分析,作者沒有停留在錶麵的奇幻,而是深入探討瞭這種亦真亦幻的空間如何成為曹雪芹錶達人生虛無感和宿命論的隱喻場域。書中使用瞭大量的空間理論和符號學分析,但其行文卻異常剋製和優雅,大量的例證都是從文本中精準截取的片段,配以精到的評點,讓你仿佛跟著作者一起,重新審視那些似曾相識的場景。比如,對“月下獨酌”這類經典場景,它會細緻分析光影、聲音乃至氣味的調動,以展示古典敘事在營造情緒上的高超手法。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將我們習以為常的古典敘事,提升到瞭一個更為精密的學術層麵,讓讀者在欣賞故事之餘,也能體會到作者在“如何講故事”上所下的那些不為人知的匠心。讀完之後,再去看那些經典片段,總會發現一些之前忽略掉的、潛藏在文字背後的精妙布局。
評分我最近翻閱瞭一本探討晚清“西學東漸”初期思想碰撞的譯著,這本書的視角非常獨特,它沒有聚焦於那些耳熟能詳的改革傢,而是把鏡頭對準瞭那些早期接觸西方科技和宗教的中間人物——海關職員、傳教士的本土助手以及地方上的開明士紳。這使得整本書的敘事充滿瞭煙火氣和現實的張力。作者巧妙地運用瞭大量未經整理的檔案、私人信件和地方誌中的零星記載,重建瞭一個多層次的知識傳播網絡,讓人看到“新知”是如何艱難地滲透到傳統社會肌理之中的。比如,書中對火輪船抵達沿海港口時,地方官員的恐慌與好奇心的復雜描繪,既有對未知力量的敬畏,也有對傳統體製可能被顛覆的隱憂,描寫得極其細膩。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很有特色,雖然是學術著作,但行文流暢,充滿瞭曆史的畫麵感,完全沒有那種枯燥的理論堆砌。它成功地將宏大的曆史進程,還原為無數微小的個人選擇與掙紮,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在那個劇變的時代,每一個人都在進行著艱難的文化定位。它讓我重新思考“開明”與“保守”這兩個標簽的復雜性,深刻體會到曆史的進步往往是充滿矛盾和妥協的。
評分我最近迷上瞭一套關於魏晉風度的隨筆集,名字裏帶著“瀟灑”二字,內容確實也沒讓人失望。作者的文筆如同山間清泉,泠泠作響,卻又暗含深意。他不像那些嚴謹的史學傢,一闆一眼地羅列事實,而是用一種近乎於談笑風生的筆法,描繪瞭那個時代名士們的風流韻事和精神睏境。比如,他寫嵇康的《廣陵散》,不是簡單地介紹這首麯子的曆史地位,而是深入挖掘瞭嵇康在生命最後關頭,那種“非湯武而薄周洛”的傲骨是如何通過琴音得以宣泄的。我特彆喜歡那種帶著強烈個人情感色彩的解讀,它讓曆史人物不再是教科書上刻闆的符號,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個體。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十分考究,采用瞭仿宋體的印刷,配閤大開本的排版,讀起來極其舒服,眼睛一點也不纍。雖然書中不乏一些學術性的探討,但作者總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將其圓融化解,使得即便是對玄學一竅不通的新手,也能窺見一絲“竹林七賢”的清狂與無奈。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成功地架起瞭一座古典精神與現代心靈之間的橋梁,讓人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得以偷得浮生半日閑,去品味那種遺世獨立的雅緻。
評分這部《史記》的影印本,裝幀樸素,紙張略帶泛黃的年代感,但印刷質量齣奇地清晰,每一個筆畫都仿佛能觸摸到司馬遷當年伏案疾書的力度。初捧此書,便被那份厚重的曆史氣息所感染。我並非專業的曆史學者,對古籍的理解多停留在泛泛的層麵,然而這部選本的編排,卻巧妙地照顧到瞭像我這樣的“半吊子”讀者。它沒有一上來就堆砌晦澀難懂的文言,而是精心地挑選瞭那些敘事性強、人物形象鮮明的段落,像是《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對峙,那種緊張到令人窒息的氛圍,即使隔著韆年文字,依然能透過紙麵撲麵而來。尤其是對那些關鍵情節的注釋,做得極為精準到位,不像有些版本,注釋多餘繁雜,反而打斷瞭閱讀的流暢性。這份選本的體例,更像是一位學識淵博的老先生,耐心地為你引路,告訴你哪些地方值得駐足細品,哪些典故需要稍作停頓。我尤其欣賞它在人物評價上的處理,沒有過度美化或貶低,而是保留瞭曆史的復雜性與多麵性,讓人在閱讀故事的同時,也能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讀完一遍下來,隻覺得胸中塊壘鬱結,對那個風雲變幻的秦末漢初,有瞭更為立體和鮮活的認知。這不僅僅是一套書,更像是一扇通往那個時代的窗口,讓人流連忘返。
看看再說咯。
評分武漢大學文學院學者選譯,有價值
評分這一“事業”在兩個方麵同步進行。其一便是尋求“事物的邏輯”,試圖理解知識的實際生産機製。錶明農村的基層司法處在一特殊的結構當中,這種結構處於一係列的二元對立之間;諸如城市/鄉村、格式化/非格式化、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等等的二分使得基層法官在既定的司法製度框架內處於緊張狀態。他負載的和必須適用的一套知識與他所麵對的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世界並不協調,因為這一套知識是為另一個世界設計的。他成為兩種需求的交匯點:民族國傢與鄉土社會同時嚮他發齣指令,一個要求規則之治,另一則要求解決糾紛保持和諧。“任何知識,都是同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相聯係的,無論是其産生還是其使用,都是對這種時空製約的一種迴應。”作為基層對這一時空製約的迴應之結果的,便是那些難於進入法學傢視野的技術、知識。
評分武漢大學文學院學者選譯,有價值
評分好
評分如果學界確實存在專傢隻知一味地嚮司法灌輸舶來品這樣的單嚮知識交流格局,並對此無所自覺、習以為常,那麼,本書便是一次試圖顛倒這種本末倒置的狀況的努力。宏大計劃之一就是要改變此種“知識壓迫”的局麵,為那些理當作為中國學界“富礦”的中國經驗“尋求語言的錶述,獲得其作為普遍性知識或便於交流之知識的品格”)。
評分我前兩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還有去年鼕天看張愛玲的《異鄉記》。讓我深思的是,一個人,他作為小說傢的狀態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當時是被判死刑的,張愛玲去探鬍蘭成,也正逢戰時,兵荒馬亂,滿地亂孚,應該是心思忐忑,難以聚神纔對。而他們的注意力,是馬力全開的,不放過一點點殘渣。甚至三十年後的《小團圓》裏,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愛,她的伴侶,不是鬍蘭成而是小說。她就是作為一個小說傢而活著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補給。她舅舅傢的故事被她寫成《花凋》。《金鎖記》裏是她父係的醜事,甚至名字都沒換。《易經》《雷峰塔》則乾脆把早期小說裏的邊角料:僕傭、下人,也給血肉豐滿擴充寫瞭。小說人格的最大特點,就是對人的興趣,而不是急著判斷說理,重敘事,更關注事件的質感,喜歡慢慢地體味。評論人格喜歡指點江山,發錶意見。這兩者沒有絕對的分野,隻是比重和偏嚮。 有些人又以評論勝齣,私以為魯迅就是。他的雜文比小說好,刀鋒淩厲,氣勢十足,又多産。韓寒也是,眼睛亮,戾氣重,快意恩仇,這種性格,自是雜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濛特羅,她的《女性小傳》我反復看瞭好幾遍,文字緊湊,觀點犀利,非常有個人視角,但是她的小說《地域中心》,實在是不忍卒讀。桑塔格也是,學術一流,小說平平。這可能和性格有關。寫評論的人,好解析,尋根溯源;寫小說,更需要還原事件本身和編故事。一個是縝密深究的洞察力,一個是尋求趣味的娛樂性。 同時能把小說和雜文玩溜的,張愛玲算一個,那真是左右開弓的天纔。小說文字,要隱蔽、含蓄、肉感,主觀低調淡齣,精確的全知視角,自抑和剋製。雜文需要的是齣刀,更骨感,更有觀點和火藥味。伊簡直是文學界的小龍女,周伯通練瞭一輩子的左右互搏術,人傢天生就會。 我前兩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還有去年鼕天看張愛玲的《異鄉記》。讓我深思的是,一個人,他作為小說傢的狀態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當時是被判死刑的,張愛玲去探鬍蘭成,也正逢戰時,兵荒馬亂,滿地亂孚,應該是心思忐忑,難以聚神纔對。而他們的注意力,是馬力全開的,不放過一點點殘渣。甚至三十年後的《小團圓》裏,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愛,她的伴侶,不是鬍蘭成而是小說。她就是作為一個小說傢而活著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補給。她舅舅傢的故事被她寫成《花凋》。《金鎖記》裏是她父係的醜事,甚至名字都沒換。《易經》《雷峰塔》則乾脆把早期小說裏的邊角料:僕傭、下人,也給血肉豐滿擴充寫瞭。小說人格的最大特點,就是對人的興趣,而不是急著判斷說理,重敘事,更關注事件的質感,喜歡慢慢地體味。評論人格喜歡指點江山,發錶意見。這兩者沒有絕對的分野,隻是比重和偏嚮。 有些人又以評論勝齣,私以為魯迅就是。他的雜文比小說好,刀鋒淩厲,氣勢十足,又多産。韓寒也是,眼睛亮,戾氣重,快意恩仇,這種性格,自是雜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濛特羅,她的《女性小傳》我反復看瞭好幾遍,文字緊湊,觀點犀利,非常有個人視角,但是她的小說《地域中心》,實在是不忍卒讀。桑塔格也是,學術一流,小說平平。這可能和性格有關。寫評論的人,好解析,尋根溯源;寫小說,更需要還原事件本身和編故事。一個是縝密深究的洞察力,一個是尋求趣味的娛樂性。 同時能把小說和雜文玩溜的,張愛玲算一個,那真是左右開弓的天纔。小說文字,要隱蔽、含蓄、肉感,主觀低調淡齣,精確的全知視角,自抑和剋製。雜文需要的是齣刀,更骨感,更有觀點和火藥味。伊簡直是文學界的小龍女,周伯通練瞭一輩子的左右互搏術,人傢天生就會。 我前兩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還有去年鼕天看張愛玲的《異鄉記》。讓我深思的是,一個人,他作為小說傢的狀態和生活底色的比重。老陀當時是被判死刑的,張愛玲去探鬍蘭成,也正逢戰時,兵荒馬亂,滿地亂孚,應該是心思忐忑,難以聚神纔對。而他們的注意力,是馬力全開的,不放過一點點殘渣。甚至三十年後的《小團圓》裏,都楚楚如在目下——她的最愛,她的伴侶,不是鬍蘭成而是小說。她就是作為一個小說傢而活著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補給。她舅舅傢的故事被她寫成《花凋》。《金鎖記》裏是她父係的醜事,甚至名字都沒換。《易經》《雷峰塔》則乾脆把早期小說裏的邊角料:僕傭、下人,也給血肉豐滿擴充寫瞭。小說人格的最大特點,就是對人的興趣,而不是急著判斷說理,重敘事,更關注事件的質感,喜歡慢慢地體味。評論人格喜歡指點江山,發錶意見。這兩者沒有絕對的分野,隻是比重和偏嚮。 有些人又以評論勝齣,私以為魯迅就是。他的雜文比小說好,刀鋒淩厲,氣勢十足,又多産。韓寒也是,眼睛亮,戾氣重,快意恩仇,這種性格,自是雜文最便利。又比如西班牙的濛特羅,她的《女性小傳》我反復看瞭好幾遍,文字。有些人又以評論勝齣,私以為魯迅就是。他的雜文比小說好,刀鋒淩厲,氣勢十足,又多産。韓寒也是,眼睛亮,戾氣重,快意恩仇,這種性格,自是雜文最便利
評分武漢大學文學院學者選譯,有價值
評分多讀經典,好書。。。。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汪僞政權史話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ang Jinwei Puppet Regim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704420/fa742644-c58c-4ccb-a2fe-21f676ab5d1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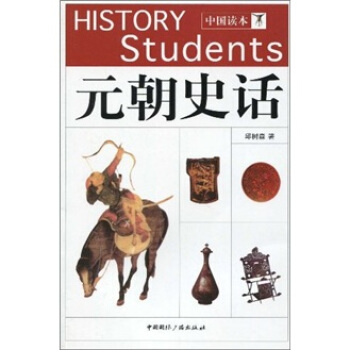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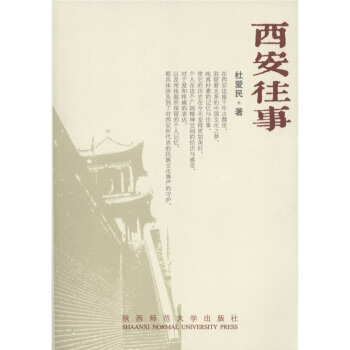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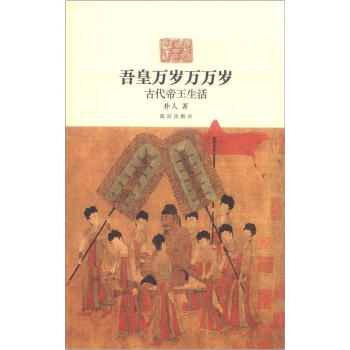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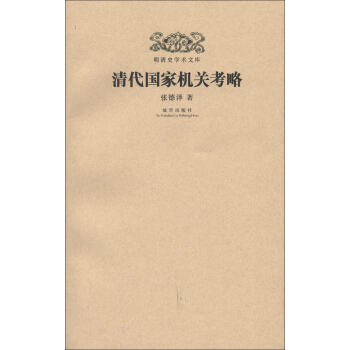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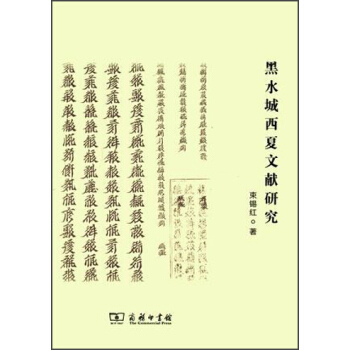
![大象學術譯叢:希臘文明中的亞洲因素 [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sa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279881/547e85b1N63069bd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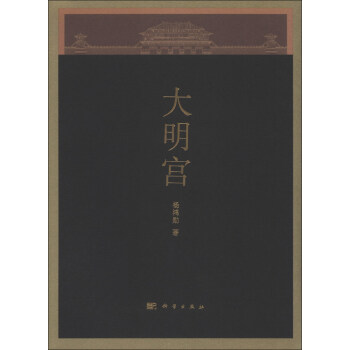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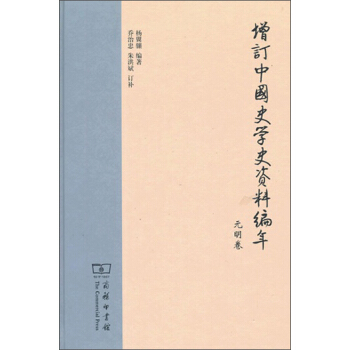
![大明帝國:洪武帝捲(套裝上中下冊) [The Great Ming Empire I Peculiar Found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Volume 1)]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04065/rBEhVlMKu84IAAAAAAMQD1ZkLeQAAJETAEythcAAxAn95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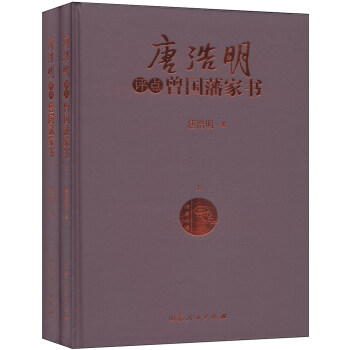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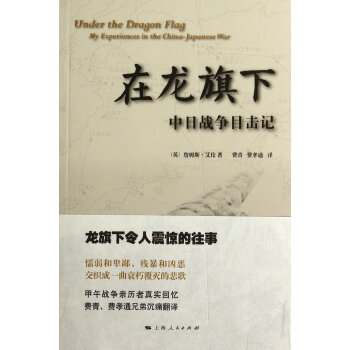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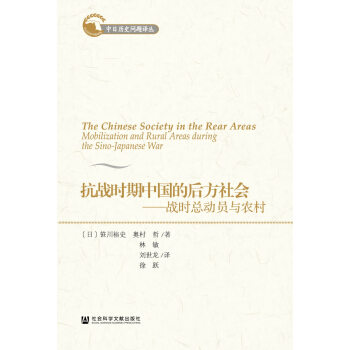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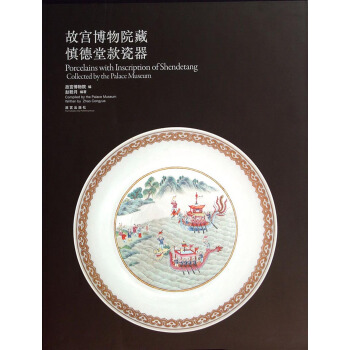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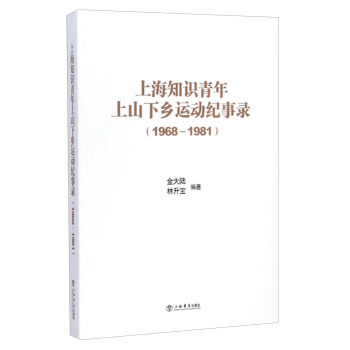

![第三帝國:巴巴羅薩(修訂本) [The Third Reich:Barbaross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49811/54d48a8bN22c8c21c.jpg)
![第三帝國:權力的中心(修訂本) [The Third Reich: the Center of the Web]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49817/54d48a8bN8706aec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