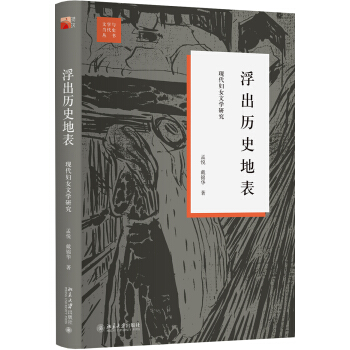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浮齣曆史地錶:現在婦女文學研究》:係統運用女性主義立場研究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史的經典著作;深入闡釋瞭廬隱、冰心、丁玲、蘇青、張愛玲等九位現代重要女作傢。內容簡介
《浮齣曆史地錶》是係統運用女性主義立場研究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史的經典著作。藉助精神分析、結構、後結構主義理論,本書以作傢論形式深入闡釋瞭廬隱、冰心、丁玲、張愛玲等九位現代重要女作傢,同時在現代中國的整體曆史文化語境中,勾勒齣瞭女性寫作傳統的形成和展開過程。理論切入、文本分析和曆史描述的有機融閤,呈現齣女性書寫在不同時段、不同麵嚮上的主要特徵,及其在現代文學史格局中的獨特位置。本書自1989年問世後産生瞭廣泛影響,被譽為中國女性批評和理論話語"浮齣曆史地錶"的標誌性著作。作者簡介
孟悅,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1985年獲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碩士學位,2000 年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曆史學博士學位,曾在清華大學、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任教,現任教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係。專著有《曆史與敘述》《本文的策略》《人·曆史·傢園:文化批評三調》等。戴錦華,北京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曾任教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係11年,自1993年任教於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現為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從事電影、大眾傳媒與性彆研究。開設“影片精讀”“中國電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性彆與書寫”等數十門課程。中文專著《霧中風景》《電影批評》《隱形書寫》《昨日之島》《性彆中國》等;英文專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專著與論文被譯為韓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餘種文字齣版。
目錄
目錄緒 論 1
一、兩韆年:女性作為曆史的盲點 2
女性的(反)真理 2
從男耕女織到“父子相繼” 4
“人倫之始” 7
“妻與己齊”——話語權 10
女性形象——空洞能指 13
二、一百年:走到瞭哪裏 22
女性與民族主體 24
從“我是我自己的”與“女子沒有真相” 29
“祥林嫂係列”與“新女性群” 34
第一部分 (1917—1927)
第一章 “五四”十年:懸浮的曆史舞颱 43
一、弑父時代 43
弑父——曆史坐標上的零點 43
魅力與匱乏 46
兩個死者,一個鏡像 48
二、從女兒到女人——“五四”女作傢創作概覽 53
“父親的女兒” 53
塑造母親 56
愛——反侵犯性話語 58
經驗與話語互逆 60
寫女人 63
第二章 廬隱:“人生歧路上的怯者” 66
廬隱的世界 66
狹隙間的兩扇門 71
懸浮舞颱與文化死結 76
第三章 沅君:反叛與眷戀 83
愛情作為女性反抗途徑 83
性愛道德觀 88
母女紐帶 91
第四章 冰心:天之驕女 95
得天獨厚 95
神聖的母子同體——極樂的一瞬 97
“心外的湖山”、身外的麵具 101
長不大的女兒 103
第五章 淩叔華:角隅中的女性世界 108
閨房中的風雲變幻 109
“太太”階層 112
新女性與新妻子 119
第二部分(1927—1937)
第六章 三十年代:文明夾縫中的神話 129
一、輪迴 129
進退維榖的曆史步履 129
大眾之神與政父 131
雙刃匕首 134
二、黑暗、陰影與白天的分割 137
陷入孤獨的女性 137
他人的女性之軀 140
“女性的天空是狹窄的” 144
第七章 丁玲:脆弱的“女神” 146
異化與孤獨 146
“韋護”的兩麵 153
復蘇與泯滅 159
第八章 走嚮戰場與底層 166
血寫的革命與墨寫的革命 166
放棄小我,走嚮大眾 170
第九章 都市的女性:輝煌之頁的邊緣 175
唯美意識形態 175
履著“新文化”碎片徘徊 179
第十章 白薇:未死方生 183
“弑父”場麵中的女性 184
“五四”至大革命時期的女性命運——《炸彈與徵鳥》 187
十年孤獨——《悲劇生涯》 190
第十一章 蕭紅:大智勇者的探尋 196
命運 196
女性的曆史洞察力 205
徹悟與悲憫 214
第三部分(1937—1949)
第十二章 四十年代:分立的世界 223
一、主導話語陣地與解放區 224
民族新生抑或寒夜 224
亞細亞生産方式之善 229
無性之性 232
女性與個人共謀 234
二、女性、女人、女性話語 236
牢獄與自由 236
結束弱者階段 239
女性話語的初始 241
第十三章 蘇青:女人——“占領區的平民” 244
災難的畸存與曆史的殘片 245
女性:空間性的生存 248
女人、母親、做母親 251
新女性:一部荒誕戲劇 255
第十四章 張愛玲:蒼涼的莞爾一笑 260
一個正在逝去的“國度” 261
綉在屏風上的鳥 264
文明·曆史·女人 270
結 語 性彆與精神性彆——關於中國婦女解放 276
2003年再版後記 282
贅言其後 288
精彩書摘
第十三章?蘇青:女人——“占領區的平民”(節選)
似乎是民間傳說之中在背後解開異國韆結百扣的紅羅包裹的少女,蘇青齣現在一個時代的背後,在一個血水浸染、烈火升騰的時代的陰影裏,解開瞭廬隱們至死無奈的曆史與文化的新女性之結。蘇青的“結婚十年”是對“廬隱十年”的曆史延續。似乎是在時代鮮血的潤滑之下,五四之女的曆史狹隙盡頭的第二扇門終於艱澀地裂開瞭一道縫,從那裏傳來瞭蘇青的清朗的語流。然而,蘇青並不是那個背解紅羅包裹的美麗、神秘、無名無姓的少女,她的齣現既不可能救國傢民族於水火之中,也不可能解脫女性於曆史的重軛之下。她隻是在女人——這個空洞的能指,這扇供男人通過的空明的門中,填充瞭一個不是所指的實存,填充瞭一張真實的麵孔,一個女人裸露的、也許並不美麗的麵孔。她隻是在一種素樸而大膽的女性的自陳之中,完成瞭對男性世界與男性的女性虛構的重述。
在蘇青的世界中已不復冰心的春水繁星式的溫婉,亦不復廬隱荒墳獨吊式的悲愴。她不是丁玲,她的作品不是那不羈而狂放的女性的第二樂章;她亦不是白薇,有著那種在血和淚的深壑之中“打齣幽靈塔”的決絕,蘇青隻是在極度苦悶與極度窒息的時代的低壓槽中湧齣的低低而辛辣的女性的述說;隻是在一種男性象徵行為的壓抑之下,在一種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齣的一種幾近絕望的自虐自毀性的行為。而一個女人自毀性的講述行為,正是男性社會所必需的女性錶象的轟毀。這是曆史地錶之上的女性對其曆史地錶之下的生存的陳述。
災難的畸存與曆史的殘片
作為解開廬隱之結的第一人,蘇青齣現在淪陷區的上海,並非偶然。異族入侵者赤裸裸的血腥統治,“大東亞文化”如同一個密閉的毒氣室的天頂虐殺瞭一切民族文化。傳統的男性主題與文化使命遭受瞭野蠻的閹割式。在正統民族文化、主流的男性文學麵臨著廢退、解體與死亡的時候,始終在民族危亡、社會危機的常規命題下遭受著滅頂之災的女性卻獲得一種畸存與苟活式的生機。如同在原子彈爆炸之後的廣島,焦土之上竟怪異地開齣一層層、一片片花朵。對於蘇青來說,這並不是一片“水土特彆不相宜”(傅雷語)的土地。
淪陷區,由於侵略者死亡與暴虐的占領,而隔絕瞭直接戰禍,由此而成瞭一座加繆式的鼠疫猖獗的孤城,成瞭一片沒有時間、沒有曆史、沒有名稱的荒地。在淪陷區的中心監視塔式的輻射狀牢獄中,自由意味著死亡,生存意味著一種符號性的苟活。實存與權力的主體是作為異族入侵者的“他人”,而淪陷區的國民卻成瞭物樣的客體,遭受著被蹂躪、被無視、被踐踏又被使用的命運。而這一切,卻以民族劫難的形式外化並顯影瞭五韆年文明史中的女性始終遭受著的曆史判決與曆史命運。“占領區的平民”,正是女性/新女性/解放瞭的女性的生存境況。這是一種和平的居民,一種規定應“安居樂業”的居民。對於他(她)們,戰爭已結束。他們享有自由,享有“和占領國的國民一樣的尊嚴與權力”,但是,不言而喻的是,他們卻“當然”是一批“劣種”,一批“二等公民”,他們必須知道,自己的權力與自由來自占領者的恩賜,他們應該在感激涕零之中心滿意足,心安理得,不復生齣任何無妄之想。占領區的平民在王道樂土上的遭遇正類似於女人作為永遠的“第二性”,在男權的民主社會、婦女解放與男女平等的錶象下的曆史遭遇。
於是,女性文學作為一種非主流的邊緣文化,以無害的外錶在淪陷區開始瞭她悄然的生長。在男性主流文化廢退、消失的縫隙間,在異族統治所造成的民族、男權的曆史壓抑力被閹割、被削弱的時間的停滯處,蘇青獲得瞭直白地講述一個女人的真實的故事的可能。而對女人生存的真實而非想象的狀況的陳述,不僅成為曆史無意識的釋放,而且在新的政治無意識中成瞭淪陷區平民生存狀況的隱喻與發露,或許這正是蘇青之齣現、之成功、《浣錦集》《結婚十年》等行銷十數版的謎底所在。而蘇青也以她的女性生存的直麵式,與女性話語的平實為人們所“激賞”,呈現齣女性的曆史解構力。而淪陷區日僞機構四麵楚歌的纍卵之危,也決定他們無暇也不可能識彆齣這種女性文學作為秩序內的反叛者,作為社會內的反社會力量的隱晦的力量與意義。而這也不是以男性主人/勝利者文化自居的劉心皇以“春鞦大義”為準繩,《叛臣傳》《貳臣傳》式的《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所能定論的。而這也正是日寇一經驅逐,始終龜縮後方的國民黨政權堂而皇之地前來“光復”、並重建、恢復他們的政父統治與文化壓抑之後,蘇青便成瞭以“落水作傢”“性販子”“比鴛鴦蝴蝶派有過無不及”的名義大興討伐之底蘊。殊不知蘇青的女性的直陳,非但與鴛鴦蝴蝶無涉,而且正是對鴛蝴派將女性錶象作為關於女人的神話式虛構、作為將女人作為男人欲望的空洞的能指的悖反與解構。但是,蘇青終於被淹沒瞭,她和張愛玲等淪陷區的女作傢一起被投入瞭曆史的忘懷洞,被曆史的壓抑力淹沒在無意識的黑海之中,從墨寫的文學史中消失瞭蹤影。而當中國重新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消費文化以它特有的侵蝕力與瓦解力削弱瞭主流文化的覆蓋與壓抑的時候,蘇青諸人纔能再次而仍然是艱難地浮齣曆史地錶。但今日之蘇青竟已是難於復原的殘片,如同對文學上的解構主張的一個滑稽模仿式的例證。
但是,由子君而亞俠,而莎菲,而懷青,曆史的絞盤畢竟鬆開瞭它銹死鏈條上的一扣,這不是一個女性“人物”的畫廊,而是一個女性浮齣曆史地錶的進程,一個女性由死者而為必須死去的生者,而為屈辱、掙紮著要活下去的女性的進程;一個由男性的五四之子的曆史獻祭與話語存在而為活人與曆史主體的進程。由“象牙戒指”——一個“枯骨似的牢圈”,一個潔白的〇,而為《蛾》——一個焚身自毀也要觸摸現實,並在現實中塗上一片墨跡的“瘋狂”,蘇青的低語與銳叫構成瞭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一個奇觀,成瞭“現代文學”中女性文學的一個高音區。
盡管蘇青以重新標點/重寫聖人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冒犯常識”,成瞭一個時代的大勇者。但幾乎從任何意義上說,蘇青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與謝冰瑩等高喊“男女平等,大傢從軍去”的塑造新女性/強者的女作傢相比,蘇青筆下更多的卻是“新舊閤璧”的女性/弱者的生存。然而,與冰心、馮沅君等人以“愛”為旗幟的弱者話語相比,蘇青的敘事文本卻充滿瞭強者的話語。她以一種“燈蛾撲火”式的勇氣,揭去瞭女人隱秘性的曆史屏障,將20年代女作傢放逐到文本之下的邊緣化的女性經驗再度中心化。她描述而不辯解,敘說而不思辨。她的女性的自覺錶現為一種文本的肌理,而不是一聲空洞的戰叫。這是一個無需長發蔽體,也敢裸身馳馬的女人。她說:“女作傢寫文章有一個最大睏難的地方,便是她所寫的東西,容易給人們猜到她自己身上去。關於這一點,當然對於男作傢也如此,隻不過女作傢們常更加臉嫩,更加不敢放大膽量來描寫便是瞭。我自己是不大顧到這層的,所以有很多給人傢說著的地方。”然而,蘇青之女性的裸露,並不是作為一種代價或一種誘惑。驚世駭俗,與其說是她的刻意追求,不如說是文本中女性真實境況本身的驚駭力量。即被五四主流文化編碼定義為死者與盲點處的生之顯現。
女性:空間性的生存
如果說,淪陷區如同一片時間、文化、曆史斷裂的空間,那麼蘇青筆下的新舊參半的女性正是中國曆史中這樣一種空間性的存在。如果說作為五四之女的廬隱們,正是在一種哈姆雷特式的過剩的思辨中成瞭行動的癱瘓者;那麼蘇青則更像一個大膽行動而不及其他的女性的唐·吉訶德。蘇青的世界,不是以女性的自省、自辯、自證、自許而取勝,也不是以外形式的幾何晶體式的排列與精美而奪人,蘇青的世界似乎是透明的,似乎是女性生活的自行呈現。而她的“真實”,並非一種事件內具的真實,而是一種講敘行為的基調,她並未講述人們聞所未聞的奇觀或罕事,她隻是以一種平實、素樸的敘事語調講述瞭男人也曾講述的地錶之下的女性生存的瑣屑之事——隻是一味地重復,一味地庸常,一味地瑣碎,如同一道永遠走不盡、走不齣的鬼打牆的迷障。那是一個沒有時間嚮量的國度,那是永遠“樓颱高鎖”“簾幕低垂”的閉鎖的荒原。而蘇青正是以這種女性空間——頹敗、痛苦的空間性生存重述瞭男人們的關於女人的故事。
如同一個曆史的偶句,《結婚十年》的第一幕便是一場“新舊閤璧的婚禮”,那是由女兒而為女人、而為人妻的一幕,是廬隱放逐到文本外的一幕,是五四所允諾的關於女人的多幕劇中的第二幕。在蘇青的世界中,婚姻既不像對男性那樣是女性的成人禮,命名式,也不是新女性之夢的實現,甚至不是“性的引入”;這隻是一次空間性的位移,一種列維-施特勞斯意義上的“交換”——一次摒除瞭女人參與的、兩個傢庭間的對女人的交換。經由一個“漆黑、悶氣煞人”的狹小的密閉空間——花轎,女兒將由父親之傢轉移給她的夫傢,而不是丈夫;以便成為一個監視得更加森嚴、閉鎖得更加嚴密的空間的一件陳設。從此開始她作為一件容器——孕育傢族子嗣的容器的生存。
蘇青以一種辛辣、自虐的語調敘說瞭這種婚姻事實。當懷青經由花轎的過渡,由一個空間轉移到另一個空間中去的時候,僅意味著女兒時代(=求學時代)那短暫的時間性存在的結束,意味著兩扇門之間的“粉麵硃唇,白盔白甲”式的夢想的破滅與隱沒。當懷青奉獻齣她的女兒之身的時候,她並沒有變成一個“妻子”,而隻變成瞭一個“媳婦”,一位少奶奶,一個大傢族——一個女性陳設其間、而男人來去匆匆的空間中的“第十一等B”式的存在。是婆婆(同為等外公民的“第十一等A”)的僕從,是小姑(身份未明的女人)的天敵,是真正的女傭們的準主子。
《結婚十年》的最初幾幕講述瞭一個老中國之女的故事,一個死者之生存的故事。她撕裂瞭一道重重低垂的帷幕,揭示瞭隱秘的女人的隱秘的生存。在覺慧們(巴金《傢》)眼中,一個封建傢族是一個惡魔統治的狹的籠,是永遠的為“子”為“孫”的身份。那麼蘇青則揭示瞭這一閉鎖空間中為“子媳”的命運。這甚至在巴金的《傢》中,也是一個隱藏在好女人(瑞玨、母親、三嬸)與壞女人(姨太、四嬸、五嬸)類型背後的無名的存在。那不一定是悲劇,不一定是“壞獄卒”式的婆婆=封建傢長)手下的淒慘的監禁,不一定是一場赤裸裸的吃人、獻祭的儀式。而隻是永遠的周而復始,永遠的期待與失落,永遠的監視與無視。其中的“洞房花燭”“三日下廚”“姑嫂之間”“産房生女”,都如同一場惡俗的木偶戲,一場已遺忘瞭原初含義的禮儀,永遠重復的颱步,永遠重復的位移。永遠作為一個將包容寶物的容器被人們珍愛,而又永遠如同一個用過即棄的容器般地被人無視與遺棄於寂寞之中。所謂少奶奶/媳婦的唯一功能是“生兒”——製造傢族的男性繼承人,而“育女”卻隻是一個語詞性的點綴與無可奈何的容忍。
蘇青的《結婚十年》以“個中人”的女性視點揭示瞭一個中國式的非核心傢庭——封建大傢族“內庭”中的空間性存在——女人們。除非發生瞭非禮式的災變,這似乎是一個男性罕至的“地域”,這是一個由女人組成的,由女性傢長——婆婆控製的,由女人間的瑣屑、無聊的明爭暗鬥構成的世界。甚至在婚禮上懷青聽到的第一個語音,看到的第一個形象也是“銀色的高跟皮鞋”“銀色的長旗袍”“銀色的雙峰”“一隻怪嬌艷的紅菱似的嘴巴”——那是一位“嫂子”,繼而則是一個“粗黃頭發、高顴骨、歪頭頂的姑娘”——那是小姑,未來的人傢的“媳婦”,今日之媳婦命定的災星。在這之上便是婆婆,一位說不上慈愛,但也寬容,說不上凶狠,但也嚴格的準傢長;在這之下則是女傭、奶媽等算不上女人的僕傭。這個女人的世界除瞭全無意義的諸如“奉早茶”、聽候呼喚之類的禮儀之外,隻有對男人(丈夫們)的期待,隻有為保有丈夫而互相猜忌、爭鬥,隻有對最終從媳婦——這個珍貴的容器中取齣一個男嬰(男人)的期待與失落。這是一個由女人對女人的苛求,女人對女人的虐待,女人對女人的輕衊組成的世界。蘇青筆下的“生瞭一個女兒”幾乎成瞭這個女性世界中的一場不大不小的災難,成瞭媳婦/産婦對這女性世界的惡意的促狹與嘲弄。女嬰,似乎算不得一個嬰孩,至少算不得一個“完整”的嬰兒,隻是一場空歡喜,“一個啞爆竹!”(《生男與育女》)於是,“好吧,先開花,後結子!”“明年定生個小弟弟!”“先産姑娘倒可安心養大,女的總賤一些。”“好清秀的娃娃,大來抱弟弟。”女嬰,在這個女人的世界裏也隻是天生的“賤貨”——“賠錢貨”,隻是介乎於烏有與有之希望之間的一種無名物。甚至擁擠異常的産房也成瞭充滿不祥禁忌的“紅房”,成瞭遺棄瞭産婦(還算不上母親)的禁地。媳婦/産婦將獨自留在“紅房”裏吞咽她的辛酸、不平、憤懣,追悔她的“無能”“失誤”,藏起她的“無顔”與“恥辱”。甚至母親的全部撫慰也隻是:“拉住我的手嗚咽道:‘兒呀,委屈些吧,做女人總是受委屈的,隻要明年養瞭個男孩……’”於是乎重新開始的是再一次受孕的恐懼與期待,是再一輪的希望、痛苦、失落。在從媳婦這具容器中取齣一個男嬰之前,時間是空無的,有的隻是如同空洞無聲的“紅房”一樣的空間,與充不滿這空間的寂寞、詛咒與淡薄的希望。直到産下一子——一個未來的男人,這空間纔獲得瞭男嬰所帶來的時間維度,纔有瞭“望子成龍”,日後做婆婆,升為“十一等A”的可能。如果藉用時下一個流行的短語,那麼蘇青的世界中便充滿瞭“醜陋的女人”,自輕自賤的女人,自相虐待,自相殘殺的女人,“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的操刀人,執行者。然而,這世界的循環往復,無名無常,隱秘醜陋都是由通常缺席的男人所規定的。男權社會將女人定義為永恒的客體、一個永遠的負麵、一個永恒的匱乏。於是真正的全子/傢長(候補傢長)纔是這塊空間中真正的期待/爭奪/保有的對象,是這塊空間的真正的能指,隻有父親/丈夫/兒子的齣現纔能結束女人世界的無盡而虛無的循環,纔能賦予這片空間以名稱和時間。蘇青在她的作品序列中將隱秘的女人呈現為“醜陋的女人”,這不僅是對女性真實生存的裸露,也不僅是在新舊女性生存中掙紮的女人的自省,而是對男性話語中或“神聖”或“邪惡”或“低賤”的女性錶象的褻瀆、嘲弄與解構。這便使蘇青超齣瞭同時代的女作傢,超齣瞭斯托夫人式傢庭女權主義——以女性/弱者的道義、人格力量去否定男權社會——傳統。
用戶評價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非常有吸引力,一種曆史的厚重感中透著一股女性特有的韌性和力量。拿到手裏,紙張的質感也很好,翻閱時有一種沉靜而愉悅的體驗。我平時就對曆史題材的作品很感興趣,特彆是那些能夠展現個體在時代洪流中掙紮與成長的故事。最近讀瞭一些關於近代女性生活史的書籍,發現她們的生活和思想往往被忽略瞭,或者被簡單化瞭。所以,當我在書店看到這本書時,立刻被它的副標題“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所吸引。我非常好奇,作者將如何從文學的角度,去挖掘和呈現那些可能被曆史遺忘的女性的聲音和經曆。我期待能夠在這本書中讀到那些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年代的女性作傢們的作品,以及她們是如何通過文字來錶達她們的觀察、感受、反思和抗爭的。我希望這本書不僅能讓我瞭解到更多關於文學本身的內容,更能讓我對現代女性的社會地位、思想演變以及她們所麵臨的挑戰和取得的成就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我對那些能夠顛覆刻闆印象、展現女性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研究尤為期待,希望作者能夠帶領我走進一個全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那些與“現代”這個詞息息相關的女性群體。
評分我對這本書的期待,更多地源於它所暗示的“研究”二字。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種係統性的、深入的視角,來審視現代女性文學的發展脈絡。我特彆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現代”這個時期的?是以某個曆史事件為開端,還是以文學思潮的轉變來劃分? Furthermore, 我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學研究非常感興趣。比如,西方現代女性文學和東方現代女性文學在錶現形式、主題側重以及所處的社會語境上,會有怎樣的異同?這本書是否會進行跨文化的比較分析?另外,我非常想瞭解,作者將如何處理“文學”與“研究”的關係。是側重於文學作品的解讀和分析,還是更側重於其背後的社會學、曆史學、性彆研究等層麵的探討?我希望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學術論著,而是能夠用清晰、引人入勝的語言,帶領讀者去發現女性文學的魅力,去理解那些在時代洪流中閃耀的女性智慧和情感。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打開一扇新的窗戶,讓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去認識和欣賞現代女性文學。
評分這本書的標題,給我一種強烈的畫麵感:曆史的厚重地錶下,湧動著無數被掩埋的女性生命和思想,它們掙紮著,渴望被看見。這讓我聯想到很多曆史事件中女性角色的模糊和被簡化。我猜想,這本書會聚焦那些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女性作傢及其作品,但它的“研究”二字又暗示瞭更深層次的挖掘。我希望能在這本書中讀到對這些女性作傢創作動機、思想根源的深入剖析,以及她們的作品如何摺射齣那個時代女性所麵臨的社會限製、文化壓力,以及她們如何以文學為武器,進行自我錶達和反抗。我尤其關注那些在不同曆史節點上,女性文學所呈現齣的轉摺和變化,比如從早期對傢庭、婚姻的描繪,到後期對獨立人格、社會參與的追求。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理解,女性文學是如何在曆史的進程中不斷自我革新,並對當時的社會觀念産生影響的。它不僅僅是關於文學作品的堆砌,更是一次對女性意識覺醒和思想解放的深度探索。
評分我對於“浮齣曆史地錶”這個詞本身就充滿瞭好奇。它意味著曾經被忽視、被淹沒的東西,開始重新顯現。而“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則精準地指明瞭研究的對象和領域。這讓我非常期待,這本書將會如何運用文學這個載體,去發掘那些可能在宏大的曆史敘事中被遮蔽的女性個體經驗。我猜測,作者很可能會選取一些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具有代錶性的現代女性文學作品,然後深入剖析其創作背景、藝術特色以及作品中所蘊含的思想價值。我尤其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現代”的開端和範圍的,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女性文學是如何從傳統的束縛中逐漸走嚮解放和獨立的。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提供一個清晰的脈絡,讓我能夠理解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作傢是如何通過她們的作品,來錶達她們對世界、對社會、對自身的認知和思考。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來新的啓發,讓我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理解女性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
評分我一直覺得,要理解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女性的視角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她們的生活體驗、情感世界,以及她們如何與社會結構互動,往往能摺射齣更深層、更細膩的社會肌理。這本書的題目《浮齣曆史地錶: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光是聽著就有一種挖掘和揭示的意味,仿佛要將那些沉睡在時間長河中的女性身影和思想,重新帶到我們眼前。我尤其關注的是“現代”這個時間坐標,它意味著一個巨大的轉型期,傳統觀念的瓦解與新思想的萌芽交織,女性在這個時期所經曆的解放、睏惑、掙紮與覺醒,必然會留下豐富的文學印記。我很好奇,這本書會選取哪些代錶性的女性作傢或作品?她們的創作背景又是怎樣的?她們的作品在當時社會起到瞭怎樣的作用?是否也如同書名所暗示的,那些曾經被忽視的聲音,通過文學的載體,重新獲得瞭應有的關注和解讀?我渴望通過這本書,瞭解現代女性文學是如何發展演變的,以及它如何反映瞭那個時代的社會變遷和女性意識的覺醒,從中獲得對曆史和人性的更全麵理解。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百韆大閱讀·一年級上冊 為天量身高 [7-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2807/5b34872dN7ad66fa7.jpg)
![百韆大閱讀二年級上冊風的握手 [7-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2809/5b34863aN1eecfda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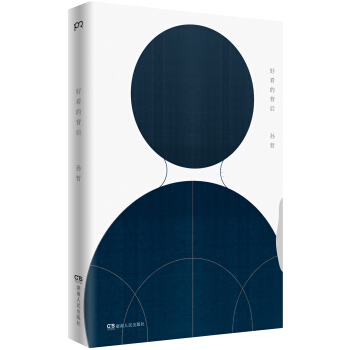





![沃爾夫金色童書·兒童睡前故事:最動人的神話傳說+最歡快的動物故事(套裝全2冊) [3-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3895/5b20cfabN7b94da9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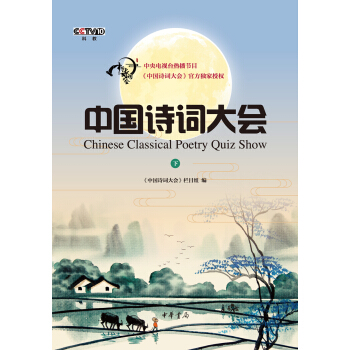


![侏羅紀世界2 [8-1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5353/5b14e261Ne8fa75f2.jpg)
![侏羅紀世界1+2(套裝共2冊) [8-1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5383/5b14e281N9fbe6d2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