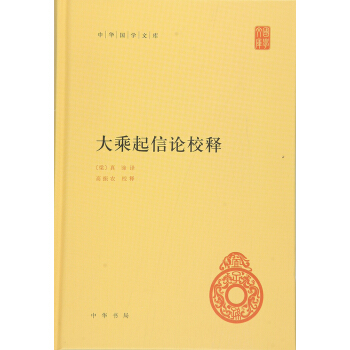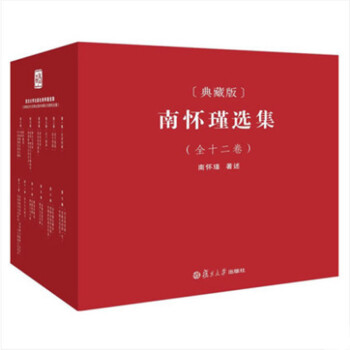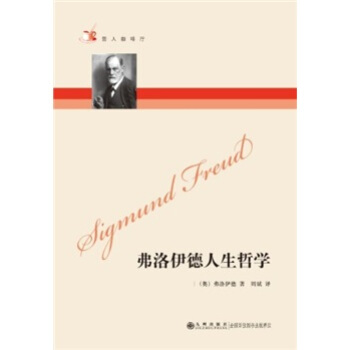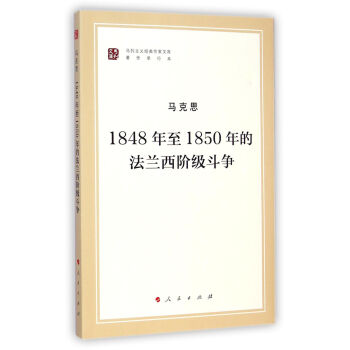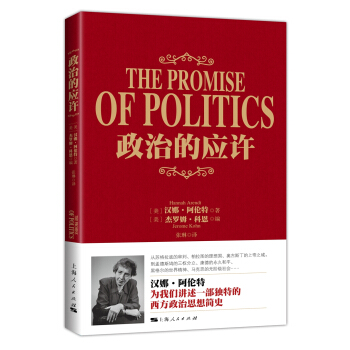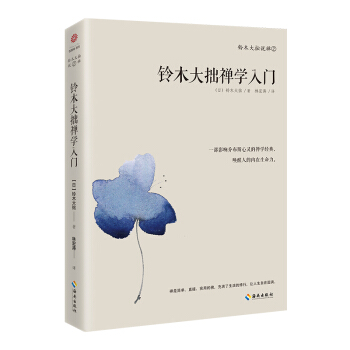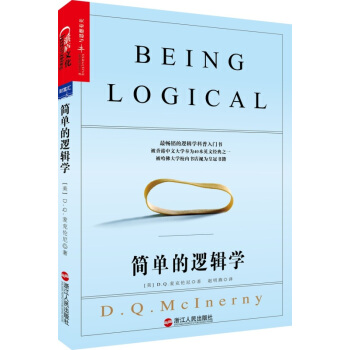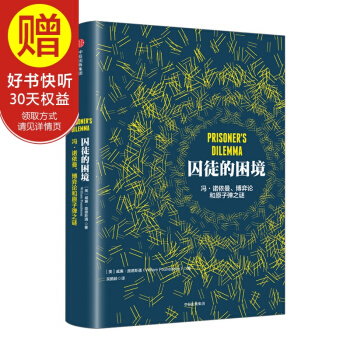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经典与解释”又发新枝,推出新的子系列——“世界史与古典传统”;新枝上的新叶,就是这本《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由“经典与解释”总主编刘小枫教授亲编。此书一如既往发源于刘小枫教授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对中国问题的迫切关怀:当中国逐渐步入世界历史大舞台的中心之际,该如何从中国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来理解世界历史?
让编者领你进入他的问题意识,带你认识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以及西方人理解历史的历史,进而转过身来认识我们自身。
内容简介
盛世之下的中国急需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这不仅包括认识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也包括认识西方理解世界历史的历史。现代世界并非一朝而成,西方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经历了较长岁月的演变,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核心观念是:“普遍历史”“世界史”“历史主义”。这些概念及其之间的关联,远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尽。我们的史学理论界已经翻译积累了一些基本文献和研究文献,但还远远不够。本书针对我国学界认识上的一些薄弱环节,选译一些具有代表性但尚无中译的重要原典作家(博丹、波舒哀、杜尔哥、赫尔德、席勒、兰克),同时注重相关研究文献。这些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展现出现代世界生成的内在机理,从而将有助于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如下迫切的理论问题:当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之际,我们应如何从中国文明自身的立场和角度理解世界历史?目录
编者说明(刘小枫) / 1原典选译
博 丹 学习历史的次第 / 2
波舒哀 论圣史和俗史 / 17
杜尔哥 普遍历史两论提纲 / 37
杜尔哥 政治地理学 / 99
赫尔德 各民族趣味兴衰的原由 / 119
席 勒 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 / 158
兰 克 论普遍历史 / 179
研究文献
克瑞格 历史主义:通史的早期史 / 198
雷努姆 波舒哀的《论普遍历史》 / 237
安布勒 施特劳斯讲维科 / 270
柯瑟尔 兰克的普遍历史观念 / 296
莫米利亚诺 重审历史主义 / 317
瑞维斯论 今天的世俗史学者 / 327
科瑟勒克“历史/史学”概念的历史流变 / 335
前言/序言
出版说明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都是GDP世界第一,至1840年代,中国武力遭遇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从此中国不再是全球经济的老大哥和亚洲人向往的文化中心,而沦为西方列强主宰下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1949年之后,中国一直处于两极世界秩序的“中间地带”,成为附着于两极斗争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1980年代以来,中国开创的经济奇迹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融入,这意味着中国又转身成为“走向世界”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
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和文化问题也会随之得到解决。可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和文明地位果真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而飙升了吗?要知道,日本经济在战后崛起,其世界政治地位却并未随之提升。美国人一面在经济上与中国加大合作,另一方面却在政治上对中国大加挞伐,这些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身位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世界秩序设想,“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难道不够高明?但毕竟,如今的世界秩序产自欧洲并由欧美接力领导,经济崛起反倒显得中国的国家肉身(地理—经济)逐渐获得世界性,而中国的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却试图在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中安身。
盛世之下的国朝更应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世界的生成与展开并非一蹴而就,唯有在世界史和有关世界史的书写中寻觅踪迹;世界史绝非诸种国别史的代数相加,而更多是各国历史的几何交错。晚清以降,华夏大地认知世界的热望高涨,遂有传教士的若干编译着作: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等等;此外还有国人编译的《四洲志》、《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寰志略》等;梁思成等人翻译的韦尔斯《世界史纲》颇为流行,但旋即遭雷海宗撰文批评其欧洲中心论。随后的历史际遇使汉语学界没能拾级而上,追溯欧洲人在“世界”生成时刻的世界史书写,却转而编撰汉语的世界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周谷城先生的《世界通史》,此书三易寒暑于1949年出版。
国人这部世界通史的结尾是《明夷待访录》的大段直引,岂是偶然?马礼逊辞典将history译作“纲鉴”,亦颇有深意。以是观之,立足华夏大地,译介欧美世界有关世界史的书写与再书写,绝不仅是单纯了解各国风俗,而是了解现代世界的生成机理,更无疑是在华夏文明又起一程的新时代使用密藏那笔墨(miseenabyme)的笔法正视我们自身。保国、保种、保教的历史使命必须也只能在世界叙事中完成。
职是之故,本丛书重点译介两类图书:其一,现代早期以降欧洲本土产生的世界史作品;其二,有关现代早期“世界”及“世界史”生成的研究作品。也可考虑在既有作品之外,编译相关主题的论文,结集成册。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丁组
2017年4月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吸引人,那种厚重又不失典雅的质感,拿到手里就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封面选择了比较克制的暗色调,配以烫金的书名和作者信息,显得非常大气。我特别喜欢它内页的纸张选择,那种略带米白的颜色,阅读起来非常舒适,对眼睛的负担也小了很多。排版上也看得出是用心了,字号大小适中,行距也处理得当,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疲劳。整体来看,从外在的包装到内在的阅读体验,这本书都展现出一种对知识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友好,这在当今快餐式的出版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让人忍不住想细细品味。
评分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安排体现了极高的逻辑性和宏观视野。它似乎遵循着一个精心设计的“螺旋上升”的结构,每一章节都在前一章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使得整体脉络清晰可循,即便内容涵盖的时间跨度和思想领域非常广博,读者也不会感到迷失方向。作者巧妙地在叙事主线中穿插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和思想家的对话,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理论探讨变得生动起来。读完全书,我感觉自己的知识地图被极大地扩展和重塑了,它不仅提供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理解人类社会进程的全新视角和分析工具,其带来的思维冲击是持久而深远的。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智力探险。它并非那种提供标准答案或简单因果链的通俗读物,而是更像一把精巧的钥匙,引导读者去质疑既有的历史叙事框架。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批判性的精神,他不断地挑战那些被奉为圭臬的传统观念,并以扎实的论据和逻辑链条来构建新的解释体系。这迫使我不断地停下来,反思自己过去对某些历史阶段或思想流派的固有认知。这种“被挑战”的感觉,正是学术著作最宝贵的价值所在——它激发了读者内心的求知欲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一味地接受信息。
评分我必须提到这本书的引用和参考体系,这简直是学术研究的典范。每一处引述都标注得极其清晰和规范,作者显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进行文献梳理和考证。对于一个有深度阅读习惯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因为它为我后续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可以直接追溯到原始资料的出处。更重要的是,这种严谨的态度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作者的观点是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而非空中楼阁般的臆测。翻阅那些密密麻麻的脚注和尾注,我感受到的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对治学严谨性的由衷敬佩。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风格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精准,时而如涓涓细流般娓娓道来,细腻地勾勒出时代的变迁与思想的演进;时而又像是激流勇进,将复杂的理论和宏大的历史图景以一种极其凝练而有力的笔触呈现出来。我发现作者在遣词造句上颇有功力,既有学院派的严谨与深刻,又不乏文学性的韵味和感染力。尤其是一些对关键概念的阐释,他总能找到一个极其贴切的比喻或者一个极富洞察力的视角,让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瞬间变得清晰明了。这种行文的高超技巧,使得阅读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享受,让人在跟随作者的思绪起伏中,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现场。
评分真的不错哦,年底物流压力这么大,还能及时送到
评分内容充实,文字耐读,排版设计舒服,很有料的一本书,满意!
评分很好,重要的参考书,不可不看。
评分非常好的书,是从活动时买的,划算。
评分值得一读的书,非常好
评分内容充实,文字耐读,排版设计舒服,很有料的一本书,满意!
评分好书值得认真对待,沉心阅读。
评分好书值得认真对待,沉心阅读。
评分很满意,京东很给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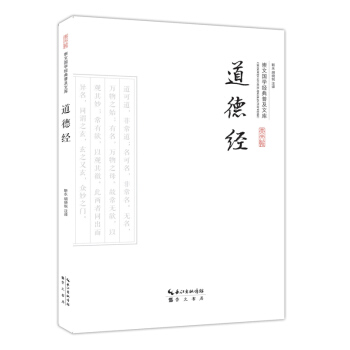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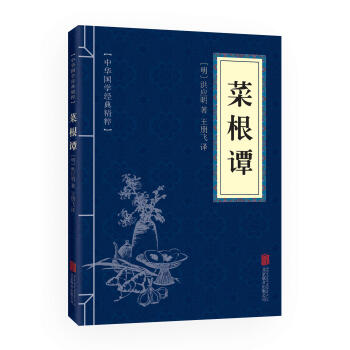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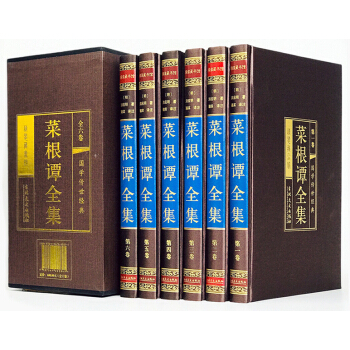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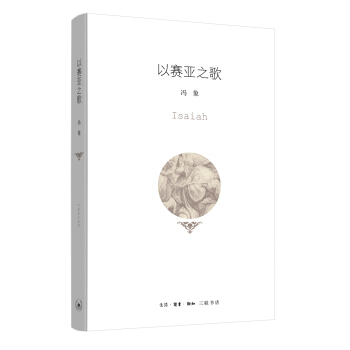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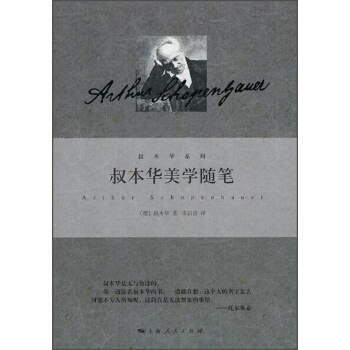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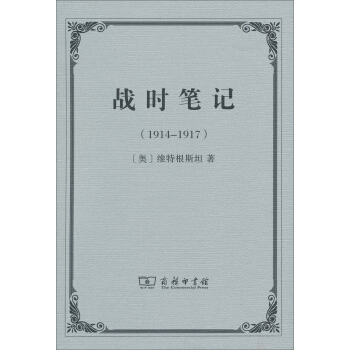
![让思维自由 [Out of Our Minds:Learning to be Creativ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49846/54debe21N5422a7f0.jpg)
![荣格心理学与藏传佛教 [The Essence of Jung’s Psychology and Tibetan Budd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04704/557685f8N1271866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