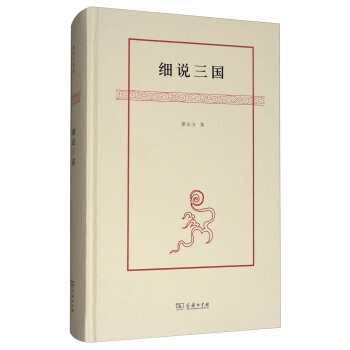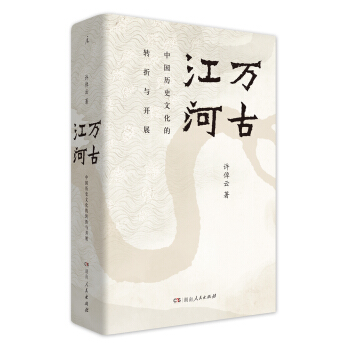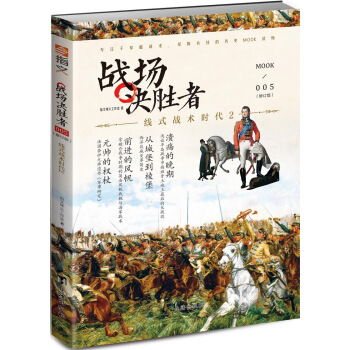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故宫藏美(插图典藏本)》为朱家溍谈古代艺术的学术随笔集,共分古代书画、古代工艺美术、清宫戏曲三个部分。内含《清代院画漫谈》、《雍正年的家具制造考》、《南府时代的戏曲承应》等文章。目录
怀人天气日初长(朱传荣)辑一
汉魏晋唐隶书之演变
清代院画漫谈
从旧藏蔡襄《自书诗》卷谈起
元人书《静春堂诗集》序卷
大米和小米
从旧藏沈周作品谈起
清高宗南苑大阅图
关于雍正时期十二幅美人画的问题
来自避暑山庄的一件画屏
《国子监敬思堂补植丁香图》诗卷小记
几净闲临宝晋帖窗明静展游春图
观真迹展览小记
辑二
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
牙角器概述
元明雕漆概说
雍正年的家具制造考
龙柜
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
明清帝后宝玺
清代后妃首饰
辑三
南府时代的戏曲承应
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
升平署时代“昆腔”“弋腔”与“乱弹”的盛衰考
升平署的最后一次承应戏
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
附录
朱家溍简要年表
精彩书摘
《故宫藏美(插图典藏本)》:关于雍正时期十二幅美人画的问题
《紫禁城》1983年第四期(总第二十期)所载《雍正妃画像》,系黄苗子先生撰文,故宫博物院提供照片。这十二幅画,故宫博物院很早就公开陈列过。
关于画像的名称问题,最早也是我说过:“可能画的是雍正的妃。”因为画中墙上有“破尘居士”题字,并钤“圆明主人”玺等,都说明是雍正的亲笔;而画中室内外的背景都是写实的画法,并且地道是那个时代的家具陈设;所绘人物面貌也近似肖像的画法,因此我这个估计就被许多同事所认可,并且曾以《雍正十二妃》的画名出现过。
我记得我还曾经纠正说:“我虽然说可能是雍正的妃,但看来只是四个女子的面貌,不像十二个女子的面貌。”黄苗子先生受《紫禁城》双月刊编辑部的约请,撰文介绍这十二幅画像时,还和我电话联系过,他同意我的看法,没写十二妃,把题目写作“雍正妃画像”。
这十二幅画自从我说过“可能是雍正的妃”,多年来“可能”二字逐渐被人去掉,演变为就是雍正的妃。在黄苗子先生撰文和我电话联系时,如果我还坚持必须说明仅仅是“可能”,那么黄先生一定会重视我的意见,文章题目也就不会定为《雍正妃画像》,而我当时没有坚持,现在我先向苗子先生检讨我的错误。
今年(1986)因为研究清代木器家具的制作,看到清代内务府档案中木作的记载,其中有一条:“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持出由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拆下美人绢画十二张,说太监沧州传旨:着垫纸衬平,各配做卷杆。钦此。本日做得三尺三寸杉木卷杆十二根。”根据这条档案材料,昔日往事记忆犹新,当年我曾在延禧宫库房工作时,为这十二幅画编过目。
记得这十二幅画是托裱过的,但没有天杆,没安画轴,当然也没有轴头,除画心本幅以外,只是四周有绫边,托裱相当薄软,平整毫无浆性,每幅画有一根杉木卷杆,比一般画轴要细得多。最近居然我还找出了当年我自己写的编目笔记,记载的尺寸和上述档案完全相符。这十二幅画每幅用杉木卷杆卷着,收贮在库房很多年,除我以外,凡当年在延禧宫库房管理过书画的同事,一定还有人记得此情形。这十二幅画正式托裱成轴是近年的事。
当初只是根据画的时代特点和题字,估计有可能画的是雍正妃,现在新发现了这条档案,已经证明没有这个可能了。因为根据清代内务府档案记载惯例来分析,凡“裱作”托裱妃嫔们的画像,都是记载为“某妃喜容”“某嫔喜容”“某常在喜容”等等,都是书以名号的,最概括的写法,也要称之为“主位”。以这十二幅画而论,如果是雍正之妃,或雍亲王时期的侧福晋,无论当时她们是活人还是已经死去的,最低限度当年也曾经是侧福晋,那么到了雍正十年,在档案上也要概称为“主位”,不能写作“美人绢画十二张”。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十二幅不是雍正妃的画像,只是“美人绢画十二张”(图二十、二十一)而已。
这十二幅画中的题字,很明确是尚为雍亲王时期的胤祯亲笔,当年贴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的。画中的家具和陈设都是写实,例如那“黑退光漆”“金理钩描油”“有束腰长方桌”“彩漆方桌”“波罗漆方桌”“斑竹桌椅”“彩漆圆凳”“黄花梨官帽椅”“黄花梨多宝格”,桌案和多宝格上陈设的“仿宋官窑”瓷器、“仿汝窑”瓷器、“郎窑红釉”瓷器,以及“剔红器”“仿洋漆器”和精致的紫檀架、座等等,都是康熙至雍正时期家具和陈设最盛行的品种。
对于这十二幅画,现在我有个建议,应另取一个名称,是否可以叫作《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十二幅,或者叫作《深闺静晏图》十二幅。
……
前言/序言
怀人天气日初长朱家溍先生是我的父亲,他1914年出生,2003年去世,离开我已经十年了。
这本书的部分文章是从父亲的文集《故宫退食录》中选出的,少数是编辑搜集补充的。
编校近尾声,责任编辑朱玲希望我写一点有关父亲的文字。
以谈论古代艺术为主题重辑父亲的文字,目的当是为更加宽泛的读者群提供一些他们之前或许未加关注的内容。艺术关注的是人,是人的生活体验与感情。观察前人对艺术的种种态度,其实也是观察他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要称赞编者的用心。
父亲一生爱戏。十三岁登台演出《乾元山》开始,八十六岁以《天官赐福》告别舞台,“没有加入任何票友组织,也不专以演戏为主。但他由看戏而演戏,由学戏而演戏,都属于业余爱好性质,完全从兴趣出发。不过嗜之既深,则力求钻研深造,从而向专业演员请教,并一招一式地从名师学戏”(吴小如先生语)。舞台实践七十年,竟然超出他服务故宫博物院的年头。投入的精力与研究的方式也是很少见的。他在《学余随笔》中介绍学习余派的过程,颇为独特,“我们把反复经常听余的唱片叫作‘临帖’。‘临帖’和一般听唱片的听法又不同。必须在安静无干扰的环境,把转速和音量都减弱,把耳朵贴近音箱,这样可清楚地听出念字、气口和发声的层次,也就是说怎样用嗓子和找韵味。在戏院里听,只是观众席中所听到的效果,而在‘临帖’时,则能听出唱法要领。我和余先生不认识,没有到他家听他吊嗓子的机会,只有‘临帖’这个办法,就像在吊嗓子的人面前听唱一样,不同的字,不同的工尺,用不同层次的发声,在转折的地方用不同的‘擞儿’”。
正是基于这样精细的体察,深入的研究,在排练演出久已绝迹舞台的《牧羊记?告雁》一出时,吴小如先生称赞,“可以说完全自出机杼,一空依傍”;“在唱念方面竟完全用余派的劲头、风格来表达,当然其艺术效果也甚得余派三昧”。
戏剧之外,书画也是父亲极大的爱好,但一生中少有平静安生的大段时间让他从容游弋其间。论书,父亲不及大伯父恣意纵横;论画,父亲以为不过是面貌不恶劣,略似古人罢了。即便是对古代书画的研究,也因为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中断,持续终生的倒是心中永不衰减的对美的欣赏,揣摩。
抗战时期,父母从即将沦陷的北平向后方出发,在交通多处中断的情况下,用五十天到陪都重庆,使用了近代中国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长途的步行。这一段经历,他们都常常说起,以致其中许多细节都刻在我脑海中,让我得以细细体会父亲在艰难环境中那种发现美好的情怀。
“走到洛阳,先经过龙门,伊川的山光水色使人精神为之一爽,连日的风尘疲惫仿佛一洗而空,站在卢舍那佛的座下,仰视慈容,感觉好像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伊阙佛龛的碑文在家时只看到拓本,现在看见原石,更觉亲切。
“也是去后方的路上,坐闷罐车到华阴,当时天黑又下雨,下车未出车站。次日天明时出去上厕所,走出候车大厅,雨过天晴,眼前一亮,很突然的看见了华山的全景。原来站的地方正面对华山,像一幅长的画卷,苍龙岭、莲花峰等等胜景都在眼前,当时不由得就想起了王世贞的诗中有‘太华居然落眼前’之句。这个‘居然’正是我此刻心头所感。”
“文化大革命”中,到湖北的五七干校,那是个湖区。干校在湖里抽干了水,种稻子。父亲当时是连队里的壮劳力,不少苦活会分配给他。譬如,插秧之前的育秧,遇下雨的时候,要派专人看管秧池,不能让秧池里的水没过秧苗,一旦池内水多了就需用盆把水淘出。此项工作有个专门名词叫“看水”(看,读“刊”音,守望之意),“看水”便要站在池边守候一夜,直到天亮才能回连睡觉。事后父亲也常说起,“这项工作虽然苦些,但也有意想不到的享受,就是雨天的雷电之美是原来从未看到过的,有一次竟然看到从天而降的一个大火柱,通天到地,真是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这是在室内所不能想像的”。
小时候家里只一个炉子,做饭,做水,取暖,全用它。总是觉得那时候的冬天真冷,老也过不完。可指不定哪一天早晨,父母会指给我们看,西屋的北墙上来了一小块阳光,这时我们就会知道,“春来了”。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开始看春的大小,看春来的时刻,看春在墙上的位置。
春的到来成了家里专用的物候标志,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我们兄妹四人的生活中,至今如此。
古人曾说,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见者,亲也。
父亲留给我们兄妹的不是他的天赋,不是他的出身,不是他的学识,而是他的情怀,对自己的爱与尊重,对美和好的欢喜赞叹。
想起父亲写过多次的一幅联,“契古风流春不老,怀人天气日初长”,是古人集兰亭字的对联,念之诵之,口气平淡而欢欣,让人格外难忘。
是以为序。
用户评价
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惊喜,在于它成功地将“高雅”与“易读性”结合起来,打造出一种跨越年龄层的阅读体验。我试着把这本书带给一些对传统文化不太感兴趣的朋友看,结果他们也被那些色彩斑斓的服饰和造型奇特的陈设深深吸引住了。这得益于作者巧妙的叙事结构,没有故作高深地堆砌术语,而是像一位富有激情的导游,带领读者游览故宫的宝库。例如,在介绍古代钟表时,作者不仅解释了其复杂的机械原理,还生动地描绘了它们在宫廷生活中的娱乐和象征意义,使得这些冰冷的器物瞬间“活”了起来。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美”是流动的、是有生命的,它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一次愉快的文化探险,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与历史的温柔对话,让人在浮躁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是绝对值得收藏和反复品味的精品。
评分坦白讲,我一开始对这类“大部头”的艺术鉴赏书籍是有些抗拒的,总觉得内容会过于专业和晦涩,但这本书完全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它在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上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譬如,在介绍某一类瓷器时,它不仅展示了器物本身的美感,还穿插了那个时代烧制工艺的技术细节,以及它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和地位,这种多维度的解读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理解。我特别留意了关于玉器的部分,那些温润的质地和鬼斧神工的雕刻,书中通过不同角度的特写镜头,将玉石的油脂光泽和雕刻的精细层次感展现得淋漓尽致。阅读时,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反复摩挲那些图片,甚至会忍不住去想象工匠们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所倾注的心血与技艺。这本书的排版设计也值得称赞,留白恰到好处,使得原本密集的文字信息不至于让人感到压迫,阅读体验非常舒适流畅,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它更像是一位博学的故宫专家,坐在你身边,用最亲切的语言为你娓娓道来每一件珍宝背后的故事。
评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我对这本书的印刷质量和图像处理水平非常关注。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套书的图片质量达到了专业级别的水准。光影的层次感、色彩的饱和度以及细节的锐利度都处理得非常到位,这对于欣赏那些对光线极为敏感的文物(比如珐琅彩或者镀金器物)来说至关重要。我注意到,书中的一些细节图特写,其分辨率之高,甚至能清晰地看到釉面上的微小气泡或是金缮修复的痕迹,这种坦诚的展示,反而更增添了文物的真实感和历史厚重感。此外,这本书的装订工艺也体现了其典藏价值,书页夹层牢固,即便是经常翻阅,也不会担心书页松动或脱落。这让我可以放心地将它作为一本工具书来使用,随时查阅和对比。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在技术层面上对原作最好的致敬,让远方的文物得以近距离、无损耗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对我而言,远超出了单纯的“图册”范畴,它更像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美学史。我最欣赏它在选取藏品上的独到眼光,避开了那些被过度宣传的“网红”文物,而是深入挖掘了一些相对低调却更具时代代表性的艺术精品。比如,对于一些早期书画作品的介绍,它不仅仅停留在对笔墨技巧的分析上,而是深入探讨了其精神内核与时代思潮的碰撞。文字的运用非常考究,作者似乎深谙如何用最精准的词汇描绘出那些难以言喻的“意境”。每一次翻阅,我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感悟,这可能就是“典藏本”的魅力所在——它经得起反复的品味。我甚至会根据书中的描述,对照一些我曾经在博物馆看到的实物,那种在书本中重温和细致观察的感觉,让人对文物的记忆更加鲜活和立体。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能够沉淀心灵、提升审美层次的佳作,是书架上不可或缺的一员。
评分这本《故宫藏美(插图典藏本)》的书名听起来就让人心生向往,一拿到手,厚重而典雅的装帧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封面设计非常有格调,那种沉稳的色彩搭配上精美的纹饰,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迫不及待地翻开内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幅幅高清的彩印插图,色彩还原度极高,细腻的笔触仿佛能将你带到那个辉煌的宫廷之中。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清代宫廷服饰的章节,那些精巧的刺绣、华丽的材质,通过书中的图片和文字描述,我仿佛能触摸到丝绸的质感,感受到皇家服饰的庄重与华贵。文字部分的编排也十分用心,并非那种枯燥的学术说教,而是将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娓娓道来,读起来轻松却不失深度。对于我这样一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扇通往中华瑰宝的窗户,它让我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些国宝级文物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那种在指尖翻阅、在眼前欣赏的愉悦感,是任何电子设备都无法替代的。
评分发货速度独步全网,促销力度冠绝全网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值得一读的好书,
评分我为什么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因为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我为什么每个商品的评价都一样,因为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订单,所以我统一用段话作为评价内容。网上购物这么久,有买到很好的产品,也有买到比较坑的产品,如果我用这段话来评价,说明这款产品没问题,至少85分以上,而比较糟糕的产品,我绝对不会偷懒到复制粘贴评价,我绝对会用心的差评,这样其他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作为参考,会影响该商品销量,而商家也会因此改进商品质量。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打折购入 商品未拆 京东物流很快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发货速度独步全网,促销力度冠绝全网
评分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