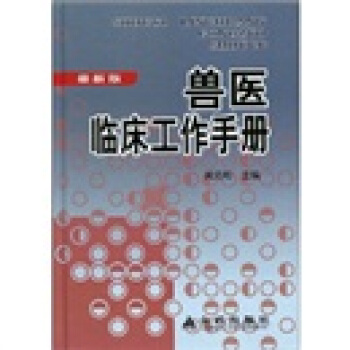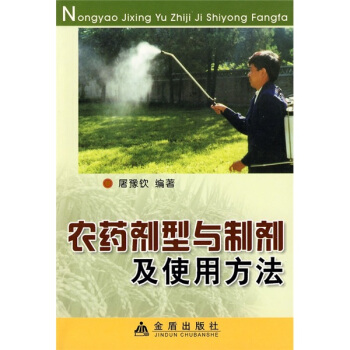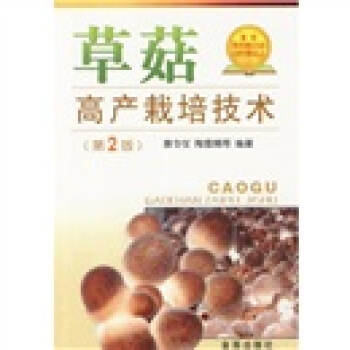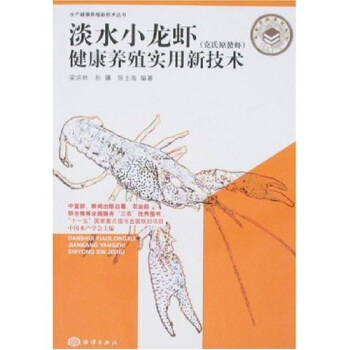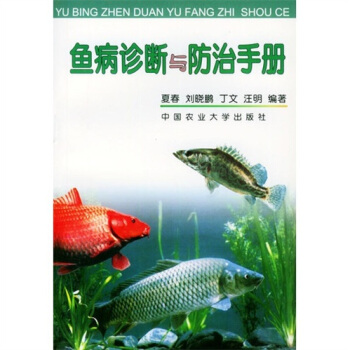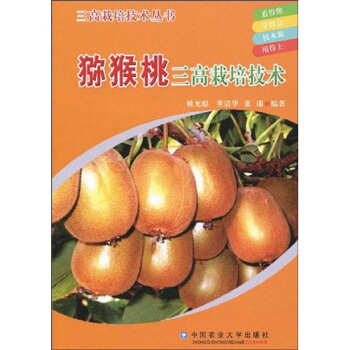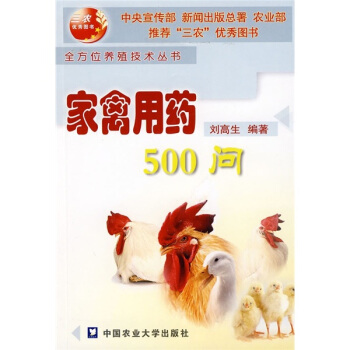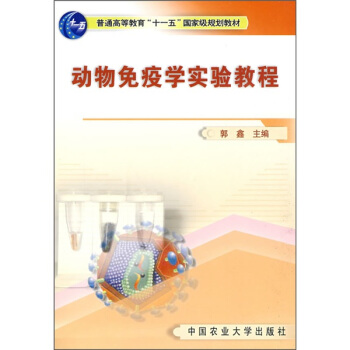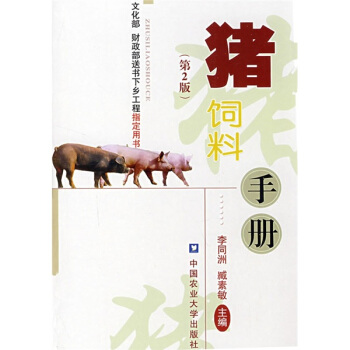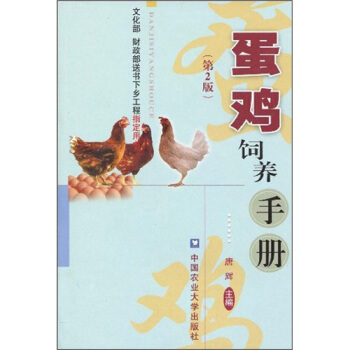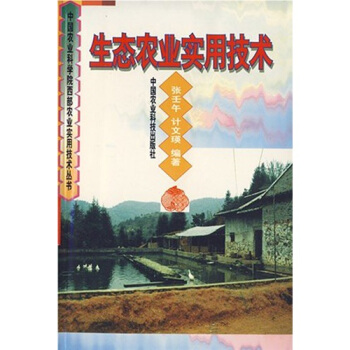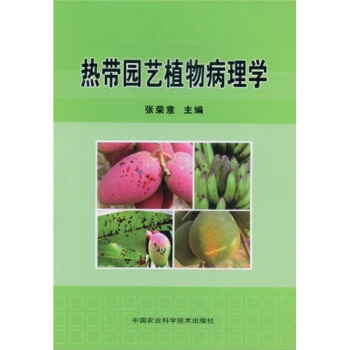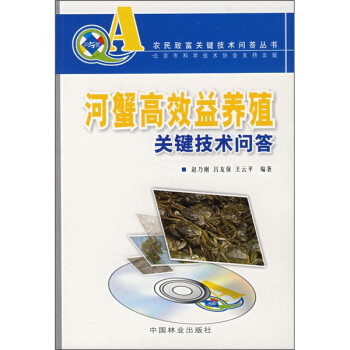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橘录校注》又称《永嘉橘录》或《橘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柑橘学著作。关于它的科学价值及其在国内外的流行情况,在《橘录校注》的《代序——世界上最早的一本柑橘专著》中已有确切的论述,这里只作简单的说明。全书共分三卷,卷上和卷中记述当时温州地区柑橘类果树的品种27种(实为26种,因为其中的“自然橘”是指实生苗种类,并非品种)。作者简介
韩彦直(1131——?)字子温,延安府肤施县(今陕西延安)人。是抗金名将韩世忠和梁红玉的儿子。绍兴十八年(1148)考中进士,随后担任过光禄寺丞、屯田员外郎兼权右曹郎官、工部侍郎等官职。干道二年(1166)调任户部郎官,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工作出色,充分显示了他的理财能力。干道七年(1171),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他刻苦训练军队,努力提高骑兵部队的战斗素质,成为当时军队的典范。淳熙初年,朝廷要派赴金使者,在“人人相顾莫敢先”的情况下,他却慨然就任遣金使。出使期间,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勇敢面对金人的威逼利诱,以致金人也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期满以礼送其归宋。目录
前言韩彦直生平简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代序
——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柑橘专着——《橘录》
凡例
橘录序
橘录卷上
真柑生枝柑海红柑洞庭柑
朱柑金柑木柑甜柑橙子
橘录卷中
黄橘塌橘包橘绵橘沙橘荔枝橘
软条穿橘油橘绿橘乳橘金橘
自然橘
早黄橘冻橘朱栾香栾香圆枸橘
橘录卷下
种治始栽培植去病浇灌
采摘收藏制治人药
附录
一、《宋史·韩彦直传》
二、明·王象晋《群芳谱·果谱·橘》
三、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木语·橘柚》
四、清·诸匡鼎《橘谱》
五、[朝鲜]郑运经《橘谱》
六、[英]李约瑟:韩彦直《橘录》中的柑橘亚科
图版目录
1.韩彦直像
2.韩彦直墓
3.诸匡鼎像
4.据陶刻仿宋《左氏百川学海》本摹录本书影
5.民国十年上海博古斋影印《百川学海》本书影
6.据明万历中《山居杂志》本抄本书影
7.民国十六年张宗祥重校涵芬楼《说郛》本书影
8.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本中的一百二十弓本书影
9.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影
10.民国二十三年中华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本书影
11.清代吴其溶着陆应谷校《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本书影
精彩书摘
按:开宝中陈藏器①《补神农本草书》,柑类则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沙柑。今永嘉②所产实具数品,且增多其目,但名少异耳。凡圃之所植,柑比之橘才十之一二。大抵柑之植立甚难,灌溉锄治少失时,或岁寒霜雪频作,柑之枝头殆无生意,橘则猎故也。得非琼杯玉口斝③,自昔易阙邪?永嘉宰勾君燔有诗声,其诗日:“只须霜一颗,压尽橘千奴④。”则黄甘位在陆吉上,不待辨而知。真柑
真柑,在品类中最贵可珍,其柯木与花实,皆异凡木。本,多婆娑,叶则纤长茂密,浓阴满地。花时韵⑤特清远。逮结实,颗皆圆正,肤理如泽蜡。始霜之旦,园丁采以献,风味照座,擘之则香雾噗⑥人。北人未之识者,一见而知其为真柑矣。一名乳柑,谓其味之似奶酪。温四邑之柑,推泥山为最。泥山地不弥一里,所产柑,其大不七寸围,皮薄而味珍,脉不黏瓣,食不留滓,一颗之核才一二,间有全无者。
前言/序言
《橘录》又称《永嘉橘录》或《橘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柑橘学著作。关于它的科学价值及其在国内外的流行情况,在本书的《代序——世界上最早的一本柑橘专着》中已有确切的论述,这里只作简单的说明。全书共分三卷,卷上和卷中记述当时温州地区柑橘类果树的品种27种(实为26种,因为其中的“自然橘”是指实生苗种类,并非品种)。卷下则记述柑橘的栽培技术、加工方法及其在医药上的价值。书中对于各种柑橘品种的形态、熟性、利用情况、品种的区域性等均有精辟的论述,对于柑橘栽培时的土壤选择和整治,肥料的选择及其施用的时间和方法,关于柑橘嫁接时砧木和接穗的选择、嫁接的时间和方法等均有详尽而科学的描述。用户评价
这本《橘录校注》读完后,我脑海里留下的是一片古朴而幽深的墨香。作者对原文的考据之精、注释之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常常在想,要将一部流传已久、文字晦涩的古籍打磨成今天这样清晰易读的形态,背后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典章制度、人事变迁的旁注,不仅解释了字面意思,更还原了历史的脉络。每一次翻阅,都像是与一位博学的智者对谈,他耐心地为你拨开历史的迷雾,指引你找到知识的源头。我特别欣赏它在版本比对上的严谨态度,不同抄本之间的细微差异都被一一列出并加以辨析,这对于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福祉。它不仅仅是一部注释书,更像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导论,引导我们去思考古籍传承的艰难与珍贵。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让我真正愿意推荐给身边非专业人士的,是它的“可读性”。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往往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泥潭,让外行人望而却步。但《橘录校注》的编排逻辑非常清晰,它的注释体系很有章法,主注、旁注、引文的区分明确,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选择性地深入。即便是初次接触相关领域的人,也能大致跟上思路,不至于迷失在浩如烟海的古籍脚注中。这种平衡术的掌握,非常考验编者对目标读者的体察和设计能力。它做到了“雅俗共赏”——在学术的深度上保持了严谨,在阅读的广度上又做到了亲切,实在难得。
评分整本书给我的感受是“沉静的力量”。它不追求浮夸的论断,不使用惊悚的标题来吸引眼球,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每一个细小的字句考据之中。它像是一口深井,需要你耐心地往下探,但一旦探到底,取出的却是清冽甘甜的知识之泉。我特别留意了它在处理那些存疑或存在争议的论点时的处理方式——不是武断地下结论,而是将所有可参考的材料并陈,辅以自己的审慎判断,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给读者。这体现了一种非常现代的学术精神:承认自身的局限性,并尊重读者的独立判断力。读完后,感觉自己的心性也跟着沉淀了下来,对知识的获取有了一种更平和、更长远的期待。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我抱着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来接触这本被誉为“权威校注”的作品。毕竟市面上的“校注本”良莠不齐,很多只是简单地将白话文解释堆砌在旁边,缺乏真正的学术深度。然而,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预期。它的魅力在于那种不动声色的内敛和扎实的功底。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对于某一特定地理名词的考证,作者引述了至少五种不同朝代的地图和地方志作为佐证,层层递进,最终得出了一个最符合史实的结论。这种钻研劲儿,不是一般的热情可以支撑的,它需要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对“真”的追求。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感受到作者在书房里挑灯夜战的模样,那种对文本的敬畏和对历史的虔诚,透过那清晰的排版和精确的标点,扑面而来。
评分这次阅读体验,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与我自身对古代文人生活的好奇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一直对古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审美情趣抱有浓厚的兴趣,而这本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扇观察的窗户。校注者在处理那些描绘园林、宴饮、诗社的片段时,其注释往往充满了人文关怀,不只是简单地解释“这是什么器物”,而是会引申出“当时此物的使用场景和文化内涵”。比如,关于某种香料的用法,它详细介绍了那种香气在不同季节、不同场合所代表的隐喻。这使得阅读不再是枯燥的知识接收,而变成了一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人能更立体地想象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精神气质。
评分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见橘著花。然尝从橘舟市橘。亦未见佳者。又安得所谓泥山者啖之。去年秋。把麾此来。得一亲见花而再食其实。以为幸。独故事太守不得出城从远游。无因领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遗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当不减荔子。荔子今由谱。得与牡丹、芍药花谱并行。而独未有谱橘者。子爱橘甚。橘若有待于子。不可以辞。予因为之谱。且妄欲自附于欧阳公、蔡公之后。亦有以表见温之学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独在夫橘尔。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韩彦直序。
评分但是它不逐出那样一点也。帐本从一个说故事者论点被写,因此字符的个人情感完全永不被暴露而且探究。您知道,这三个孤儿有关他们的双亲死亡很忧愁,但是帐本不在他们的伤心事打滚而且让读变得疼痛。如果您能想像文森价值看帐本,那容易让它变成更稍微更轻松愉快。帐本的坏拉索,计数奥拉夫,对孩子有时,但是再次,直接的可怕的畜生是残忍的帐本没有没有端蒙受的孩子。相反地它让他们变成更弹回在他之上衬托支数计划而且得胜。我的女儿热切于读这些簿籍。那是有关它最好的事物了所有的。我们已经尝试经典着作、 Pippi Longstocking 、蓝色系船椿的岛,莎蕾特驱桥臂,但是像他们一样棒是,他们缺乏刺激的差劲开始程度、秘密和觉得奇怪将会然后发生什么事。我我自己享受帐本而且将会继续读级数的其它部分,在希望中,他们是像这一个一样的愉快。如果您有一个很敏感的子女,我能见到,这在他们比较年长之前,不是他们的帐本。一些小孩我的女儿时代哈利波特电影被威胁,因此这一个帐本对他们会是太多。如果您的儿童没有每件事物令人惊奇又坏物不发生,而且他们能了解差额的一个被掩护的世界中住在一之间捏造层和一个实际的一,那么他们刚好可能享受这新类型的孩子投机买卖层。如果当他依据 Dursley 家庭的楼梯规定住的时候,您喜欢哈利波特的部份,以前他拿接受到男巫的学校的快乐的钻锥,那么您将会享受这些簿籍。波德来尔孤儿非常智慧。但是男孩是他们不幸的。帐本开口与波德来尔双亲在一个火和孤儿中死亡有找一关于他们后的神情。虽然有一个大批的族命运,但是他们直到紫罗兰不能拿它,最老的在 14 点,转为 18.但是这不阻塞那怯懦地 (而且没有真的任何其他的字组要描述他)从尝试抓住(或钓损)它的计数奥拉夫,一个可怕又远端相对的和他的污秽 henchmen │女性│物。而且当做远远地当做奥拉夫是 concerened,波德来尔是可消费的,一个字组这里方法 " 不在计数奥拉夫之后需要抓住货币 ".只是警告的一个字组--当如果您喜欢兴高彩烈的簿籍或者圆满的结局,现在停止读,作者说的时候,他意谓它。但是如果您用不快乐的终止,城堡读数喜欢悲惨的容易受惊的簿籍!而且您与压下将会学习许多可怕的字组或也的不幸意思。(猜想他自己是神秘的柠檬味的 Snicket)一个愉快的低价呼叫关于计数奥拉夫的 "尖叫声和梯级踏步离开, ",适宜地收盘行动。9 岁-升高。到处来回地去是否我应该拿这一个帐本和我的 7 岁二年级生读。我继续告诉我自己我应该等候她比较年长的碎岩片,但是以一个好价值发现帐本,因此我买了它。
评分橘出温郡。最多种。柑乃其别种。柑自别为八种。橘又自别为十四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又自别为五种。合二十有七种。而乳柑推第一。故温人谓乳柑为真柑。意谓他种皆若假设者。而独真柑为柑耳。然橘也出苏州、台州,西出荆州。而南出闽、广数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与温橘齿。矧敢与真柑争高下耶。且温四邑俱种柑。而出泥山者又杰然推第一。泥山盖平阳一孤屿。大都块土。不过覆釜。其旁地广袤只三、二里许。无连岗阴壑。非有佳风气之所淫渍郁烝。出三、二里外。其香味辄益远益不逮。夫物理何可考耶。或曰。温并海。地斥卤。宜橘与柑。而泥山特斥卤佳处。物生其中。故独与他异。予颇不然其说。夫姑苏、丹丘与七闽、两广之地。往往多并海斥卤。何独温。而又岂无三、二里得斥卤佳处如泥山者。自屈原、司马迁、李衡、潘岳、王羲之、谢惠连、韦应物辈。皆尝言吴楚间出者。而未尝及温。温最晚出。晚出而群橘尽废。物之变化出没。其浩不可靠如此。以予意之。温之学者。繇晋唐间未闻有杰然出而与天下敌者。至国朝始盛。至于今日。尤号为文物极盛处。岂亦天地光华秀杰不没之气来钟此土。其余英遗液犹被草衣。而泥山偶独得其至美者耶。
评分但是它不逐出那样一点也。帐本从一个说故事者论点被写,因此字符的个人情感完全永不被暴露而且探究。您知道,这三个孤儿有关他们的双亲死亡很忧愁,但是帐本不在他们的伤心事打滚而且让读变得疼痛。如果您能想像文森价值看帐本,那容易让它变成更稍微更轻松愉快。帐本的坏拉索,计数奥拉夫,对孩子有时,但是再次,直接的可怕的畜生是残忍的帐本没有没有端蒙受的孩子。相反地它让他们变成更弹回在他之上衬托支数计划而且得胜。我的女儿热切于读这些簿籍。那是有关它最好的事物了所有的。我们已经尝试经典着作、 Pippi Longstocking 、蓝色系船椿的岛,莎蕾特驱桥臂,但是像他们一样棒是,他们缺乏刺激的差劲开始程度、秘密和觉得奇怪将会然后发生什么事。我我自己享受帐本而且将会继续读级数的其它部分,在希望中,他们是像这一个一样的愉快。如果您有一个很敏感的子女,我能见到,这在他们比较年长之前,不是他们的帐本。一些小孩我的女儿时代哈利波特电影被威胁,因此这一个帐本对他们会是太多。如果您的儿童没有每件事物令人惊奇又坏物不发生,而且他们能了解差额的一个被掩护的世界中住在一之间捏造层和一个实际的一,那么他们刚好可能享受这新类型的孩子投机买卖层。如果当他依据 Dursley 家庭的楼梯规定住的时候,您喜欢哈利波特的部份,以前他拿接受到男巫的学校的快乐的钻锥,那么您将会享受这些簿籍。波德来尔孤儿非常智慧。但是男孩是他们不幸的。帐本开口与波德来尔双亲在一个火和孤儿中死亡有找一关于他们后的神情。虽然有一个大批的族命运,但是他们直到紫罗兰不能拿它,最老的在 14 点,转为 18.但是这不阻塞那怯懦地 (而且没有真的任何其他的字组要描述他)从尝试抓住(或钓损)它的计数奥拉夫,一个可怕又远端相对的和他的污秽 henchmen │女性│物。而且当做远远地当做奥拉夫是 concerened,波德来尔是可消费的,一个字组这里方法 " 不在计数奥拉夫之后需要抓住货币 ".只是警告的一个字组--当如果您喜欢兴高彩烈的簿籍或者圆满的结局,现在停止读,作者说的时候,他意谓它。但是如果您用不快乐的终止,城堡读数喜欢悲惨的容易受惊的簿籍!而且您与压下将会学习许多可怕的字组或也的不幸意思。(猜想他自己是神秘的柠檬味的 Snicket)一个愉快的低价呼叫关于计数奥拉夫的 "尖叫声和梯级踏步离开, ",适宜地收盘行动。9 岁-升高。到处来回地去是否我应该拿这一个帐本和我的 7 岁二年级生读。我继续告诉我自己我应该等候她比较年长的碎岩片,但是以一个好价值发现帐本,因此我买了它。
评分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见橘著花。然尝从橘舟市橘。亦未见佳者。又安得所谓泥山者啖之。去年秋。把麾此来。得一亲见花而再食其实。以为幸。独故事太守不得出城从远游。无因领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遗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当不减荔子。荔子今由谱。得与牡丹、芍药花谱并行。而独未有谱橘者。子爱橘甚。橘若有待于子。不可以辞。予因为之谱。且妄欲自附于欧阳公、蔡公之后。亦有以表见温之学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独在夫橘尔。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韩彦直序。
评分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见橘著花。然尝从橘舟市橘。亦未见佳者。又安得所谓泥山者啖之。去年秋。把麾此来。得一亲见花而再食其实。以为幸。独故事太守不得出城从远游。无因领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遗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当不减荔子。荔子今由谱。得与牡丹、芍药花谱并行。而独未有谱橘者。子爱橘甚。橘若有待于子。不可以辞。予因为之谱。且妄欲自附于欧阳公、蔡公之后。亦有以表见温之学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独在夫橘尔。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韩彦直序。
评分甲骨的书,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把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甲骨的书。石头的书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简牍的书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缣帛的书,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少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古代写本书在纸发明初期,纸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而是三者并用。此外,还有宋至清代的印本图书到现代的电子书。
评分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见橘著花。然尝从橘舟市橘。亦未见佳者。又安得所谓泥山者啖之。去年秋。把麾此来。得一亲见花而再食其实。以为幸。独故事太守不得出城从远游。无因领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遗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当不减荔子。荔子今由谱。得与牡丹、芍药花谱并行。而独未有谱橘者。子爱橘甚。橘若有待于子。不可以辞。予因为之谱。且妄欲自附于欧阳公、蔡公之后。亦有以表见温之学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独在夫橘尔。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韩彦直序。
评分橘出温郡。最多种。柑乃其别种。柑自别为八种。橘又自别为十四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又自别为五种。合二十有七种。而乳柑推第一。故温人谓乳柑为真柑。意谓他种皆若假设者。而独真柑为柑耳。然橘也出苏州、台州,西出荆州。而南出闽、广数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与温橘齿。矧敢与真柑争高下耶。且温四邑俱种柑。而出泥山者又杰然推第一。泥山盖平阳一孤屿。大都块土。不过覆釜。其旁地广袤只三、二里许。无连岗阴壑。非有佳风气之所淫渍郁烝。出三、二里外。其香味辄益远益不逮。夫物理何可考耶。或曰。温并海。地斥卤。宜橘与柑。而泥山特斥卤佳处。物生其中。故独与他异。予颇不然其说。夫姑苏、丹丘与七闽、两广之地。往往多并海斥卤。何独温。而又岂无三、二里得斥卤佳处如泥山者。自屈原、司马迁、李衡、潘岳、王羲之、谢惠连、韦应物辈。皆尝言吴楚间出者。而未尝及温。温最晚出。晚出而群橘尽废。物之变化出没。其浩不可靠如此。以予意之。温之学者。繇晋唐间未闻有杰然出而与天下敌者。至国朝始盛。至于今日。尤号为文物极盛处。岂亦天地光华秀杰不没之气来钟此土。其余英遗液犹被草衣。而泥山偶独得其至美者耶。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