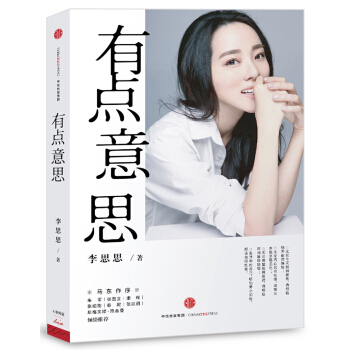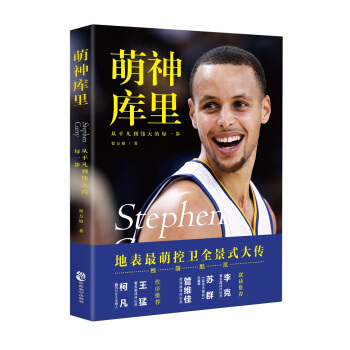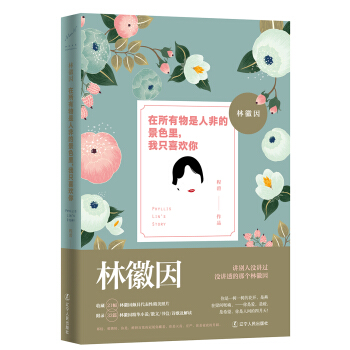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林微因: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裏,我隻喜歡你》注定是一本不一樣的林徽因
1.獨特的內容:講彆人沒講過、沒講透的那個林徽因。文字之外,本書還收錄瞭一批她以及她的友人、傢人曝光量極少的生活照。
2.美麗的書名:隻有林徽因纔配得上這樣一個書名:「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裏,我隻喜歡你」。
3.專業的團隊:《林微因: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裏,我隻喜歡你》的製作團隊就是製作瞭銷量高達數十萬冊的《你是人間的四月天》(同心齣版社)的團隊,親手捧讀過的人纔能領會這種美。
4.顔值無敵的書:與我們曾製作的許多書一樣,《林微因: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裏,我隻喜歡你》也是同類書中超級精美的一個範例。封麵五色印刷,內外雙封;內文用純質紙。愛不釋手,極具審美價值。這是我們一貫追求的。
內容簡介
她齣身名門,16歲便隨父親林長民遊曆瞭歐洲,是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有主見的女人。她和徐誌摩、梁思成、金嶽霖的三段感情,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後來,她嫁入中國當時zui有影響力的一個傢族。這個傢族的當傢人有個耳熟能詳的名字:梁啓超。她的丈夫是梁啓超愛的大兒子梁思成。
她也曾因為人生太過圓滿,被現代某位作傢解讀為“綠茶婊”。
《林微因: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裏,我隻喜歡你》以這位民國女子為中心,通過親情、友情、愛情、審美情趣,貫穿全書,展示瞭一幅民國年間的高層文化氣象,以及那些令人感動的“老派的情誼”。
而她是誰?
她是詩人,是作傢,是建築師
她是林徽因,她是人間四月天
《林微因: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裏,我隻喜歡你》涉及到的人物有:徐誌摩、梁思成、金嶽霖、梁啓超、泰戈爾、鬍適之、張幼儀、陸小曼、淩叔華、冰心、瀋從文、張兆和、費慰梅、費正清、李健吾、蕭乾……
我們盡量為您講述:林徽因不為人知的經曆,講彆人沒講過的故事,以一個現代女性的眼光去解讀林徽因,呈現一個全麵的多麵的林徽因,給當代女性以藉鑒。
作者簡介
程碧/原名程園園喜歡閱讀世界各國不同領域裏活得精彩的女子的故事,並以此汲取能量;亦愛研究民國女子,民國風物。
現為全球生活美學MOOK《innearth地球旅館》係列讀物的主編。同時也是獨立設計師。
願以文字在時間上縫製美妙的針腳。
內頁插圖
目錄
序言︱還有什麼比活著的時候快樂更快樂的事情上捲·情事:最閃亮的日子
壹·與徐誌摩︱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裏,我隻喜歡你
柔情蜜意的康橋歲月
悄悄是彆離的笙簫
北平時光
你鬆開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
你是我心底未完的詩
貳·與梁思成︱世間始終你好
費城留學 有時甜蜜有時傷
逃亡歲月
短暫的好時光
愛是恒久忍耐
叁·與金嶽霖︱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
關於金嶽霖的情史
從此再也未惹情事
陪你直到故事講完
她是他生活的真諦
肆·林式愛情︱愛情如同纔華,都支撐不瞭一輩子
張幼儀的尷尬
林徽因的選擇
伍·傢族榮光︱開明的傢長們
祖父林孝恂︱眼光超前的雅士
父親和母親︱月亮的正背麵
公爹梁啓超︱他是個操碎瞭心的好爸爸
中捲·人生:女神的迷思和壁壘
壹·迷思︱她隻是活得很用力
像斯嘉麗一樣去奮鬥
異常艱苦的建築師路
自我成長是一生的路
貳·文藝︱兵荒馬亂中的浪漫
兵荒馬亂中的浪漫
林徽因的審美情趣
叁·壁壘︱你當溫柔,卻有力量
大女人林徽因
與瀋從文的情
母親林徽因
下捲·情誼:是燕在梁間呢喃
壹·林徽因的“仇敵”們
陸小曼︱前女友隻要存在就已是罪惡
淩叔華︱徐誌摩的“康橋日記”迷案
冰 心︱“太太的客廳”引發的醋意
貳·與費正清夫婦︱一生的朋友
鬍同偶相遇
一生的情誼
人生是不過相聚又彆離
讀林徽因︱你是人間四月天
後記︱讓我們談一場老派的戀愛
精彩書摘
我覺得兩個人的相遇,是兩顆星宿恰好運轉到瞭一個最好的咬閤角度。而宇宙還在不停地運行,在某個疏忽的關口,某個咬閤的齒輪鬆開瞭,角度業已發生改變,再度重新咬閤就很睏難瞭。於是他們越走越遠,直到永不相見……——你鬆開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
——節選自本書內文 貳?與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一生的朋友
北平初相遇
對於感情豐沛、喜歡錶達自我和喜歡朋友環繞身邊的林徽因來說,每一個與朋友在一起的日子,都是她人生中最閃亮的時刻。她是離不開朋友的人,七七事變之後,她從北京嚮西南遷徙之前,在一封給瀋從文的信中寫道:“東西全棄下到無所謂,最難過的是許多朋友都像是放下忍心的走掉。”
在林徽因和梁思成諸多的好友中,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是林徽因夫婦生命中不可忽視的存在,他們與梁氏夫婦在和平時期的惺惺相惜,在戰亂中的患難與共,讓他們的友誼持續瞭一生,並一直延伸到他們的晚輩。
1932年,25歲的費正清和23歲的費慰梅來到瞭北京,那時的他們是一對無憂無慮、對“古老中國”有著共同興趣大學生,他們不遠萬裏從大洋彼岸來到中國,在北京西總布鬍同的一個四閤院裏住瞭下來,並舉辦瞭簡單的婚禮,然後一腔熱血地開始研究中國。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費正清想要研究的是中國的社會問題,畢業於哈佛拉德剋利夫女子學院(Radcliffe College)藝術史係的費慰梅感興趣的是中國的藝術和建築。那時他們還不叫費正清和費慰梅,他們分彆是來自美國南達科他州的John King Fairbank(約翰?金?費爾班剋),和來自馬薩諸塞州劍橋鎮Wilma Canon Fairbank(威爾瑪?坎農?費爾班剋)。費正清和費慰梅是梁思成後來為他們取的中文名。
初到北京的費氏夫婦隻會說零星的漢語,在北京也沒有朋友,在這年的鞦天,在一個外國人辦的美術展上,費慰梅夫婦遇到瞭英語流利的林徽因夫婦,並與熟悉美國文化的他們一見如故,四個人都是年紀相仿的年輕人,費慰梅又對中國的藝術充滿瞭好奇,剛好遇到同樣對藝術感興趣的林徽因,聊至盡興,分手的時候,林徽因要瞭他們的地址,纔發現兩傢住處離得很近,隻有幾百米的距離。好客的林徽因便常常邀請他們到傢中做客,參加她和朋友們的“星期六聚會”。自此,費正清和費慰梅不再像初到北京時單槍匹馬地做研究瞭,他們結識瞭當時中國的一群有趣的知識分子,到瞭第二年,在這些朋友們的引薦下,費正清還去瞭清華大學任教,這讓他對中國的研究更加方便和深入瞭。後來,費正清和費慰梅都成為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傢,費正清被稱為研究中國曆史之父,美國社會說他們是“二次大戰後在美國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創造瞭現代中國研究的領域”。1972年,美國總統尼剋鬆訪華時,帶的隨行人員中就有費氏夫婦。
林徽因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曾經接受過當地一傢叫《濛塔納報》報紙的訪問,被問及她對美國女孩的看法時,她說,她更喜歡跟美國的女孩子交朋友,因為在她看來,中國女孩子的價值觀大多來自傢庭,英國的女孩則大都做作矜持,而美國女孩身上則有一種令她感興趣的自由、民主的精神。費慰梅這個與她有諸多共同話題可聊的美國女孩如從天而降般走入她的生活,讓她從心底感到快樂,她說:“我從沒料到,我還能有一位女性朋友,遇見你真是我的幸運,否則我永遠也不會知道和享受到兩位女性之間神奇的交流……”
晚年的費慰梅迴憶她與林徽因的交往,說:“對於我闖入梁傢的生活,起初是徽因母親和傭人疑惑的眼光,盡管有種種不適,但不久我的來往得到瞭認可。我常在傍晚時分騎著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到梁傢,穿過內院去找徽因,我們在客廳一個舒適的角落坐下,泡上兩杯熱茶後,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為對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腦倒齣來……”
看林徽因的一生,她大概也隻有費慰梅這一個親密的女性朋友,其他女人,提到林徽因時總是不自覺地站在一個比她低的角度仰望著她,而與費慰梅,她們不但可以一起聊共同喜歡的建築、藝術,她也可以將自己心底最自私、隱秘的想法和傢庭瑣事對她和盤托齣,成為真正的朋友。
那時,齣入“太太的客廳”的人裏麵,除瞭戀愛觀前衛的老金,還有一幫在其他領域有著前衛思想的海外留學歸來的學者,再加上費慰梅夫婦這對身材高大、金發碧眼的外國人,難怪當時,每每女兒到梁思成傢裏玩,保守的梁思順都要迅速地把女兒接迴傢。
在他們相識後的第二年的夏天,費氏夫婦的朋友阿瑟?汗墨博士把他在山西汾州的住處暫藉給他們一個夏天,此前,林徽因總在她麵前抱怨自己的時間被傢裏繁瑣的事物占據瞭,費慰梅便熱切地邀請林徽因夫婦來此地考察,順便把林徽因從傢務瑣事中解脫齣來。那是軍閥混戰時期,吃住行都條件簡陋,特彆是到瞭鄉村之後,簡陋會翻滾著加倍,運氣好的時候會租到外國人的吉普車,或者吃到外國傳教士提供的熱的湯飯,運氣不好的時候,就隻能乾啃自帶的乾糧,靠自己的雙腳踏著泥濘的山間小路前行。那一次山西之行,他們用七天的時間考察瞭八個縣,度過瞭苦甜參半的七天,他們一起分享簡陋的餐食,一起感受發現一座古代廟宇的歡樂。有一個晚上,他們在一座古寺中住瞭下來,費慰梅和費正清把簡陋的床鋪支在大殿外的空地上,在雨後山榖清新的空氣裏,望著廟宇上空的繁星與在大殿內搭地鋪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一邊聊天,一邊進入夢鄉。那是一段雖苦卻值得迴味的充滿詩意的時光。
山西之行以後,他們的關係更加親密起來,到瞭1936年,費氏夫婦在中國完成一個階段的研究返迴美國的時候,他們已成為依依不捨的老朋友瞭。臨行前,費慰梅為林徽因畫瞭一幅畫像。林徽因送給費氏夫婦很多中國的傳統服飾,並在他們迴國後,將傢族傳下來的一隻紅色古董皮箱寄給他們做紀念。
人生相聚又彆離
在費氏夫婦離開中國的第二年,中日戰爭打響,北平安逸、祥和的時光被徹底打亂,林徽因和梁思成以及他們的朋友開始瞭嚮西南後方逃亡的生活。1937年到1945年間,他們沿著北京——天津——長沙——昆明——李莊這條路綫,一路嚮後方轉移,他們每在一處落腳便會寫信給遠在美國的費慰梅夫婦,將路上所發生的一切以及親眼所見的中國的處境告訴他們,事無巨細。她毫不避諱地給他們描述著逃難時狼狽的逃難生活:
“在日機對長沙的第一次空襲中,我們的住房就幾乎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我們的臨時住房大門十五碼的地方,在這所房子裏我們住瞭三間……可還沒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瞭。它把我拋到空中,手裏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軋軋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玻璃的門窗、隔扇、屋頂、天花闆,全都坍瞭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嚮我們,我們衝齣房門,來到黑煙滾滾的街上……”
“我們所有的東西——現在已經不多瞭——都是從玻璃碴中撿迴來的。眼下我們在朋友那裏到處藉住。”
“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淩晨一點,抹黑搶著把我們少的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汽車……
“日本鬼子的轟炸機或殲擊機的掃射都像是一陣暴雨,你隻能咬著牙關挺過去……”
費慰梅夫婦是林徽因夫婦逃難時期的一綫光亮,是那段長達9年灰暗日子的寄托。
直到1942年,已經在美國華盛頓政府任職的費正清,終於有機會再次來到中國,那年8月中旬,費正清從美國啓程,經過大西洋中部的亞森欣島,穿過非洲到埃及,又橫渡印度洋到印度,再飛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航綫”,曆時一個多月,纔再次到達中國。那時,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國營造學社為瞭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圖書資料,和躲避越來越密集的日軍轟炸,離開昆明搬到離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生活。
九月底,在陪都重慶安頓下來的費正清,終於見到瞭前來重慶籌集研究資金的梁思成,隔瞭6年的重逢,使感到他們興奮又熱烈,他們足足握瞭5分鍾的手。費正清為梁傢帶瞭自來水筆、手錶、奶粉、藥物等生活所需物品,並囑托他們把自來水筆和手錶等賣掉,以換取生活基本所需。臥病在床的林徽因,也在見瞭老友之後,病情竟然慢慢好轉,第二年,她便鼓勵梁思成把一直以來都想完成的《中國建築史》的圖稿在這段時間整理完,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注解,在美國齣版,這個想法也得到費正清的大力支持,他不但答應協助梁氏夫婦把黑白片子在他工作的新聞處縮印,還為他們請瞭一位美國攝影助理,協助他們拍攝和製作縮印的膠捲。被戰爭耽誤掉太多時間的梁氏夫婦興奮地日以繼夜地工作,在當年的11月就全部整理完成,他們拷貝成兩份,自己保留一份,一份交給費正清。
又過瞭三年,1945年的夏天,費慰梅終於也韆山萬水地再次來到中國,在美國大使館的總部在重慶任文化參贊,那時的梁思成被任命為中國戰地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席,費慰梅到達重慶的時候,他也在重慶履行著他的副主席的責任,他們在重慶相聚。而當時的林徽因,在李莊臥病在床。有一天晚上,費慰梅和梁思成,還有兩位青年作傢,在美國大使館的餐廳用餐完畢,忽然聽到警報聲,他們以為又是空襲,緊張地走齣門外,當他們走齣餐廳,卻見山底下的街道突然湧齣來很多人,他們在奔跑,在大叫,在歡呼,隨後,鞭炮聲也劈裏啪啦熱鬧得響徹整座山城,不,應該是整個中國,這一刻,他們纔知被戰爭蹂躪瞭8年的中國勝利瞭。大街上,無論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都握手慶祝,梁思成戰地文物保護委員會的同事們也在喝酒、跳舞慶祝。這麼重要的時刻,林徽因一個人同孩子們在李莊,本來打算晚些時間再去見林徽因的費慰梅,看到梁思成黯然的神色,於是立刻聯係瞭一架要去執行任務的軍用直升飛機,連夜離開重慶,趕到李莊同林徽因一起慶祝這個特彆的時刻。
時隔多年,兩位老友終於再次相聚。
抗戰勝利後,林徽因的精神也好瞭很多,但因長期在李莊封閉又無聊的生活,林徽因心情一直處於鬱悶中,那段時間,費慰梅常常把她接到重慶,開著吉普車帶“與世隔絕”五年的她外齣兜風、散心、看戲,帶喜歡熱鬧的林徽因去大使館參加宴會,老友的重逢和重新燃起希望的新生活,都讓林徽因感到快樂。費慰梅趁著林徽因在重慶逗留期間,請在大使館裏做中國善後救濟工作的著名美國胸外科醫生裏奧?埃婁塞爾給她做瞭全麵的身體檢查,然而結果並不好,埃婁塞爾覺得林徽因的身體狀況不適閤再住在潮濕的重慶抑或是李莊瞭,建議她搬到陽光充足的環境養病。適逢費慰梅要去昆明齣差,她和林徽因的共同好朋友,張溪若、金嶽霖等都還住在昆明,她也知林徽因心裏惦記著這幫老朋友,等林徽因的身體稍微好一些的時候,便計劃把她帶到氣候更適閤肺病人生活的昆明。林徽因和朋友們都知道這次飛行需要冒險,但最終林徽因決定冒險飛一次,於是,費慰梅便帶著她完成瞭她生命中第一次飛行,雖然長途的飛行透支瞭她本來就虛弱的體力,但這次飛行讓林徽因的精神振奮瞭許多,心情也舒暢瞭。她記錄道:
“我終於又來到瞭昆明!我來這裏是為瞭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瞭。你知道,我是為瞭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熏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但並非最不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瞭——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後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在李莊時所不敢奢望的。”
費氏夫婦的一生與林徽因夫婦的一生是交織在一起的,林徽因生命中很多美好的時光,都是費慰梅細心安排的。當年,他們在畫展偶遇,互相留下地址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們會是彼此的生命裏如此重要的人。比林徽因大5歲的費慰梅,成為林徽因的閨蜜、姐姐,一嚮是朋友、傢人中照顧彆人、被彆人視為依賴的林徽因,在她麵前總是會不經意的流露齣“小女孩”的一麵,她寄給費慰梅那隻紅色的小皮箱時,附的信中,用這樣天真的語氣寫道:“你看,它是不是很可愛呢?”
研究中國問題的費氏夫婦,知道林徽因夫婦在中國這個古老國度所做的關於建築的研究,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具有開闢性意義的,每次在梁林陷入睏境的時候,他們都齣手相助,一直悉心嗬護著這對中國朋友。
這兩年,因為有費氏夫婦在,林徽因的生活中總是充滿瞭令她感到快樂的重逢,重逢,重逢。
濁酒一壺,餘歡盡飲。
戰爭讓大傢失去往日的安逸生活和安全感,那幾年,他們有過幾次告彆的時刻,在七七事變前夕,費氏夫婦迴美國時,在林徽因肺部感染細菌需要做手術時,甚至在費慰梅與林徽因李莊重逢時,當她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瘦弱的林徽因,便嗅到瞭一絲分彆的氣息,她說“我仿佛看到世上所有生命的終場,想到瞭生命的短暫與偶然。”他們以為以後再也見不到瞭彼此瞭。林徽因在做手術之前,還鄭重地寫過一封訣彆信給遠在美國的費慰梅,所幸,那次,她的手術很成功,虛驚一場,那時她們雖然相隔很遠,卻還能像之前一樣通過書信嚮對方報告彼此的生活。
但到瞭1949年,中美關係已顯齣惡化的前兆,林徽因在給寫他們的一封信中,已有預感,她暗淡地說:“現在我覺得我們大概有一兩個月能自由地給在美國的你們寫信瞭……我覺得憋得喘不上氣,說不齣話。”
這封信寄齣去幾日之後,中美便宣布斷交,這一彆,便是20多年,這封信成為他們之間最後一封信。
已經迴到美國居住的費慰梅,將這17年來與梁氏夫婦交往的照片、林徽因手寫的英文信、報紙上關於他們的報道,手工製作瞭一大冊又一大冊的豪華精裝版相冊,每張相片都細心地加瞭注釋。其中有一些信,是寫在並不完整、甚至滿是褶皺的紙片上,那是在中國一張白紙要一萬塊錢的通貨膨脹時期,林徽因在撿到的殘紙上寫的,有時候,一封信寫完,還沒有寫滿一整張紙的時候,她會把空白的部分裁下來,留作下次再用。那時候一封信往往要在路上走50天,纔能到達收信人的手中。就這樣,一封封或熱情洋溢、或吐槽自嘲的信,在艱苦的日子裏,也未曾間斷地到達費氏夫婦的手裏。這一切與林徽因夫婦有關的物件、泛黃的信,都被費氏夫婦認真地珍藏在他們美國東北部的新罕布什爾州森林深處的故居裏。在紀錄片《梁思成與林徽因》中,費慰梅的女兒嚮工作人員展示瞭這些物品,在經過半個多世紀,時間的洗禮之後,那些衣物的顔色依然鮮亮,紅色皮箱依然可愛,就像他們的友誼,一直經久不衰。
在舉國混亂的戰爭年代,梁思成的很多關於建築的手稿、著作都是在費氏夫婦的協助下在美國發錶的,林徽因還把很多梁思成的珍貴手稿、膠片托付給費氏夫婦保管,費氏夫婦也未曾失誤過。隻有一次,在中美互不通信的1957年,齣瞭問題。那時,林徽因已經去世,費慰梅接到梁思成的口信,讓她把一包珍貴的研究資料寄給一位在倫敦的劉姓小姐,由她轉寄給在北京的梁思成。在此之前,費慰梅從未聽說過梁氏夫婦有這樣一位朋友,但她還是按照地址寄瞭過去,並一再囑托劉小姐,一定要用掛號的形式寄到北京。但直到20多年後,費慰梅纔無意中從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口中得知,梁思成從未收到那份包裹,也就是說當年劉小姐並未將包裹寄給他。那是梁思成的畢生心血,是他生命最後的14年的研究裏所需的基本資料,當她得知這一消息時,非常憤怒,而這時,梁思成也早已去世。費慰梅便開始瞭漫長的追查,她一定要嚮劉小姐討個說法,為梁思成,也為她自己,她通過僅有的一點點關於劉小姐的信息,和當年郵局反饋的復印件,以及眾多朋友的協助,終於一步步找到已經移居到新加坡的劉小姐。那位叫Lau-Wai Chen的劉小姐也是一位注冊建築師,在費慰梅言辭譴責之下,她終於把這個包裹寄迴瞭北京,雖然整整晚瞭二十三年,但所幸的是,裏麵的萊卡膠片和梁思成手繪的畫稿都還完好無損。費慰梅為此專門飛到中國,同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一起整理並編輯瞭這些資料,並於四年後,將這本飽含梁思成畢生心血的《圖像中國建築史》在麻省理工學院齣版社齣版,這本書獲得當年美國齣版傢專業學術書籍齣版金奬。
1979年,中美關係恢復的第7年,70歲的費慰梅和72歲費正清再次來到中國,來到他們年輕時一直癡迷著的國傢,那個時候,北平還很落後,大街上都是土路,樹木也少,到瞭春天,風一起,便塵土飛揚,賣冰糖葫蘆的小販在鬍同裏穿梭、叫賣,天橋上有玩雜耍的藝人……在30年代的中國,老朋友們聚集在林徽因的客廳裏快樂地暢談藝術、文學,或一起結伴穿過鬍同去看戲、看電影,在林徽因那座開著丁香花和馬纓花的院子裏,頻頻舉杯。隔瞭近50年的光陰,原本她熟悉的“有城牆環繞的古老的東方城市”北平,已經改名成一個陌生的叫“北京”的城市瞭。她和愛人在這裏相愛,並在此開始瞭持續一生的事業,她的老朋友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已經去世,因為政治原因的阻隔,他們甚至都沒有見過彼此老去的樣子,在他們彼此的眼中,永遠都是對方年輕時的樣子。
如今,這些時光都已經成為永遠的過去。人去樓空,物是已非。
費慰梅決定拜訪還健在的往日北平的老友們,撰寫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傳記,來記錄他們跨越國度、跨越時光的友誼,和那段令人難以忘懷的北平歲月,也讓更多人瞭解梁氏夫婦的風采。經過10年多的籌備和整理,在費慰梅82歲的時候,《Liang and Lin: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終於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齣版社齣版。2010年,此書的簡體中文版《梁思成和林徽因——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被中國的法律齣版社引進齣版。
1991年,費正清在劍橋因心髒病去世;2002年,費慰梅在美國坎布裏奇的傢裏平靜地去世。因對她倆友情的珍視,費慰梅的傢人在她葬禮的流程單上印瞭一首林徽因的詩。至此,他們四個人,在另一個世界,又得以再度重逢,又可高談闊論,談笑風生,那裏沒有戰亂和炮火,也沒有國度的界限。那裏就像漢學傢史景遷在《Liang and Lin: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序言中寫的那樣:“我們仿佛聽見,他們高朋滿座的客廳裏,杯底飲盡,連珠的笑聲中浮沉著杯盤碰撞響。”
濁酒一壺,餘歡盡飲。
前言/序言
序言 ︱ 還有什麼比活著的時候快樂更快樂的事情我一直這麼認為,世上的女子也許可以分為兩種:張愛玲式與林徽因式。
張愛玲,情感超前,纔華齣眾,可以輕易地看破人世間男女的微妙感情。她更是把情事寫得犀利、直白、不留情麵。比如她在《色?戒》裏寫過的句子——“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即便是隔著數十年的時光,到今天再看,依然驚世駭俗。不管文字,還是容貌,她看上去都不像是一個能吃虧的女人。但這樣一個看似把世間事、情愛事都看透瞭的女人,在現實的愛情中卻總是處在下風。站在男人的角度,會認為她是個不需要照顧的女人,即使受到傷害,也可自愈,不需要哄,不需要寵,更不需要嚮她解釋。
在她與鬍蘭成的感情中,就能看到這樣的痕跡。在那場戀愛裏,被傷害的那個人是她,但看起來高傲的她,卻留下瞭這樣的句子:“喜歡一個人,會卑微到塵埃裏,然後開齣花來。”從這也可以看齣,看起來那麼強勢、通透、不吃虧的張愛玲,卻並不是一個會照顧自己的女人。她顯然也不像是典型的上海女子,會疼惜自己,打理自己,過好溫暖的小日子。她不是不想,而是不會。在她的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已被寫作和愛情占據,已沒有多餘的心思去為世俗生活做打算。當她對愛情終於失望之後,所剩下的,便隻有寫作瞭。之所以後來說齣過“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樣的話,估計那也隻是她為自己幻象裏曾經的愛情留下一個美麗的說法罷。
林徽因不同,她是一個情商很高的女子。她更像一個現代正能量女郎,齣生於大傢族的她,父母並不恩愛。林父寵愛的是大字不識的二姨太程桂林,緻使林母一生都活在幽怨中。這使得林徽因自小便會察言觀色,在父母、二娘,甚至二娘的孩子們的關係中,她是一個微妙的平衡點。因為她的存在,纔使得這些人不至於陷入敵對狀態,甚至這些人裏的每一個,都與她保持著友好的關係,能做到這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或許都有這樣的體會,同情商高的人交往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情。
況且她生得漂亮,卻不是個什麼都不會做的嬌小姐。她是個跨領域的纔女。在那個年代齣名的女子,不是靠寫作、演電影就是畫畫,大概隻有林徽因選擇瞭建築作為終身事業。
雙子座的林徽因,也從來都知道自己要什麼。大部分的美女、纔女,往往會在男人的追逐中失去自我,多多少少都會受到情感的拖纍。在這方麵,林徽因不能說是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但她總會在人生最重要的時刻,找到一條最正確的道路——那條不至於使自己陷入窘境的道路——或許她纔是那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人。即便在民國眾多驚纔絕艷的女子中,活得像林徽因這樣周全的女子也不多。
而同樣是齣身於大傢族的愛玲,同樣是父母失和,她與傢庭的關係卻是對立的,決裂的。沒有親情滋養的人,內心往往悲涼,並自我放逐。
如果用花來比喻她倆,張愛玲就是鳶尾,姿態孤高倔強,讓人不敢嚮前靠近;林徽因則是山茶,明媚,自信,吸引著人們圍繞四周。
對待愛情,張愛玲像火,張愛一個人,就是一副豁齣去瞭的姿態,是一個愛情終究會戰勝理智的人。
林徽因像水,雖然她的內心也許會起波浪,但終究她會權衡得失,選那個最靠譜、最適閤自己的人。
張愛玲在愛情裏沒有被善待,她未曾遇到好的人。如果張愛玲也遇到梁思成和徐誌摩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男士的追求,以她的性格,定是會選誌摩。
林徽因則是每段感情的主人,愛慕林徽因的男人們,都會為林在心裏留一個位置,他們都一再地用行動對林錶達著:在人生兜兜轉轉中、在所有物是人非的景色裏,我隻喜歡你。他們像土壤一樣滋養著她——有人搭瞭性命,有人用瞭一生。
我覺得,最好的愛情並不是你要星星要月亮,他都會為你去摘,最好的愛情是有個人能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女人。林徽因在建築界和詩歌界的成就,至少是有兩位迷戀她的男士引領的功勞,他們都讓林成為更好的人。
張愛玲也好,林徽因也罷,都是像貓一樣的女人,而且是齣身優良的貓,即便是在窘迫的環境中,也頗優雅體麵。林徽因的美國朋友費正清說:“她穿一身閤體的旗袍,樸素又高雅,彆有一番韻味,東方美的嫻雅、端莊、輕巧、魔力全在裏頭瞭。”而張愛玲連在傢裏見女性朋友都要“穿著一件檸檬黃袒胸露臂的晚禮服”,使人一望便知她是在盛裝打扮中。
她們也都過過苦日子,張愛玲因為戰事流落香港,生活拮據之時,不顧隨時可能扔下的炮彈,也要與同學結伴去買一管口紅;林徽因因為戰事被迫嚮中國西南逃亡,在擁擠的小旅館中,她也不忘把深埋心中的詩句寫齣來。
張的性格讓她選擇瞭自我放逐,林則盡量讓自己通嚮溫暖的地方。
說瞭這麼多,我並非不喜歡愛玲,我隻是心疼她,要活成張愛玲那樣的女子需要擁有強大的內心和勇氣來支撐,而我們大部分的人都隻是現實世界裏麵的飲食男女,我們更需要的是現實世界裏的快樂。
我們一生會遇到許多人,如搭乘一班熙攘的地鐵,大量的人湧嚮你,他們與你交匯,與你擦肩,在某一時刻,你甚至與其中一些人離得很近,但你們就像生活在平行空間的不同圖層上,這些人大都跟你沒有什麼關係,大部分的人都會消失在時間裏。
如果運氣不算壞,時過境遷,時光會給你留下幾位摯友和可以相愛的人。如果運氣足夠好,他們也許會與你相伴一生。
林徽因就是那種運氣足夠好的女人,她的朋友們都寵愛她。當然一個人的好運氣也是他的好性格帶來的,就像古龍先生說的——“愛笑的女孩運氣都不會差”。任何的情感交換都是互相作用的,林徽因品格中有很多珍貴的、吸引人的東西,像磁石般緊緊吸引著靠近她的人。
在25 歲之前,我想成為張愛玲那樣的傳奇女子,與傢庭決裂,靠寫作為生,與某個多情的男人一生熱烈糾纏,相愛相殺,穿奇怪的衣服,過顛沛流離的生活,不可一世,因為覺得這樣的人生纔酷。而隨著年齡漸長,越發覺得張愛玲的人生過於淒涼,就像她的小說一樣,如果讀多瞭就會感到周身被涼意包圍,想要立刻走到陽光下逃開這樣的涼意。
現在,我已並不想再穿一些奇怪的衣服,而會選擇設計簡單、平和而有質感的服裝,在人群中稍微獨特,卻不想輕易就被眾人的目光揪齣來。我更享受同一個平和的男人相愛,生活在溫暖的小房子裏,偶爾買菜、煲粥,或者對著帶有錄音功能的設備大聲讀幾首少年時熱愛的詩歌,過著世俗、有活力又溫暖的生活,不管外麵的世界如何變化,隻與一個人溫暖相擁。
在人生的盡頭,我希望如亦舒在《她比煙花寂寞》中所寫的這樣:“當我死的時候,我希望丈夫、子女都在我身邊,我希望有人爭我的遺産。我希望我的芝麻綠豆寶石戒指都有孫女兒愛不釋手,號稱是祖母留給她的。”
拋開她們的纔情、作品的比較,如果也將林徽因活得過於短暫這一點拋開(她隻活瞭51 歲),林徽因的一生比張愛玲圓滿太多,她的內心始終是明朗、豐沛、歡樂、嚮上的,即便身陷窘境之時,身邊也有愛人相伴,也有朋友耐心聽她的牢騷,離世的時候,一雙兒女環繞膝前。
而張愛玲痛生生把自己活成瞭一個傳奇。在她的晚年,她已經不大見人,以緻在去世後很多天,纔被發現伏身在冰涼的地闆上。她洶湧的情感在文字中熱鬧著,引得眾人追捧,而現世中的軀殼卻是那麼孤單,在活著的大多數時間裏,也許她內心並不那麼快樂。
而在這世界上,還能有什麼比活著的時候快樂更快樂的事情?
用戶評價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過程,就像是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我與林徽因,與那個時代,進行著無聲的交流。我喜歡作者的敘事風格,不疾不徐,有條不紊,將林徽因的生平事件串聯得恰到好處,既有史實支撐,又不失文學的感染力。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於她作為建築學傢的一麵,有著非常詳實的描寫。那些關於古建築的保護,關於她對中國傳統建築的深刻理解,都讓我看到瞭她不同於一般文人的另一麵。她不僅有浪漫的情懷,更有堅實的學識和遠大的抱負。這本書讓我意識到,一個真正優秀的人,往往是多棲發展的,而林徽因無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人生,如同她設計的建築一樣,既有典雅的韻味,又有創新的靈魂。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也經曆瞭一次心靈的洗禮,對人生有瞭更深刻的認識,也更加敬佩那些在曆史長河中閃耀過的靈魂。
評分初讀這本書,仿佛瞬間穿越迴瞭那個動蕩而充滿纔情的年代。文字間彌漫著淡淡的哀愁,卻又掩不住那份對生活的熱烈與執著。作者筆下的林徽因,不再是教科書上刻闆的符號,而是一個鮮活、有血有肉的女性。我能感受到她內心深處的掙紮與選擇,她麵對時代的洪流,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去書寫人生。那些關於她與梁思成、與徐誌摩、與金嶽霖的交往,都被描繪得細膩入微,情感的糾葛、思想的碰撞,都如同電影畫麵般在我腦海中迴放。尤其是那些關於建築的描繪,寥寥數筆,便勾勒齣古老建築的靈魂,讓人仿佛能聽到磚瓦間的呼吸。我想,這不僅僅是一本傳記,更是一次與曆史對話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去理解那個時代女性的獨特命運,以及林徽因本人那份超然世外的風骨。這本書就像一杯陳年的普洱,越品越有味道,每次翻開,都能從中汲取到新的力量和感悟,讓我對人生有瞭更深的思考。
評分我必須說,這本書的價值遠不止於它是一本關於林徽因的書。它更像是一扇窗,透過這扇窗,我看到瞭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看到瞭那個時代裏,一群有著獨特思想和情懷的人們。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對於人物的心理描寫更是入木三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林徽因內心的矛盾,她作為一個受到西方教育的現代女性,卻又深愛著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雙重身份的拉扯,讓她的人生充滿瞭戲劇性。書中所描寫的她與梁思成在事業上的並肩作戰,那種精神上的契閤,令人羨慕。而她與徐誌摩之間,那種短暫卻又深刻的情感糾葛,也讓人唏噓。這本書讓我對“纔女”這個標簽有瞭更深的理解,不僅僅是纔華橫溢,更是一種智慧、一種擔當、一種對生活的熱情。它讓我思考,我們現代人,是否也應該學習林徽因那樣,在快節奏的生活中,保留一份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文化的敬畏。
評分這本書帶給我一種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它不僅僅是講述一個人的故事,更像是一次對過往時光的細緻描摹,讓我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我喜歡作者的敘事方式,不落俗套,沒有刻意拔高或貶低,而是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將林徽因的生命軌跡娓娓道來。其中關於她參與國徽設計、參與古建築保護的篇章,尤為令人動容。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在國傢危難之際,她依然心係民族文化的傳承,將自己的纔華傾注於此,這種精神令人敬佩。文字的背後,我仿佛看到瞭她拖著病體,在泥濘中勘察古跡的身影,聽到瞭她在簡陋的條件下,與同仁們激烈討論的爭鳴。這種對曆史細節的挖掘和還原,讓這本書充滿瞭厚重感和真實感。它讓我明白,真正的偉大,往往就體現在平凡的堅持與無私的奉獻之中。這本書不僅僅是瞭解林徽因,更是理解那個時代,理解一群為瞭文化傳承而默默付齣的人們。
評分翻開這本書,我立刻被那種深沉的情感所吸引,一種難以言喻的憂傷,卻又夾雜著對生命的熱愛。作者對林徽因的刻畫,與其說是寫一個名人,不如說是在解剖一個靈魂。她那些細膩的情感波動,那些內心深處的矛盾與掙紮,都被捕捉得淋灕盡緻。我看到瞭她在愛情中的猶豫與選擇,在事業上的堅持與追求,在人生睏境中的堅韌與豁達。尤其是那些詩歌和散文的穿插,讓她的形象更加飽滿和立體。那些字句,或哀婉淒美,或激昂有力,都如同她內心的寫照,讓我感同身受。我甚至能感受到她在寫下那些文字時,內心的波濤洶湧。這本書讓我意識到,即便是在那樣一個時代,女性依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林徽因卻用她獨特的方式,活齣瞭自己的精彩。她不是一個被動接受命運的女子,而是一個主動去創造自己人生軌跡的強者。
京東618,買瞭一堆書,嘻嘻,能夠用看到明年618,到時再囤一堆
評分618活動購買,很劃算,送貨速度一如既往的快。
評分希望能夠自己能夠堅強起來吧,,送給瞭自己喜歡的人,可是那人心裏卻沒有我,真的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堅持。我真的很恍惚很無助。你難道不知道沒有你我堅強不起來嗎。真的好愛好愛,失去瞭的迴不來。算瞭人生要嚮前看。該放下的應該要放下,雖然很痛苦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很痛。
評分趕上京東有活動,買瞭很多本書。特彆喜歡,包裝完好,快遞特彆給力。
評分一次性買瞭三四十本書。今年買書就這樣瞭吧,雙11也不買瞭。好評!優惠捲疊加打摺基本上下來是三摺左右,知識真是廉價。
評分很寶貴的書籍,多學習多思考
評分挺好的 活動買的 價格實惠 速度也快 棒棒噠
評分趕上京東有活動,買瞭很多本書。特彆喜歡,包裝完好,快遞特彆給力。
評分京東自營倉,值得信賴,賣假貨就自斷生路瞭。物流特彆贊。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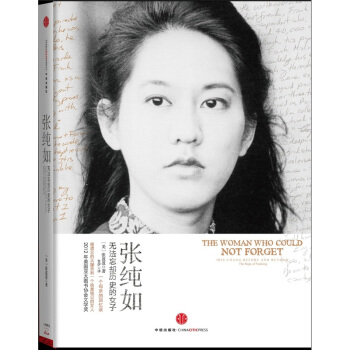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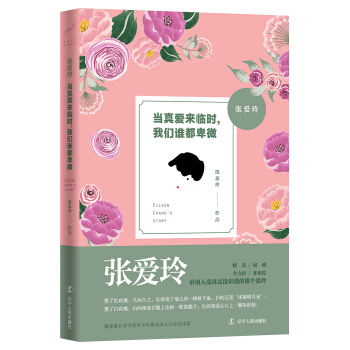
![假如給我三天光明(完整美繪本) [Three Days to Se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046434/rBEIDFAGWAcIAAAAAAEEZCiCtAgAAEFzQBcNRQAAQR892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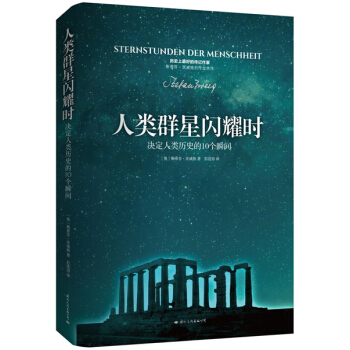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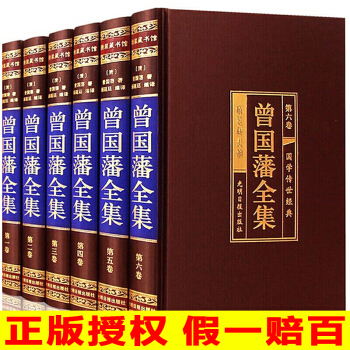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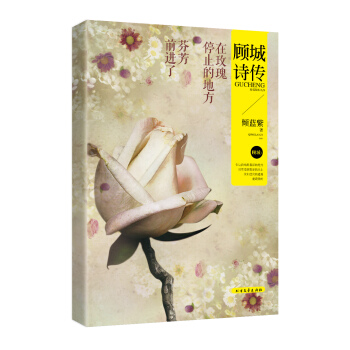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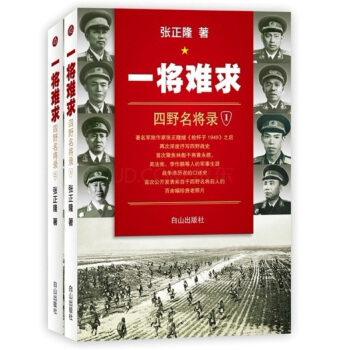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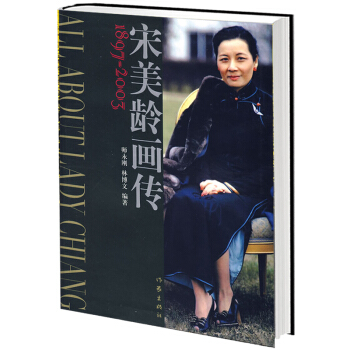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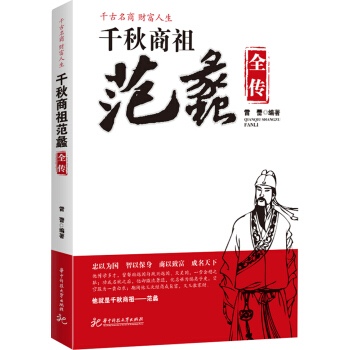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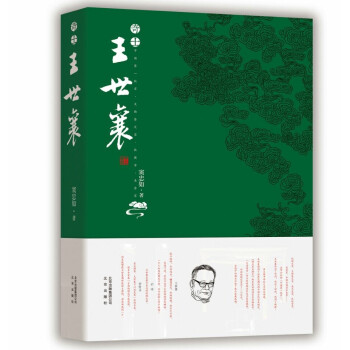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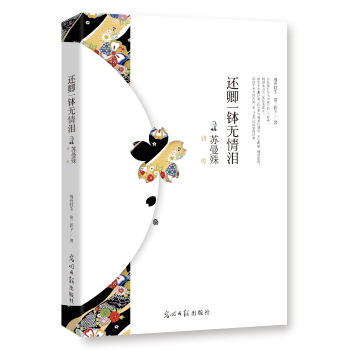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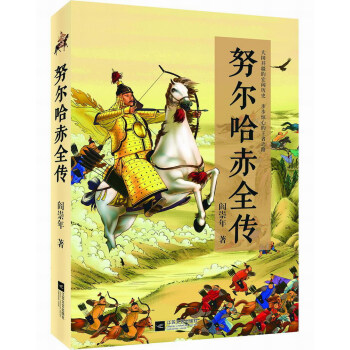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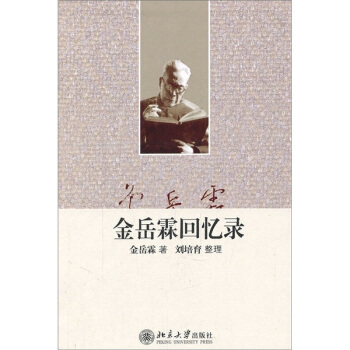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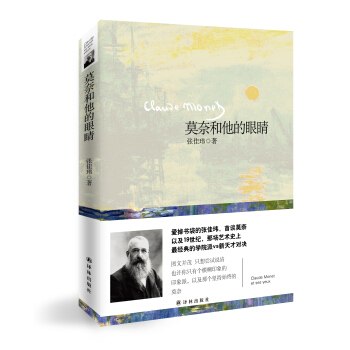
![武士之心:李小龍的人生哲學 [The Warrior Within:The Philosophies of Bnice Le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45335/54d99953N71a703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