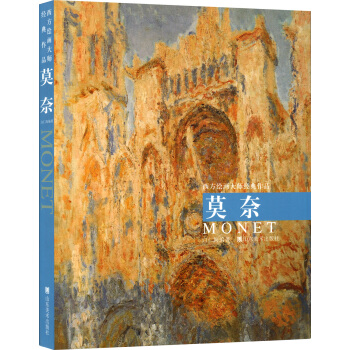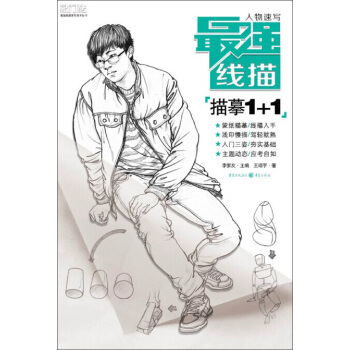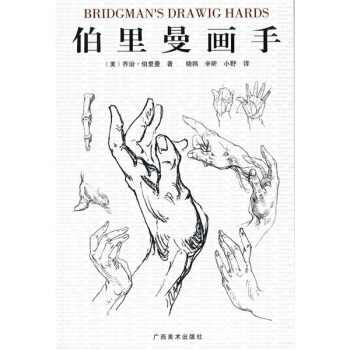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老树画画《一尺闲梦》超值礼盒套装是首度将微博红人@老树画画的画作、诗作、文章组合成为一套多功能文化产品。★24幅画作画作可装裱装框挂于居室及咖啡馆、茶馆等。物超所值。
★《老树说》文集共五万余言,系十余年老树精选文字,首度结集,一睹为快。
★布面精装主题笔记本内有老树精选画作百幅,可赏画品诗纪事绘图。
★超值赠送2016年老树画画2016年日历四开大幅单页。
收藏雅品·馈赠雅人
本书获2015腾讯·商报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
内容简介
“老树画画”用古体画与打油诗搭配调侃现代生活,借助微信与微博等新媒体传播,近年来在网络上广受欢迎。本书选取老树新精选画作24幅,以优质机宣纸单页印刷,程度还原原作典雅古朴的艺术风格,可装裱挂框,并附赠《老树说》老树十年文字首度结集、《世间破事去他个娘》老树画画主题笔记本及“老树画画”2016年年历。可以满足喜欢老树画画的都市中青年白领收藏、馈赠之需求。作者简介
老树,名刘树勇,1962年生于山东省临朐县。1983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艺术系主任。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自习绘画,问学于梁崎、王学仲、霍春阳诸师。后开始致力于视觉语言与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广泛涉及文学、绘画、电影、书法等领域。9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评文章行世。目前,主要从事影像的媒介传播研究和具体实践。2007年始,重操画业。
新浪微博@老树画画
微信公众号老树工作室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老树的画必得配上老树的诗来看。他采用古体诗的形制,大量运用反转、戏谑的手法,把俚俗与雅致杂糅在一起。那些诗明白晓畅,结尾时常出其不意,讽喻、批判和疏离也往往在轻松的句式中被消解。——《三联生活周刊》
★老树画的是一种新文人画,颠覆了传统人文画固有的一些东西。传统人文画多清雅,不介入社会,以保持画家个人的高洁情怀。还有一种,是主动干预社会的世俗绘画。而老树的画,是两者的结合,文人的笔墨写意,漫画式的讽刺干预。也就是说,他绘画中那些貌似遁世的场景,实则是入世的,是对当下社会生活温婉地干预。
——新华社
★树勇的画,把自身陪进去,的确蕴了不少潜台词。但孩童的天真嬉戏之心,又使他免于玩世不恭,这条界线,是高手雅人敷彩最后才能趋至的境界,故能使每幅图画新鲜起来,笔墨不拘,那又或可称之“护身画”了。所以说,“具冷眼者兼具热肠”是其本质。虽时代所致,个人与社会关系,聚散无常,“护生”与“护身”颇为不同,其复杂性,包括感受,也绝非“一百零八笔”(郑逸梅记:丰子恺画佛,不论大小,均作一百零八笔)能囿。树勇的作品,看似简单、浪漫,却大巧若拙,不光笔力、安排高简,虽芭蕉一林,青苔满地,却也难分古今,即便社稷时势,也风流蕴藉、策杖携琴,掩映了不少曲笔,刺贪枉、宏大,而同情人间山水,或准。
——钟鸣
★他要用笔墨确证自己。他做到了。他把那个走出“影响之焦虑”的自己称作老树。现在,整个中国都知道“老树画画”、“花乱开”,尽管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刘树勇__这不难理解,符号的名称并不重要,符号带给生活的隐喻才是重要的。老树画画给了我们关于自由的隐喻。
——汪惠仁
★老树画画,画的就是自己。一个安静下来的,随心所欲的自己;一个逗自己玩,也逗别人玩的,无为无不为的自己;一个天真浪漫的,调皮滑稽的,书卷气十足的自己;一个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极其认真地对着自己灵魂说话的自己。这恰真实地传递了老树的当下状态,从喧哗与骚乱的外面世界,回到了自己逐渐安顿下来的内心,正如杨绛先生百岁感言写到的:最后发现,这个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我觉得这是需要用很长时间而且很认真地活过的人才能悟出来的一句话。
——苗福生
★老树老师,气象万千。他就是山东野地里生出的一棵又正又妙的庄稼。树老师鼻直口方。两道剑眉,一双眼睛很有英气。印象里他总穿一件藏蓝的大背心,圆领,或各种文化衫。他讲话时夹叙夹议,夹笑夹损。教了我们太多东西。奇怪的是,我现在感觉,他几乎直接就讲了庄稼,土地……的关系。那是一种骨子里的血性,是一种粗粝的真情。是一铁锹一铁锹的翻土,一棵苗一棵苗的插秧。
——夏日山间(学生)
目录
《老树说》十年文字首度结集市井百态 旧人旧事
一个有硬度的山东汉子跃然纸上
冶原一年/1
药铺/22
王五/28
活在北京的程东和刘树勇/38
我的朋友孙京涛/49
重要的是一直在看/62
1900传奇/68
睡在画报里的民国女子/74
死亡让我渐渐平静/79
精彩书摘
王五王五是个打柴的,五十多了,没有老婆。他大概是有个什么名字的,不过不大有人叫,时间一久,村里人便把名字给忘了,只知道他行五,去过朝鲜,于是便呼他为王五。
王五是外乡人,据他说是在蚌埠一带一个什么地方。某年,淮北大水,村落尽没,看着一路饿毙的灾民,他娘带他逃荒到了山东,落户在此地。娘死了,他便参了军,因为可以吃饭。王五不会什么手艺。据他说,他曾在上海拉过黄包车,别人皆不相信是真的,而且这手艺在这山里是无用的。种地又不会,王五还嫌啰嗦,于是就打柴。
这村子居处山口,乃山里与山外的物资集散地,挺大,但并不繁华。只有一家烤鸡店,是山里一个老头儿来这里开的,姓吴,店号便称作吴家烤鸡。本地人都觉得奇怪,烤这东西谁吃?本地人是不会吃的。但生意一直还过得去,因为山外便是城市,有缫丝业、水泥制造业及果品加工业兴起,不时有些老外来考察。宾馆过去一直也没什么客人来住,尽是本地大小农民头目开会时下榻。吃食上却是越洋气越好,远道运来无非海参鱼翅龙虾鲍鱼,西洋红酒。有一阵子竟然流行吃法式蜗牛。一干人等铺张开来,穿廉价西服,初时模样儿也算斯文,急了便开始划拳行令。划着划着,就光了膀子。硬着头皮吃下去,旋即找个角落呕净,回家也说是吃过法国菜了。
真的老外一来,却说是要尝尝本地风味。宾馆领导想了一夜,忽记起进山拉山货时见过一面烤鸡的布幌子,仿佛姓吴。派人打探,果然有,而且带回两只烤鸡来。老外左右扯着吃罢,大喜过望,扎煞着两只油汪汪的肥手,说是“玩了够德”。于是宾馆主事儿的很是得意,开过几个会议,又报上级领导批准了,将这风味列为本地菜肴之冠。又想重点开发开发,将这老头儿请到城里宾馆,说,可商量着开个分店。吴老头只是不答应。问为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也不为,只是不想去,想订货是可以的。说完便回去。于是宾馆只得长期订货。于是这烤鸡店便一直开下去。
王五便是为这烤鸡店打柴。烤鸡用什么木柴,柞木的好还是野海棠木的好,王五很清楚。吴家烤鸡有些名气,王五也以此自豪,逢人便说自己是吴家烤鸡店的伙计。吴家烤鸡店名气传到四乡,别人自然也对王五另眼相看。
王五就高兴。每日晨起,着一身精简打扮,青布褂子,宽腿裤子,千层底的布鞋。将一副猪鬃编成的毛绳挽在扁担一头,出得门去,一路吹着口哨儿进山打柴。傍晚回来,村里干活儿的人也从地里回来了,便能看到王五在家门口当街上磨斧子,旁边放一碗白开水。王五头上冒着热气,磨一阵子,停下,直起腰身,在初上的月亮下用拇指去试斧刃。月牙儿一样的斧刃在手里亮得发白。嘴里口哨一直吹着,听得懂的便知道他吹的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过只是吹半截,后半截便不会了。
村里人似乎觉得,王五天天这样过着,很快活,没有人想过他也应该有老婆孩子的事。人们看到他天天撮着嘴吹着口哨,吴家烤鸡店后院的木柴垛一天一天地高起来。过路挑水的人有时会听着院子里噼噼叭叭的劈柴声,不时有木柈子蹦出墙外,打在刨食吃的母猪身上。人们都知道,王五很快活。
可王五很寂寞。邻村掏了个煤窑,这村里人家大都改了灶,烧煤了。山上柴没人打,进山的便只有王五一个人。王五走在空旷的山谷里,一路走一路吹着口哨,望着满山的草,满山的树,满山的鲜花儿,他觉得很寂寞。口哨吹着吹着似乎就有些腻了,打柴时便不再吹。于是一座空山里,太阳暖暖地照着,鲜花静默地开放,无有鸟喧的中午,就只有王五的斧子梆梆的砍伐声,和一株什么枯树轰然倒地的声音。
王五将柴打好,拢在一起,将绳索来捆了,放在山谷深处的道上,就坐谷底的河水边儿上吃干粮。
这水的上游有一座古寺,年久无人居住,颓废了,只有风吹破庙四周的风铃微妙的响动传过来。但总是没有人可以说话。于是王五就笑,揪一把野花扔到水里,看着水流把花冲走,王五就默默地笑。翻石头捉到一只老蛤蟆,用一根枯草插进蛤蟆的肛门里,然后撒开手,看那老家伙疯狂地在水滩上奔跑猛叫,王五便放声大笑。笑过之后又要嚎、骂,骂陈教导员,这陈教导员因为他偷偷将一件女人的亵衣打在背包里将他开除了队伍。骂过之后,便躺在水边的石板上午睡。他仰头看着云彩从这山头飘过那山头去,听着水在身下清楚地流响。太阳偏西了,有山风起来了,王五觉得—天的日子又过去了,便起得身来担着柴往回走。一路上都默声不语,一进村口,便又吹起了口哨。
山里来了一老一少,说是打普陀山来。那老者一副精瘦打扮,黑布长衫,着白布袜,黑布鞋。少年大约是童子模样儿,提一只竹皮夹箱跟在身后。村长见着,问是投何处去的。那老者上前打一个揖,便说自己师傅早年在这山中隐居修身,日本人来时投普陀去了。临了时托弟子来照看一下寺院。村长便诧异,说,哪有什么寺院?老者便说,就在这山中,称作不了居的。村长更不知道了,便唤个孩子去找村里的长者打问,回来说是这不了居便是山中那座破庙。村长这才将信将疑,又记起了上级说过的什么尊重宗教信仰的话。忙翻文件,总是找不到。老婆便说,可是那本有红字的东西?村长说正是,哪去了?老婆便说早打鞋底子用了。骂了老婆一句什么,出来对这老者说是欢迎欢迎,村里人总是希望那庙再兴旺起来,香火续上,也保大家平安度日。老者抬眼将村长看看,说,是吗?就走出去。村长又追上去问:那怎么住?我派人帮着修修?老者已走出极远,头也不抬。唯那童子回头看他一眼,又踢一脚尾随而去的狗。只见他师徒二人一路飘飘地进山里去了。
王五很高兴。次日进山打柴,将柴打足了,担到古寺门口立着放下,爬上墙头朝寺院里看。只见老少二人已收拾出两间耳房住下,这时正在门前廊檐下煮茶。
老者大约是知道有人在看,头也不抬地说:打柴的,进来坐坐。声音洪亮深远,王五禁不住哆嗦了一下。犹犹豫豫地进到院子里来,老者已把一块石头在一边码好。王五看着师徒二人,问,能坐?那老者便说,坐。那少年朝他笑笑,转过身去用一根竹管在两块石头夹起来的火上鼓吹。火旺了,火上一只吊钵里的水沸起来。
那老者从屋里抓一把粗茶出来放进钵里,水立刻绿了。取下钵,在三只碗里斟过。
老者呷过一口,说,好茶。
童子便微微一笑。
王五也喝过一口,烫着嘴了,连说好茶好茶,真是解渴。
老者喝罢,问王五,一直在这山里打柴?
王五说,是,二十多年了。
老者说好,好,此地甚好。
王五就说,一般,弄口吃的倒是够了。
老者又说好,好。
王五不知好在哪里。那童子只管吹火煮茶,并不看他。他觉得过路吃别人茶一碗,该谢谢才是,便说,长老如不嫌弃,我是王五,有的是气力,可帮你烧了这一院子的荒草。
老者笑笑,看着满院子枯黄的野草,说,若花儿一般,烧它做什么?留着看吧。说完接着喝茶。
于是,这古寺一如往常一样颓废,并没有修葺得红漆朱瓦,更没有香火续上。除了两间耳房略微洒扫过,门窗裱糊过外,其他数间正堂依然空空荡荡,依然有虫子不住啃它。冬夜时分,朔风吹来,一座古寺破屋和周围无数参天老松呜呜作响。只有油灯两粒,让人还知道是有人住在里面。
村长初时颇怀疑两人是犯什么科的在逃者,又怀疑是台湾潜来的特务。与民兵连长暗中卧雪盯了两夜,寺内并无木鱼敲,亦不见什么电台发报的动静。灯火灭后,只闻呼噜声山一样响。村长又着人写信去普陀问是否有人过来,回信说是。这才将信将疑,慢慢宽下心来。
师徒二人在此平静地过下去,但并不去村里化缘。山中野味不少,二位行者初来北地,不大认得,幸有王五积极推荐,说,这是苦菜,这是曲曲芽儿,做菜团子吃,最好。贱年歉收时节这都是救过命的东西。说,这是山韭菜,做馅儿吃,和家中韭菜味道两个样儿。说,这是地衣,草变的,下雨天到处是,用腥油炒吃,香成个蛋。
老者与那童子一一试过,说是都好都好,唯那地衣是天地所成,吃来非人间所有。王五得了夸奖,便专拣下雨天气进山,约了老者和那童子,三人披了蓑衣,满山上走来走去采地衣。采到地衣密集处,王五便禁不住手舞足蹈,又把口哨吹起来。那老者略微有些诧异,见他不过是心中喜悦,虽然忘形,并不散神,遂与弟子相视一笑也就罢了。于是大雨时节,山风四起,一座空山便让王五的口哨吹得热闹异常。
王五自此便有了精神,不再寂寥。每日打柴不过半日,其他时间便是到寺里去与那老者相伴。师徒二人并不念经,也不打坐,只是整日在院子里煮茶,编蓑衣,种葫芦。春天里,老者和那童子在院子里胡乱选了地点,种下几十棵葫芦。葫芦藤蔓爬满院子,开一院子的白花。阴天下雨,云雾笼在四围山顶,老者便坐廊檐下对花煮茶。童子坐一侧,使一管秃笔习画,随画随丢。老者并不去管他,只顾自己喝茶。
偶尔,他也回过头来对王五说一句,好茶呀。
王五点点头。
老者又看着落对面树枝上一只麻雀说,真正的好日子天天也过得。
王五发一声喊,那麻雀惊飞了去。
老者便说,看看,走了。走了好。
回头又给王五斟茶。王五便笑。又帮老者将各色草木的种子装进许多的葫芦里去,然后挂在廊檐下的墙上。忙完,便从院子里掐一把白花夹在柴捆上,担着柴,一路吹着口哨回家。
村长老婆进城被车撞了,折一条腿,被人送进了城里的医院。村长得知,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将三个嗷嗷乱嚷的孩子交代给邻居,便坐手扶拖拉机进了城。
到了医院,见老婆两腿被吊着,周围几位穿白大衣戴口罩眼镜者忙来忙去。老婆见他来了,咧嘴大哭。
一大夫嚎道,叫个什么叫?别叫!
几个大夫便若开机器一样将他老婆两腿不住上下牵引。老婆益发叫起来。
村长过去骂一声,哭个屁?又对大夫骂,日你祖宗,这么个弄法?
大夫便罢了手,一长者过来说,你来治?
村长便不再说话,低了头,将带来的两箱吴家烤鸡放在门后,然后退出屋子,在走廊外排椅上坐着发呆,听屋里老婆杀猪一样地叫。
如此折腾两个多月,村长瘦成了面条儿。一日下午,村长正在院子里打水,大夫走来对他说,你老婆差不多了,下午做个片子,有了结果便可以出院。村长陡然精神起来,打一个在城里干瓦匠的兄弟那边拉来一辆排子车,铺两床被子等着。不一会儿,片子做出来了,一漂亮护士走过来对他说,有些不好,大概是骨头接歪了。村长一听便蹦起来,刚要骂又忍下了。将老婆背出来放在排子车上,盖上一床花被子。老婆两眼望着他。村长平淡地说,你等等,我去去就回来。村长找到那主治大夫,就说,大夫同志,我跟你说个话。那大夫过来说,什么事?村长凑近了大夫,模样儿微笑着在那大夫耳朵上放低了声说,我操你老婆。然后就走出来。
老婆躺在那里,身上满是落下来的黄树叶子。村长什么都不说,拉起老婆便回去了。
晚上便有人敲门,村长出来一看,是那山中古寺的老者。后面便是王五,挑一纸灯笼跟着。
王五小心着,说是让长老看看还能治不。村长便说,那请进吧。
老者进来,不说话。到得炕前,仔细摸摸那腿,就说,差了,差了。
村长慌忙问,还能治不?
老者要水净了手,走到院子里,对村长说,买一只乌鸡来,要当年的。
村长又慌又喜,连说不难,不难,早晨便让孩子买去。
老者不答话便走出去。村长要用手电去照路,王五说,这灯笼尽够了,你回吧。
村长只得站门口,见王五手中灯笼一路闪着、转着,从山道渐渐隐进山里去。
村长老婆的腿被那老者重新敲断,用那乌鸡并什么草石药物炼得一贴膏药贴在腿上,不消一月,便可撑两根拐杖走路了,且不觉出有什么疼痛。村长甚喜,不免在村里用高音喇叭将那老者和王五夸奖了半天。村里乡民也都出些好吃好用的物件给村长家送来。吴家店里的吴老头也着王五送过两只烤鸡来。村长感动之余,胃口大开,胡吃海喝,又渐渐丰满起来。老婆一能下地干活儿,他便四处开会去了。闲置时候,便总跟人谈起这长老的医术真正了得。于是县里各乡风闻大名,有人骨折,都不免来求老者救治。
老者初时总不拒绝。骑着病家牵来的毛驴出得山去,诊治完毕,回到寺里与那童子熬膏药。熬膏药不用草木,烧柿树的叶子。秋深时节,一老一小便打开寺门在山谷里扫柿叶。从寺门口到山下的石板路上落满了霜红的柿树叶子,一阶一阶扫起来,收在一间空屋里,当药柴用。有时王五也来帮着扫。
忙过数月,老者便有些疲惫神色。一日扫完柿叶,三人归到寺里去,坐廊檐下说话。天已冷了,老者与那童子着了皂色长夹袍,童子坐地上使那管秃笔在柿树叶子上写字。老者自宽袖中抽出一只竹箫来吹着。王五将手揣在怀里,蹲在一侧瞅着那钵煮沸的茶,一边听那老者不断地吹着什么曲子。那调子很凄凉。
吹罢,老者呷口茶,使衣袖擦过嘴,朝前一指说,那是什么?
王五循他手指看过去,见是一棵秃了的梧桐树,树身上,枝干上,爬满了千万只蝉子退下来的壳儿,仿佛是果实。
王五笑笑,说,好看。
老者笑笑,又吹过一支曲子,将那火续上些木柴,然后对王五说,你去找那村长,就说我死了,不要再来寻我。
王五看看老者,老者只是喝茶。又看那童子,那童子身边拥一堆腥红柿叶,随手写过的柿叶皆随风吹出墙外去了。
王五站起身来,下山去了。
自此,寺里重新得了清静。老者与那童子更不轻易出山外去了。只有王五天天进山打柴。在山半腰上将柴打满一担,抬头看一看漫山枯黄的野草,看看天空里慢慢飞的鹰,听着远处寺里风铃的琐碎声音,王五一点儿也不觉得寂寞。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得说,《一尺闲梦》这本书,真的有种让人“中毒”的魔力。一旦翻开,就很难再放下。作者的文笔,没有那些华丽的辞藻,却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它就像一位温婉的倾听者,用最真诚的语言,讲述着那些动人的故事。我喜欢书中对细节的刻画,那种对生活气息的捕捉,精准而生动,仿佛我就是那个亲历者。无论是清晨微露的薄雾,还是黄昏炊烟袅袅的景象,亦或是人物间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都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我常常会在某个情节处,久久不能平静,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担忧,为他们的选择而思考。这种强烈的情感共鸣,是我在阅读其他作品时很少能获得的。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原来最深刻的情感,往往蕴藏在最平淡的日常之中。它让我重新审视生活,去发现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美好,去体会那些被淡忘的情感。《一尺闲梦》给我的,不仅仅是阅读的乐趣,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对人生更深的理解。
评分《一尺闲梦》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它所展现出的那种沉静而有力量的美。在这个充斥着浮躁和喧嚣的世界里,这本书就像一股清流,缓缓地涤荡着我的心灵。作者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一种质朴的真诚,它能轻易地打动人心。我喜欢书中对人物情感的细腻刻画,那些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波澜,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都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我常常会在阅读的时候,不自觉地放慢速度,去体会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感受他们在那特定情境下的喜怒哀乐。书中对场景的描写,也同样精彩,无论是古色古香的庭院,还是烟雨朦胧的山村,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这种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让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故事,更是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阅读的乐趣,更是一种心灵的宁静和对生活更深的感悟。
评分第一次读到《一尺闲梦》这个书名,就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仿佛藏着一个温柔而悠远的故事。拿到书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作者的笔触,带着一种淡淡的古典韵味,却又不失现代的细腻。它没有那些过于煽情的描写,却能轻易地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我喜欢书中对生活细节的捕捉,那种对日常琐碎的描绘,充满了真实感,让人觉得书中的人物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一样。我常常会在阅读的时候,为书中人物的境遇而揪心,为他们的选择而思考,甚至会为他们的微笑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书中对情感的描绘,尤为出彩,那些含蓄内敛的爱意,那些难以言说的遗憾,都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我喜欢这种不落俗套的处理方式,它让故事更加耐人寻味。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找到了一处可以休憩的港湾,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去感受文字的力量,去体味人生的美好。
评分说实话,我不是那种对文学作品要求特别高的人,但我最近读到的《一尺闲梦》,无疑给了我巨大的惊喜。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突然发现了一个宁静的角落。书中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它能轻易地将我带离现实的烦恼,沉浸在那个由文字构筑的独特世界里。我喜欢它那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却能将最深刻的情感,最细腻的描绘,通过最朴实的语言传递出来。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原来最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那些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是那些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瞬间,那些人物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柔软。我常常会在读到某个情节时,不自觉地放慢阅读的速度,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可以让我更深入理解人物、理解故事的机会。我特别喜欢书中对环境的描写,那种置身其中的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仿佛我能闻到雨后泥土的芬芳,听到微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感受到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脸上的温暖。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让我觉得不仅仅是在阅读,更像是在经历一场别样的旅行。每一次翻开这本书,我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感悟,新的思考,它就像一个老朋友,总是能在恰当的时候,给我最温柔的慰藉,或者最深刻的启示。
评分《一尺闲梦》这本书,是我近期读到的一本让我眼前一亮的作品。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纷繁的世界里,找到了一片可以安放心灵的净土。书中的文字,没有刻意的雕琢,却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如同清泉般,缓缓流淌,滋润心田。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描绘,那些藏在日常琐碎之中的情感暗流,那些欲说还休的心事,都被作者捕捉得极为精准。我常常会在阅读的时候,为书中人物的遭遇而感同身受,为他们的坚韧而动容,也为他们的无奈而唏嘘。书中对场景的描绘,也同样精彩,无论是古朴的街巷,还是静谧的庭院,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我喜欢那种沉浸在书中的感觉,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我可以悠闲地品味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故事的吸引力,更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对生活的感悟。它让我明白,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经意的瞬间,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去体会。
评分《一尺闲梦》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它所传递出的一种悠远而沉静的气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作品都追求瞬间的冲击力和强烈的感官刺激,但这本书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它用一种温和而坚定力量,慢慢地渗透进读者的内心。作者的笔触,如同涓涓细流,不疾不徐,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描绘的场景,无论是古老的庭院,还是寂静的山林,亦或是繁华的市井,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在文字中鲜活起来。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那些潜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汹涌暗流,那些欲言又止的情感,都被作者捕捉得极为精准。我常常会在某个章节停下来,仔细回味书中的对话,去揣摩人物的一颦一笑,去感受他们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这种对人性的深度挖掘,让书中的人物不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鲜活个体。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与一位智者对话,从他那里获得关于生活、关于人生的智慧。它不是那种会让你惊呼“太精彩了”的作品,但它会让你在掩卷之后,久久回味,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和对生活更深的理解。
评分我一直认为,一本好书,就像一位默契的朋友,它总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你最恰当的回应。《一尺闲梦》就是这样一本书。初读之时,我并没有抱有太高的期待,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被书中营造的氛围所吸引,被其中细腻的情感所打动。作者的文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感染力,它不张扬,不喧哗,却能直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喜欢它对细节的刻画,那种对生活气息的捕捉,仿佛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书中的每一个场景,都仿佛被赋予了灵魂,充满了生命力。我会在阅读的时候,不自觉地放慢速度,去感受那份宁静,去体会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书中对情感的描绘,尤其让我印象深刻,那些含蓄内敛的爱意,那些深埋心底的遗憾,都被作者描绘得如此真实而动人。我常常会在某个情节处,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牵挂,为他们的选择而思考。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阅读的乐趣,更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和升华。它让我重新审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美好,去体会那些被遗忘的情感。
评分坦白说,我是一个比较挑剔的读者,很少有书能让我如此沉迷。《一尺闲梦》这本书,绝对是一个例外。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寻觅了许久,终于找到了那块最合心意的璞玉。作者的文笔,有一种天然的韵味,不落俗套,却又充满力量。它不像有些作品那样,上来就抛出惊天动地的事件,而是娓娓道来,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故事徐徐展开。我喜欢书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那些复杂的情感纠葛,那些隐忍的痛苦,都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却又不失含蓄。我常常会在阅读的时候,不自觉地放慢节奏,去品味其中的每一句话,去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书中对环境的描写,也同样令人赞叹,仿佛我能身临其境,闻到花香,听到鸟鸣,感受到微风拂过脸颊的温度。这种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让我觉得无比的满足。《一尺闲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故事的精彩,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和对生活更深层次的感悟。
评分我必须得承认,《一尺闲梦》这本书,在开篇的时候,我曾有过一丝丝的犹豫。毕竟,书名带着“闲梦”二字,总让人联想到一些飘渺虚无,或是过于抒情的内容。但当我真正投入阅读之后,我才发现,我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这本书所构建的世界,是如此的坚实而富有生命力,它并非只是空洞的文字堆砌,而是有着扎实的叙事基础和饱满的人物塑造。作者的文笔,可以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风格,它不像那些轰轰烈烈的叙述那样瞬间抓住你的眼球,而是像温热的泉水,缓缓地流淌进你的心里,慢慢地浸润,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爱上了这个故事,爱上了书中的人物。我尤其欣赏书中对细节的处理,那种对生活气息的捕捉,精准而到位。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叫卖声,还是庭院里花开花落的细微变化,亦或是人物之间一个眼神的交流,一句话语的停顿,都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仿佛我就是那个身处其中的旁观者,亲眼见证着这一切的发生。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整个故事变得格外真实可感,也让书中人物的情感更加细腻动人。我常常会在阅读过程中,为书中某个角色的遭遇而唏嘘不已,为他们的坚韧而感到由衷的敬佩,也为他们的不幸而默默心疼。这种情感的共鸣,是好书最动人的地方,也是《一尺闲梦》最让我着迷的特质。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光辉,也引发了我对生活更深层次的思考。
评分《一尺闲梦》这本书,初见书名,便被一股淡淡的古典韵味所吸引,仿佛能闻到古籍特有的墨香,或是温婉女子手中轻摇的团扇带来的微风。拿到实体书,纸张的质感更是出乎意料的好,触手温润,散发着一种沉静的力量,让人忍不住想立刻翻开,沉浸其中。我向来偏爱那些能在字里行间描绘出一方天地,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身临其境的作品,而《一尺闲梦》恰好满足了我的这一份期待。书中细腻的笔触,仿佛是画家手中最精细的笔刷,一点一滴地勾勒出那些或繁华、或宁静、或愁绪万千的场景。它不是那种一蹴而就的壮丽山河,而是更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工笔画,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细细品味。我曾在某个午后,窗外阳光正好,微风拂过窗帘,手里捧着《一尺闲梦》,读到书中某个关于月夜的描写,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就坐在了书中人物的身旁,一同望着那轮皎洁的明月,听着远处的虫鸣,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宁静与感慨。书中对人物情感的刻画尤为深刻,那些隐忍的、含蓄的、或是炽热的爱恨情仇,都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却又不落俗套。我常常会在某个情节处停下来,反复咀嚼字句,试图去理解人物内心的波澜,去感受他们在那特定情境下的喜怒哀乐。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觉得不仅仅是在读一个故事,更像是在经历一段人生,一段我可能从未有机会亲身经历,却又如此真实感人的旅程。读完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那种余韵,就像是一曲悠扬的古琴,在心底回荡,久久不散。
评分帮朋友在京东购买的图书,买过很多次了,值得信赖,一如既往地支持京东,也还会买其他商品,京东方便省心。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非常实在的价格,货真价实
评分送的画很好,很有诚意
评分挺好的,方便快捷,洪荒之力
评分不错,喜欢老树作品。
评分没有我想要的扇子……伤心……………………
评分买来送给朋友的,朋友很喜欢
评分贵啊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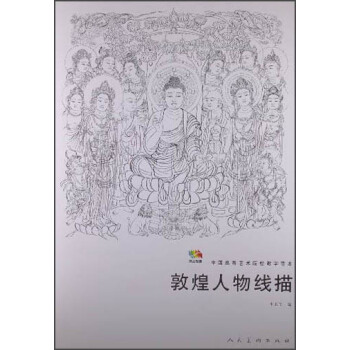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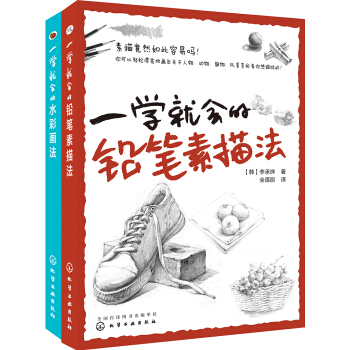

![去伦敦上插画课 [London Illustrate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72921/rBEhWVHfprcIAAAAAAYNLFrY6gIAAA-hwJsjxUABg1E1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