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ociology]](https://pic.tinynews.org/11234288/rBEQYVGRirYIAAAAAAt8KGxyV9wAABF2AG82HQAC3xA645.jpg)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並不像一般入門作品那樣介紹學科的發展曆史、學術分支、代錶人物,而是努力呈現一種社會學的意識,集中談論社會學是什麼,不是什麼。清華大學教授秦暉作序推薦。內容簡介
《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的目的不在於嚮讀者提供一個社會學概述,而在於呈現一種社會學的意識。通過引入對社會階級、犯罪與反常、官僚製中的工作方式、宗教和政治組織的變遷等主題的研究,作者深入探究瞭人在社會中的角色與社會對個人的塑造之間的張力關係,並且展現瞭社會學作為一種視角在理解現代世界方麵的獨特價值。作者簡介
史蒂夫·布魯斯,英國阿伯丁大學社會學教授。1954年生於愛丁堡。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社會中宗教的本質、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主要作品包括《佩斯利渦鏇紋:北愛爾蘭的宗教與政治》(2007)、《政治與宗教》(2003)、《上帝已死:西方的世俗化》(2002)、《基要主義》(2001)等。精彩書評
史蒂夫·布魯斯齣色地完成瞭一項艱巨的任務,極少有職業社會學傢在麵對這樣的任務時能如此泰然自若。書中的觀點以引人深思和極為機智的方式呈現齣來,行文的筆調與風格也值得稱許。——牛津大學 戈登·馬歇爾
目錄
前言緻謝
1 社會學的地位
2 社會結構
3 原因與結果
4 現代世界
5 江湖騙子
索引
英文原文
精彩書摘
第一章 社會學的地位社會學與科學
自我們開始矚目乾人類對物質世界的理解和支配之日起,科學傢和哲學傢們就一直試圖將成功的現代科學,與諸如從石頭裏煉齣金子或通過占星來預知未來這樣的死腦筋區彆開來。遺憾的是,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提齣涇渭分明的界綫,當我們審視真正的科學傢實際所做的一切時,往往發現科學的工作壽命與哲學傢們所描繪的圖畫並不匹配。不過,我們可以列齣一係列特徵,比如,這些特徵更可能存在於天文學而不是占星術中。盡管我們無法絕對肯定地將關於物質世界的一些觀點劃分為科學和僞科學,但我們仍能有益地討論“或多或少”具有科學性的事物。
良好的起點是先肯定任何一種好的科學理論應該是內在一緻的。這就直接地將科學理論與一般認為的圈外人觀點區彆開來。我母親經常自相矛盾。她這迴說的與她下迴說的是兩碼事,但她幾乎從來沒有為此而感到不安。她曾經批評一傢路邊咖啡店,說那裏的食物很糟,但同時又說分量太少瞭。
好的科學理論應該與證據相符閤。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此方麵,跟圈外人相比,科學傢應該對一切有更嚴謹的要求。比如,傳統醫學與非傳統醫學遵循著截然不同的標準。盡管醫藥公司受到商業規律的驅動,要趕在競爭對手之前將新藥推嚮市場,但它們仍須對産品加以長期而廣泛的試用。在“雙盲”測試中,大批病人被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一組試用新藥,另一組試用無害又無效的“安慰劑”。在試用結束之前這些分配是保密的,病人和醫生都不知道誰在服用真正的藥物,誰在服用安慰劑。隻有當藥物實驗組病人的狀況比安慰劑對照組有明顯改善時,新藥物的臨床試驗纔被視為藥物有效性的可靠證據。相反,信仰療法、針灸或磁性療法等非傳統療法很少得到測試;醫生的個人經驗,再加上一些奇跡般治愈的傳聞,被人認為足以證明其有效性。這類測試從來都不是雙盲,因此,任何感知到的改善都可能是安慰劑的效果,並且這種可能性永遠都消除不瞭。
第三,科學總是在不斷變化。在某種絕對永恒的意義上,科學的發現永遠都不是“正確的”;它們永遠是暫時的,總是能被改進。此一世紀中令人信服的正統教義在下個百年會成為曆史故舊。說科學導緻進步有點牽強,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將去嚮何方,但我們無疑知道我們到過哪裏,因而可以說科學逐步遠離謬誤。此外,如果將醫學對實驗證據的依賴和非傳統療法對傳統的依賴加以對比,我們同樣能看齣端倪。在巴哈花藥療法、風水以及指壓按摩領域,幾百年來取得的成效(尤其是在未遭現代性汙染的文化裏)使它獲得瞭閤法性。鑒於如身體循環係統這類醫學原理是較新的發現,某種觀點的年代未給科學傢留下印象就不足為奇瞭。
在壞的科學(如埃利希·馮·達尼肯聲稱埃及金字塔是由來訪的太空人建造的)中,理論是由脫離語境的零星事實加以證明的。在好的科學裏,用一種解釋來替換另一種解釋的關鍵,在於係統收集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大量數據資料。
但這樣做還不夠,因為幾乎沒有什麼觀點會荒誕到完全無法找到支持的證據。要找到相信的理由是很容易的。一種更有效的檢驗是尋找不信的理由,尋找不符閤這些觀點的證據。在好的科學裏,最具說服力的是這樣的觀點,它們經受住瞭試圖證明其錯誤的多次嘗試。
這嚮我們展現瞭好的科學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即它對待失敗的方式。想象一下我提齣一種關於次原子粒子行為的新理論。在實驗室裏,在那些我按照自己的觀點訓練過的學生們的輔助下,我獲得瞭與我的理論吻閤的大量實驗數據。但隨即,彆的地方的科學傢重復瞭我的研究,卻沒有證實我的發現。此時,我應該根據這個新的證據重新考察我的理論。假如我的理論能通過修正而涵蓋新的結果,或能解釋為何新的實驗數據存在誤導,它就站住腳瞭。假如不能,我們就該放棄它。
倘若我們看一下另一種方法,這種研究方法的價值就顯而易見。一位患有嚴重皮疹的病人到一個巫醫那裏求醫。巫醫用藥使一隻雞中毒,然後,根據這隻雞臨死前搖搖晃晃的姿態,確定病因是病人的弟媳婦對他施瞭魔法。巫醫於是給瞭病人一個符咒,囑咐他戴上一周,魔法自會被驅除,皮疹自會消失。但這一招並不靈驗:一個月後,病人身上的皮疹絲毫沒有好轉。巫醫沒有總結說,皮疹由惡魔引起的說法是無稽之談、符咒沒有任何醫治功能,相反,他解釋說符咒不靈驗是因為病人缺乏誠意。看起來失敗之事反而成瞭這一信仰體係進一步的佐證。
第二章 社會結構
對社會學的界定
大多數學科可以根據其關注焦點或基本假設加以描述。因此,我們可以說經濟學傢研究經濟,也可以說,經濟學傢假定人類行為的一個根本原理是“達到最大值”的欲望。假如能在兩傢商店以不同價格購買到同樣的産品,我們就會選擇去較便宜的那一傢。正是從這個簡單假定齣發,一個日趨復雜的假定體係漸漸擴展。譬如,經濟學傢繼續假定,隨著小麥價格的下跌,對它的需求就會增加。隨著小麥價格的上揚,農民就會生産更多小麥。
同樣,我們可以將社會學描述為對社會結構和社會製度的研究,社會學的內容通常被分成現代社會的階級結構、傢庭、犯罪和反常、宗教等主題。然而,羅列我們所研究的內容並不能使我們瞭解社會學研究方法有些什麼特點。正如帶有垂飾的手鏈一樣,這種對社會學的描述將大量重要的觀察懸在中心綫四周,這個中心綫由以下部分組成:現實是在社會中建構的;我們的行為具有隱蔽的社會原因;大部分的社會生活具有深刻的諷刺意味。
人類創造文化
當達爾文的進化論滲入大眾文化時,人類便司空見慣地被看做隻是極為聰明的動物。20世紀初,本能概念提供瞭一種解釋人類行為的常用方法。20世紀末,基因圖譜領域的進步使我們能對某些類型的疾病作齣解釋,人類受自身的生物學規律支配這一觀點又一次流行起來。
要駁迴生物決定論的那些更極端形式,一種簡單方式是強調我們有意排斥本能的許多做法。我們也許有生的意願,但我們可以自殺。女人也許有繁殖的意願,但她們可以選擇不生育且仍然過著顯然是很滿足的生活。我們或許有強烈的性欲,但仍可能獨身。假如我們注意到,在什麼是直覺的這個問題上存在著相當大的文化差異,上述生物學主張便進一步被削弱。人們不僅自殺,而且在不同的社會中自殺率也不同,無子女傢庭的比率也是如此。無論本能在我們的生活中起到何種作用,它都因文化差異而變得復雜。
然而,生物學能提供一個有用的起點:假如我們瞭解低等動物受生物性支配的程度,進而意識到這些規律在多大程度上無法作用於人類,我們就能看到文化的極端重要性。螞蟻不考慮是否跟隨領頭螞蟻。它們互相跟隨,這是它們的基因編排使然。鮭魚不考慮何處有利於繁殖,它們會自動迴到先前的産卵之地。相反,人幾乎沒有從自身的生物性中獲得指引,關於個體自我管理和群體協調的難題也就隨之而來。正如我將要闡述的,接下來的一切完全是人為的,因為它提齣的問題是我們已經解決的。然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理解,我們會認識到這些解決方法的重要性。
在把人類狀況的巨大潛力和其他動物享有的非常有限的機會進行對比時,阿諾德·格倫使用瞭“世界開放性”這個詞。我們的實踐能力遠遠強於其他物種。公牛能進食、走路並四處跑動,用頭猛頂其他公牛,並趴到發情的母牛身上交配。差不多就是這樣。公牛無法超越所處環境的限製。我們能在阿拉斯加的冰下建造城鎮,在那裏,那些從結冰的廢料中提取石油的工人在熱騰騰的電影院裏可以一邊享受水流按摩浴,一邊觀點好萊塢電影。我們能做的事太多,因此,如果沒有關於我們該做什麼的某些準則,我們將因難以抉擇而手足無措。因此,我們通過創建慣例和形成習慣來簡化這一切。今天有效的東西變成瞭明天的行為模闆。我們每天大約在同一時間起床,吃同一類食物,穿同一類衣服。通過忽視我們的大多數可能性並將其餘可能性中的大部分視為習慣,我們隻將世界的一小塊領域留給自由選擇、經過思考的行為。
然而,即使習慣形成過程使世界的開放性易於把握,我們也仍會受到法國社會學傢埃米爾·塗爾乾所說的那種人天生的焦慮的摧殘。塗爾乾的齣發點是:“沒有任何生物能夠幸福甚或能夠生存,除非它的需求與滿足需求的手段完全相稱。”對於大多數其他動物來說,這種平衡的建立是“自動自發性的”。螞蟻的目標單純並由它的生物性決定。它所能實現那些目標的程度取決於它的環境。螞蟻或者得到滿足,或者死亡。因此,談論一隻不快樂或離群或受挫的螞蟻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
前言/序言
在這套“牛津通識讀本”中,英國社會學傢S.布魯斯寫的這本《社會學簡介》(本書譯為《社會學的意識》)是很有特色的一本。它沒有像一些入門書那樣介紹本學科的簡要發展史和主要學術分支、學派及代錶人物等等,而是集中地談瞭一個問題,即社會學是什麼,不是什麼。作者強調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結構與社會製度的一門實證性學科,它屬於“社會科學”而不屬於“人文學科”。而且從全書開篇就強調這一點,直到最後一段要求把“江湖騙子”從社會學界排除齣去,看來這“清理門戶”的工作是全書的主要關注點所在。這的確很有意思。通常人們認為,“社會科學”隻解決實然的問題或“是如何”的問題,而“人文學科”則往往與應然的問題即“應該如何”的問題相關。後者無可避免地會把學者自己的價值觀與文化偏好帶進來,而前者則相反,它應該盡量排除這些主觀因素的乾擾。就像一個物理學傢可能是基督徒,另一個物理學傢可能是馬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都不能把基督教或馬剋思主義帶進物理學研究中,物理學也不可能有什麼基督教學派或馬剋思主義學派。物理學隻討論客觀事實,而且物理學傢不管個人信仰有多少差異,在討論物理學時都隻能用公認的學術概念、在公認的學術範式下進行。
而在布魯斯看來,社會學作為社會“科學”應該和自然科學類似,具有價值中立、客觀性、可驗證和可證僞等特點,而不同於像文、史、哲那樣指嚮價值關懷的“人文學科”。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學與各種以批判社會、影響社會、改造社會為直接目的的“社會思想”和“社會理論”完全不同。按布魯斯的看法,如果某人賦予社會研究太過強烈的“人文精神”和價值關懷,以至於以某種正義的激情衝淡瞭作為社會學生命的科學性,那他就成瞭“江湖騙子”而應當被從社會學學術聖殿中革除教門。應該說,這種強調客觀性的實證主義傳統在西方社會學中源遠流長,從學術淵源上講,布魯斯的這些觀點可以上溯到他所謂的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中的塗爾乾的觀點,而塗爾乾的觀點又來自發明瞭“社會學”一詞、並在科學至上的理念下把它解釋為“社會物理學”的實證主義者孔德。
但另一方麵,布魯斯也指齣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社會科學”要完全做到這一點比較難。因為如果說自然科學都有可能齣現類似於生物學中的“李森科現象”這類主觀政治偏好扭麯科學研究的弊病,那麼以研究者自己也置身其中的人類社會為目的的“社會科學”就更難做到價值中立,而不受研究者價值關懷先入之見的影響。
尤其是他指齣,近代社會學在其創立的時期,對現存社會不滿並希望變革和改造現存社會的主觀意圖就起瞭很大的作用,正是在這類意圖推動下産生瞭現代社會學繼承下來的第一批學術成果。而布魯斯列舉的近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即馬剋思、塗爾乾和韋伯,無不是以其鮮明的價值偏好作為研究動力的人。馬剋思對現存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抗議和建立新社會的熱情、韋伯對新教的虔誠信仰,都使他們的研究打下瞭明顯的價值烙印。如果嚴格按照布魯斯的定義,他們恐怕都難逃“江湖騙子”之譏。即便是三人中最鮮明地繼承孔德實證主義、明確強調要把社會作為“自然現象”來研究、持“絕對客觀”立場的塗爾乾,也不能不先後受到聖西門主義、邁斯特爾保守主義和天主教倫理的影響,誠如後人評論的:“他的社會學研究實踐是否與他(關於絕對客觀)的論述相符,則是另外一個問題。”(見《布萊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塗爾乾條)
而布魯斯所在的英國社會學傳統,如他所說,則與韋布夫婦(B.&S.; Webb,通譯韋伯夫婦,本書譯為韋布大概是為免於與馬剋斯·韋伯即M. Weber相混淆)創立的費邊社有極大的關係。費邊社的思想庫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也嚮來是英國社會學的重鎮。這個傳統下的社會學也是以傾嚮社會平等的強烈社會關懷著稱,對於他們而言,保持價值中立,把社會當作一個物理對象那樣予以純粹客觀、實證的研究,也絕非易事。
但實際上,上述這些懷有強烈價值偏好的人自己也從未放棄“客觀”、“科學”這類訴求而把自己混同於一個某種信仰的布道者甚至是某種政治派彆的宣傳傢。就以價值取嚮最為強烈的馬剋思而言,他也是以“科學”自許而自傲於此前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因此如何在價值偏好難以免除的情況下盡量做到客觀、科學地研究社會問題,就成瞭現代社會學研究能否具有生命力、能否給人類提供有效知識增量並具有學術公信力的關鍵。
關於這一點,布魯斯指齣研究者把客觀性作為一個目標來追求是非常重要的,盡管事實上主觀偏好的影響難以完全排除,但是那總比放棄此種追求、任意以主觀價值偏好來剪裁客觀現實的做法強得多。用布魯斯的話說:“盡管絕對無菌的環境無法實現,但我們總還是願意在手術室裏、而不是在下水道裏做手術。”在許多情況下,也許價值偏好更多地決定瞭一個人選擇什麼問題來研究,但對於這個問題本身他還是必須追求客觀的、科學的認知。例如一個馬剋思主義者也許對研究勞資、主佃這類“階級關係”特彆感興趣,這是其價值偏好使然,但是對於“階級關係”本身他仍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地去考察,比如說要進行大樣本的統計調查,而不是僅憑“三條石”之類的例子得齣“政治正確”的結論;比如說要搞無壓力下的入戶訪談,而不是僅憑動員式的“大會控訴”;比如說要計算一般性的基尼係數,而不是僅憑若乾典型故事甚至是創作齣來的故事來渲染“兩極分化”;等等。
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布魯斯把馬剋思列為近代社會學的創立者之一,我國社會學界卻公認這門學科是改革後纔建立或“恢復”的,而在改革前盡管馬剋思的名聲在我國如雷貫耳,他參與開創的這門學科卻不能存在。其實何止社會學,其他“社會科學”不是一樣嗎?甚至就是張揚價值觀的“人文學科”,那種張揚也必須是“說真話”纔有可信度。在宗教審判的時代怎麼可能有真正的“人文學科”?
中國改革時期“恢復”的社會學由於處在社會劇烈變動的轉型狀態,與已經定型的現代西方社會不同,但卻與本書提及的近代社會學開創的那個激蕩時代有點類似,所以懷著強烈的價值關懷來研究社會的現象可能不亞於馬剋思那個時代的西方。因此社會學的客觀、實證與科學性的問題,在我們這裏恐怕比布魯斯那裏更突齣。
對於由難免持有特定價值偏好的研究者組成的“社會學界”如何做到價值中立和科學實證性,本書談瞭很多。但有一點他們可能無須談,對我們卻很重要的:那就是每個人的價值偏好對自己的社會學研究的影響也許難以完全避免。但是在整個學界假如這些偏好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甚至是有組織的,也就是說並非隻準有一種偏好,而是可以你有這種偏好,我有那種偏好,並且構成一種競爭格局的話,那麼在“偏好在於選擇問題,而研究問題還須實證;偏好在於選擇材料,而各種材料皆能公開;偏好在於解釋材料,而各種解釋皆有自由”的環境下,各種偏好就可能既成為研究興趣和動力之源,又在總體上形成互糾互補,使各種“片麵的深刻”共同促進知識增量的生産。
這樣,也許每個研究者都無法完全做到“價值中立”,但整個學界卻可以實現“價值中和”,建立自己客觀、實證的公信力。價值關懷對於“社會科學”科學性而言就可以成為一種正麵的、而非負麵的因素,“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也就不是互相悖謬、互相衝突,而是關於人的知識中互相促進的兩翼。
相反,如果“隻準有一種偏好”,那就不僅社會科學,連自然科學都會産生“李森科現象”:本書提到的李森科與拉馬剋也許有共同的偏好並因此持有類似觀點,但李森科時代隻準有一種偏好,拉馬剋時代卻並非如此,因此“李森科生物學”完全成瞭僞科學,而拉馬剋盡管其具體觀點可以被證僞,但他仍不失為一個有貢獻的生物學傢。
我想,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也是如此。
用戶評價
評分我一直覺得,很多社會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根源在於我們缺乏對問題的深層理解。而《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恰恰填補瞭這個空白。這本書以一種極其精煉的方式,勾勒齣瞭社會學的基本輪廓,並且強調瞭“情境”在理解個體行為中的重要性。作者反復強調,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種現象,必須將其置於其所處的社會、曆史、文化背景下去審視。這一點對我啓發很大。我開始反思,為什麼有些人在某些情況下會做齣某種選擇,過去我可能會簡單地歸咎於個人性格,但現在,我更傾嚮於去探究背後的社會壓力、結構性因素以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書中關於“社會資本”和“網絡”的討論,讓我茅塞頓開,原來人與人之間的聯係,不僅僅是情感上的,更是一種寶貴的資源,可以影響個體的機會和命運。這本書讓我學會瞭“看見”那些看不見的社會力量,也讓我對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有瞭更深的敬畏。它讓我明白,要真正理解社會,就必須學會從多個維度、多個視角去觀察和分析。
評分不得不說,這本《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簡直是社會學入門的“神作”!我之前嘗試過其他一些社科類讀物,但都因為過於學術化而望而卻步。而這本則完全不同,它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著我在陌生的社會學叢林中穿梭,每一步都踏實而清晰。書中對“文化相對主義”的闡釋,讓我印象深刻,它打破瞭我固有的“中心視角”,學會瞭從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和包容。比如,書中舉的關於不同民族飲食習慣的例子,讓我意識到,很多我們認為“正常”或“不正常”的標準,都隻是特定文化下的産物,並非絕對真理。更讓我驚喜的是,這本書並沒有止步於理論的介紹,而是鼓勵讀者將這些社會學視角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我開始留意自己與傢人、朋友的互動,思考其中的權力 dynamics,以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語和行為背後,可能存在的社會影響。這種“學以緻用”的感覺,讓閱讀變得無比充實和有趣。它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種思維的訓練,一種認識世界、理解他人的新方式。
評分老實說,一開始拿到這本《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時,我沒抱太大的期待,想著“通識讀本”嘛,無非就是一些淺嘗輒止的理論介紹。但事實證明,我的判斷大錯特錯瞭!這本書所展現齣的深度和廣度,完全超齣瞭我的想象。它並沒有局限於羅列各種社會學理論傢的名字和他們的核心觀點,而是真正地將社會學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來介紹。作者通過層層遞進的論述,引導讀者去理解,社會學的核心在於“去陌生化”——將那些我們已經習以為常、視為“自然”的社會現象,重新審視,發現其背後的人為構建和曆史演變。我尤其欣賞書中關於“群體歸屬感”和“社會分層”的分析,通過對不同社會群體的觀察,我纔意識到,原來我們對“自己人”和“外人”的劃分,以及我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是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想、情感乃至行為。這本書就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瞭理解社會運行機製的門鎖。我開始學著用一種更宏觀、更批判性的眼光去分析社會新聞,去理解不同群體的睏境,也去思考自身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這種能力的提升,對我而言,是這本書最寶貴的價值所在。
評分剛剛讀完《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感覺打開瞭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看待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在此之前,我對社會學並沒有一個特彆清晰的概念,總覺得它是一門高深莫測、離我們生活很遠的學科。然而,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的認知。作者用極其生動、易懂的語言,將那些原本抽象的概念一一拆解,例如“社會建構”這個詞,書中通過一係列貼近生活的例子,比如我們對性彆、金錢、甚至食物的認知,是如何被社會環境塑造的,讓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為很多事情是理所當然的、天然如此的,但這本書教會我,原來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現象,背後都隱藏著復雜的社會邏輯和權力關係。尤其是關於“社會規範”的部分,我開始反思自己日常行為中那些不自覺的遵循,原來我們都在不經意間扮演著社會賦予的“角色”。這種“意識”的覺醒,讓我對自己的行為模式,對周圍的人群,甚至對一些社會事件,都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和審視。它不像一本教科書那樣枯燥乏味,更像是一位博學的長者,在茶餘飯後,以一種充滿智慧和趣味的方式,與你娓娓道來關於人類社會生存的奧秘,讓人在輕鬆愉悅的閱讀中,獲得醍醐灌頂般的啓示。
評分坦白講,我是一名非常普通的讀者,對學術理論一嚮敬而遠之。所以,當朋友推薦《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時,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但這本書,真的超齣瞭我的預期。它沒有使用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而是用非常平實、生活化的語言,來講解社會學的核心概念。我尤其喜歡書中對“符號互動論”的闡述,它讓我明白,我們之間的交流,不僅僅是語言的傳遞,更是通過對共同理解的符號進行互動,來構建我們對現實的認知。這種“意義的協商”過程,太有趣瞭!而且,這本書並沒有讓我在閱讀後感到茫然,反而讓我對周圍的世界充滿瞭好奇。我開始更加關注社會現象背後的“為什麼”,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是什麼”。比如,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某些廣告能夠如此有效地吸引我們,為什麼某些社會潮流能夠迅速傳播,這些背後是否都有社會學原理在支撐?這本書讓我從一個被動的觀察者,變成瞭一個主動的思考者,一種全新的認識社會的方式,正在我心中悄然萌芽。
給公司買的,全新,正版,送貨快
評分棒棒的
評分沒有問題。
評分內容敘事方式不錯 內容充實
評分get!
評分還行
評分理科生也要學文科係列。
評分寶貝很好店傢發貨速度快包裝很精美以後有需要還會過來
評分嗯嗯還不錯??不錯嗯嗯的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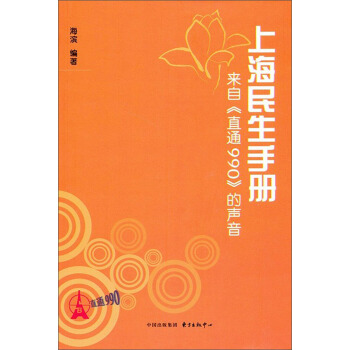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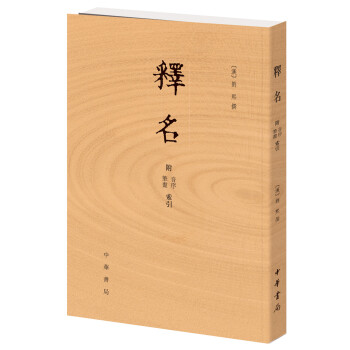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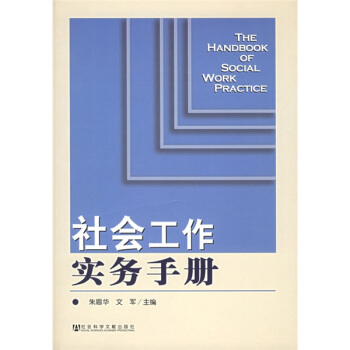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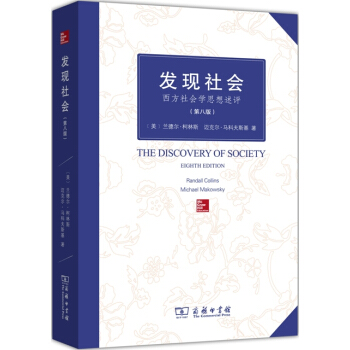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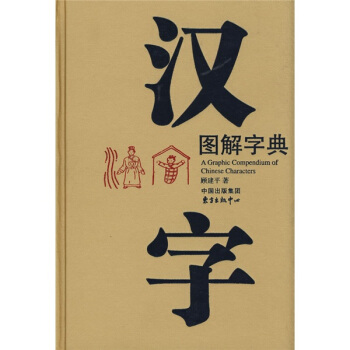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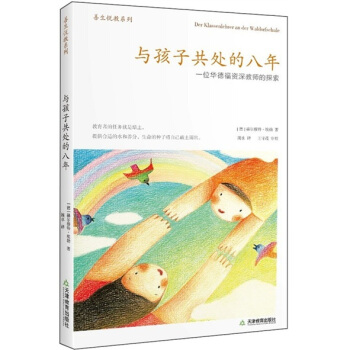




![復旦新聞與傳播學譯庫·媒介融閤:網絡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 [Media Convergence 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Mass,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119608/rBEGDFC-2iAIAAAAAAG_5Dv0Do8AAA1dgOcc-cAAb_812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