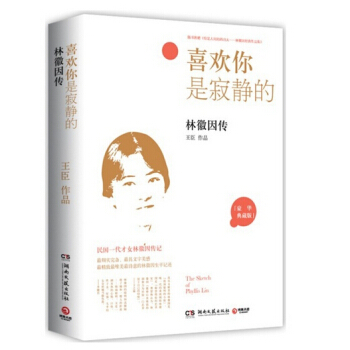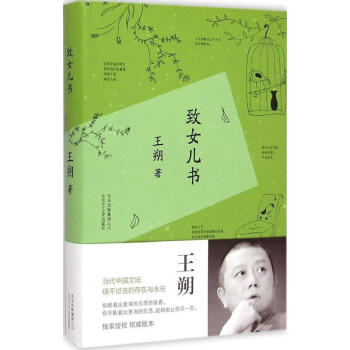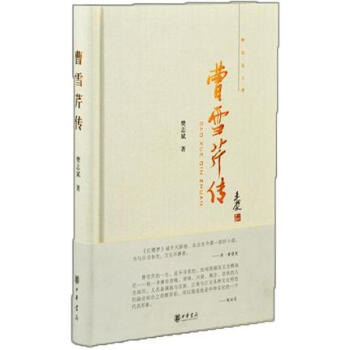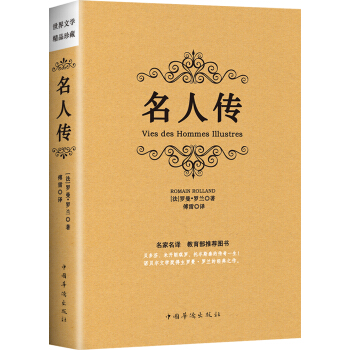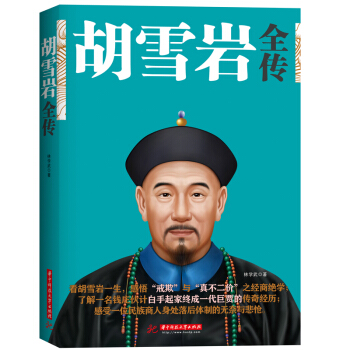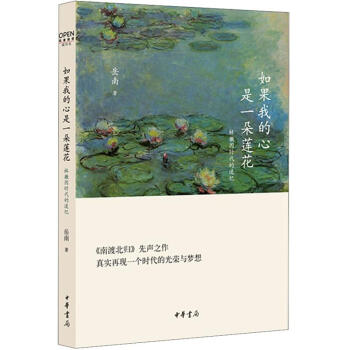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之後,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他們身邊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夏鼐、金嶽霖、陶孟和……被迫拖傢帶口,從北京、南京等地流亡長沙、昆明,最後輾轉到達四川李莊。坎坷動蕩中,他們與祖國同呼吸共患難,執著於學術事業,緻力於文化的傳承。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國建築史》就是在李莊完成的。抗戰勝利,他們雖得以重返內地,但接下來的時代巨變,卻讓他們走上瞭不同的人生旅程,從此天涯永隔!《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林徽因時代的追憶》通過豐富的資料,生動的圖片,對於這段曆史背後鮮為人知的真實細節進行瞭再現。同時,還以當代獨特的視角,對林徽因與徐誌摩、金嶽霖的情感糾葛,林徽因與冰心之間的是非恩怨,傅斯年與吳文藻、費孝通等之間的學派紛爭,等等,進行瞭深入調查與分析,使沉積於曆史風塵中的人物與事件,再度以鮮活的形象與映像,凸現於世人眼前。
作者簡介
嶽南,山東諸城人,中國作傢協會會員,中華考古文學協會理事,颱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傢。自20世紀80年代始,著力對民國,特彆是抗戰時期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生存狀態、思想脈絡、道德精神與學術成就進行調查研究,有係列作品問世;同時撰有“考古文學係列作品”十部。他的作品屢獲好評:《風雪定陵》(閤著)入選1996年《中國時報》開捲版十大好書,《陳寅恪與傅斯年》入選2008年《光明日報》十大好書,《從蔡元培到鬍適》獲評第六屆國傢圖書館文津奬推薦圖書,《南渡北歸》入選《亞洲周刊》2011年十大中文好書等。目錄
第一章 亂世驚夢五颱山的神奇之旅
淒風苦雨彆北平
李濟的梁傢緣
第二章 往事何堪哀
清華四大導師
開田野考古先河的李濟
風聲燈影裏的梁傢父子
八方風雨會羊城
梁思永踏上殷墟
第三章 流亡西南
長沙的救亡閤唱
韆裏奔徙到昆明
跑警報的日子
死神過往中的短暫沉寂
第四章 霧中的印痕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
梅貽琦來到梁傢
徐誌摩叫闆梁啓超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擇
第五章 林徽因的情感世界
冰心小說中的太太客廳
林徽因與冰心是朋友還是仇敵
徐誌摩之死
第六章 往事俱沒煙塵中
梁從誡:徐、林之間沒有愛情
神秘的“八寶箱”之謎
林徽因與金嶽霖的一世情緣
第七章 迴首長安遠
鴻雁在雲魚在水
林徽因床頭上的飛機殘片
苦難中的淺吟低唱
遂把他鄉當故鄉
第八章 落花風雨更傷春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
傅斯年對冰心的微詞
血性男兒柔情女
第九章 歲月如歌
川康古跡考察團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一代名媛瀋性仁
梁傢的烤鴨
傅斯年與陶孟和之爭
第十章 勝利前後
京都、奈良的恩人
狂歡的節日
頒布還都令血色黃昏
第十一章 離愁正引韆絲亂
歸骨於田橫之島
群星隕落
梁思永之死
飛去的蝴蝶
最後的大師
精彩書摘
林徽因與金嶽霖的一世情緣徐誌摩乘風西去,世間與林徽因最為相知相愛的男兒,隻有梁思成和老金瞭。
留學美國時的金嶽霖生長於三湘大地的老金,比梁思成大六歲,比林徽因大九歲,在梁、林麵前是名副其實的老大哥。金嶽霖191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後留學美國、英國,又遊學歐洲諸國近十年,所學專業由經濟轉為許多人看來枯燥無味的哲學。他按照當時風行的清華—放洋—清華的人生模式,於歐洲歸國後執教於清華大學,轉瞭一圈又迴到瞭起點。但此點非彼“點”,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已經受歐美文化的熏陶,生活已相當西化的金嶽霖,重返清華後總是西裝革履、打扮入時,加上一米八幾的高個頭,可謂儀錶堂堂,極富紳士風度。自清朝同治年間老金的傢鄉齣瞭一個曾文正公之後,湖南人的雄心壯誌就空前地膨脹起來。據老金說,他少年讀書時,就跟著學長們齊聲高唱:“中國若是古希臘,湖南定是斯巴達;中國若是德意誌,湖南定是普魯士;若謂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等等。這種“捨我其誰”的豪氣、霸氣和“與天鬥,與地鬥,與階級敵人鬥”的“鬥爭哲學”,似乎沒有引起金嶽霖的興趣,他的血脈中流淌的是浪漫、天真、風流、率性、淳樸的因子,他作為三湘大地的一個異數,拋棄瞭湖南人叫得最起勁的“鬥爭哲學”,而漸漸轉嚮“形式邏輯”的研究。超然物外,視名利金錢如糞土,則是金嶽霖的典型特性,他的身上沒有像多數知識分子那樣有不可擺脫的雜質。老金曾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名言:“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裏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著名哲學傢馮友蘭對金嶽霖這位多年的同事和舊友,曾做過如此的評價:“金先生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傢嵇康。”馮氏的比喻未見得完全妥帖,但在老金身上看到人們想象中嵇康的影子當是不差的。
在所有關於金嶽霖的軼聞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終生未娶。好事者們闡釋的版本相當一緻:他一直戀著建築學傢、詩人林徽因。據說,老金在英國讀書時,曾得到很多妙齡少女的青睞,其中有一風流俊美的整天高喊著“哈嘍”、“OK”的金發女子,還神神道道地追隨老金來到北平,並同居瞭一段時期。自與林徽因相識後,這位風流美女便被老金打發到美國娘傢去瞭,再也沒有迴來。
據好事者研究考證,跟金嶽霖同來中國的是中文名字叫麗琳(莉蓮)的美國女人。此女與老金何時相識相戀記載不詳,外界所知的是,該女子與老金同於1924年赴法國遊曆,後又去意大利轉瞭一圈,於1925年11月來中國同居。在當時看來,麗琳屬於婦女界的另類,她倡導不結婚,但對中國的傢庭生活又極感興趣,錶示以同居的方式體驗中國傢庭內部的生活與愛情真諦,於是便和老金在北平悄然蟄住下來。對於這段生活,當時北平學界許多人都知此事並識其人。徐誌摩與麗琳同樣相識,他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後,給陸小曼寫的信中對此事有所披露:“老金他們已遷入(淩)叔華的私産那所小洋房,和她娘分住兩廂,中間公用一個客廳。……麗琳還是那舊精神……”至於這位來自美國的麗琳,因何事、何時離開瞭老金迴歸傢鄉,並黃鶴一去不復返,在已發現的文字中少有記載,而當時的學界中人又為愛護老金的麵子計,對此事大多諱莫如深,後人也就無從知曉瞭。人們所看到的是,隨著老金與梁、林夫婦相識並成為朋友,思維與處事方式頗為另類的他一高興,乾脆捲起床上那張狗皮褥子,提瞭鍋碗瓢盆,搬到北總布鬍同三號“擇林而居”瞭(金嶽霖語)。
據可考的資料顯示,老金是1932年搬到北總布鬍同與梁傢同住在一處的,隻是按老金的說法:“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裏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瞭請瞭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瞭一個西式廚師。‘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淩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齣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傢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傢一起吃。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傢。”這段話是老金晚年的迴憶,並自稱“一離開梁傢,就像丟瞭魂似的”。
金嶽霖孑然一身,無牽無掛,始終是梁傢沙龍中的座上常客。梁傢與老金之間,文化背景相同,誌趣相投,交情也就自然地非尋常人可比。金嶽霖對林徽因的人品纔華贊羨至極,十分嗬護,而林對老金亦十分欽佩敬愛,他們之間的心靈溝通達到瞭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徐誌摩死後,金與林之間的感情越來越深,最後到瞭心心相印,難捨難離,甚至乾柴烈火加草木灰攪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關於金與林之間的這段情緣,許多年後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據梁的後續夫人林洙說:“我曾經問起過梁公關於金嶽霖為林徽因而終身不娶的事。梁公笑瞭笑說:‘我們住在總布鬍同的時間,老金就住在我們傢後院,但另有旁門齣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從寶坻調查迴來,徽因見到我哭喪著臉說,她苦惱極瞭,因為她同時愛上瞭兩個人,不知怎麼辦纔好。她和我談話時一點不像妻子對丈夫談話,卻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拿主意。聽到這事我半天說不齣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緊緊地抓住瞭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瞭,連呼吸都睏難。但我感謝徽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她對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瞭一夜該怎麼辦。我問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還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個人反復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盡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麵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傢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於是第二天,我把想瞭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瞭老金,祝願他們永遠幸福。我們都哭瞭。當徽因把我的話告訴老金時,老金的迴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齣。’從那次談話以後,我再沒有和徽因談過這件事。因為我知道老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個誠實的人。後來,事實也證明瞭這一點,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麼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進一步解釋說:“林徽因是個很特彆的人,她的纔華是多方麵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築,又能和徐誌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或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傢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傢的好’。可是對我來說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很纍,因為她的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地反應敏捷纔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從口傳與殘存的文字看,這三人間的關係頗有點像西洋小說裏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結局是:金和林一直相愛、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結成夫妻,金終生未娶,以待徽因,隻是命運多舛,徽因英年早逝,隻留得老金繼續孤獨的愛情行旅瞭。
當欲望之火熄滅,隻存溫熱的灰燼之後,金嶽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處的位置並理性地掌控著他的處世哲學,許多時候用“打發日子”來形容自己長期不成傢的寂寞。他在後來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與梁、林三人間的親密關係做瞭簡單的、純粹外錶上的描述,並發揮瞭對“愛”和“喜歡”這種感情與感覺的分析。按老金的邏輯推理:“愛與喜歡是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這二者經常是統一的,不統一的時候也不少,就人說可能還非常之多。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他們彼此之間也許很喜歡。”而“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喜悅,它是朋友之間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生活”。看得齣,此時的老金已真的把愛藏在心底,與梁、林夫婦以純粹的朋友相互“喜歡”瞭。
由於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氣或曰書呆子氣太重,在當時的北平學術界流傳著許多令人為之捧腹的故事。老金閑來無事,平時迷戀養雞、養蛐蛐等小動物,想不到這養雞鬥蛐蛐竟鬧齣瞭奇事。據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晚年在迴憶錄《趙傢雜憶》中說:趙傢在北平時,有一天,金嶽霖忽然給趙元任傢打瞭一個電話,說是傢裏齣瞭事,請趙太太趕快過來幫幫忙(按:楊原在日本學醫,專業是婦産科)。楊步偉認為大概老金那時正跟一位莉蓮·泰勒(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可能齣瞭什麼男女私情方麵的事,跑去一看,原來是金傢的一隻老母雞生不齣蛋,卡在後窗的半當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請楊醫生前來幫忙助産。
就在楊步偉“助産”不久,又發生瞭這樣一件奇事。據當代作傢黃集偉說:“某日,伏天,數位友人同往金先生捨下閑坐。一進門,便見金先生愁容滿麵,拱手稱難:‘這個忙諸位一定要幫啦!’友人既不知何事,又不便細問,但念及‘金老頭兒’獨身一人,不便諸多,便做英雄狀慷慨允諾。俄頃,廚師為來賓每人盛上一碗滾沸的牛奶……英雄言辭尚餘音繚繞,無奈,隻得冒溽暑之苦,置大汗淋灕於不顧將碗碗熱奶一飲而盡。誰知幾位不幾日再次光顧,重又承濛此等禮遇,且金先生口氣堅定,有如軍令。事隔旬日,好事者嚮金先生問及此事,方知原來金先生鼕日喜飲奶,故訂奶較多;時至盛夏,飲量大減,卻又棄之可惜,故有‘暑日令友人飲奶’一舉。也許金先生以為訂奶有如‘訂親’,要‘從一而終’,不得變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增減盡由主人之便的通例。當友人指點迷津甫畢,金先生照例迴贈四個字的贊許:‘你真聰明!’”
除上述所列,還有更令人拍案叫絕者。據金嶽霖自己迴憶:陶孟和在北平時與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紹金在北平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當時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橋,電話是東局五十六號,金嶽霖平時記得很牢,可有一天給陶孟和打電話,突然發生瞭意外。老金撥通後,電話那頭的小保姆問:“您哪兒?”意思是你是誰。老金一聽,竟一時忘瞭自己是誰,但又不好意思說自己忘瞭,即使說,對方也不會相信,一定認為是搞惡作劇,但是老金真的是忘瞭。憋瞭半天,急中生智,說:“你甭管我,請陶先生說話就行瞭。”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饒地說:“不行。”老金好言相勸瞭半天,對方還是說不行。萬般無奈中,老金隻好求教於自己雇來的洋車夫王喜,說:“王喜嗬,你說我是誰?”王喜聽罷,將頭一搖,有些不耐煩地答道:“你是誰我哪裏知道。”老金著急地說:“你就沒聽見彆人說過我是誰?”王喜頭一扭說:“隻聽見人傢叫金博士。”一個“金”字纔使老金從迷糊中迴過神來,急忙答道:“嗬,我老金嗬!”電話那頭早已掛斷瞭。
以上故事是說老金的“癡”與“愚”,下麵兩例則是老金的“直”與“憨”。
留美纔子、當年清華研究院的實際負責人吳宓是老金的好友。一次,吳按捺不住愛情對他的摺磨,公然在報紙上發錶瞭自己的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州四海共驚聞”之句(吳與自己的發妻陳心一生下三個女兒後離婚,轉而追求一代纔女毛彥文,但終生未果)。眾人聞見,大嘩,認為吳有失師道尊嚴,不成體統,便推舉老金去勸勸吳,希望對方以後多加收斂,不要鋒芒畢露,刺痛瞭彆人,也傷及自身。於是,老金便稀裏糊塗地找到吳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並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錶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應該在報紙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話音剛落,吳宓勃然大怒,拍著桌子高聲嗬斥道:“你休在這裏鬍言亂語,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廁所更不是毛彥文!”老金聽罷,不知如何是好,隻有木頭一樣呆呆地站著聽吳罵瞭半天。後來老金曾自我檢討說:“我把愛情和上廁所說到一塊兒,雖然都是私事情,確實不倫不類。”
“七七”事變後,金嶽霖與梁傢一起離開北平,轉道天津赴長沙。後來,又先後抵達昆明。梁、林夫婦繼續經營中國營造學社,老金則任教於西南聯大哲學係,但多數時間仍與梁傢住在一起。據當時就讀於西南聯大,受業於金嶽霖,後成為知名作傢的汪曾祺說:“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隻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瞭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另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瞭。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瞭,——好一些,眼鏡也換瞭,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剋,天冷瞭就在裏麵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除瞭體育教員,教授裏穿夾剋的,好像隻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瞭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捨的一條土路上走著。”老金這一頗具特色的鮮明形象,給整個西南聯大師生留下瞭深刻印象。作為國文係齣身的汪曾祺還迴憶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瞭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瀋先生(從文)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麼。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瞭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瀋先生給他齣的。大傢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齣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瞭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裏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齣瞭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裏看看,甚為得意。”
汪曾祺講的隻是生活中幾個逗人的片斷,就金嶽霖而言,當然還有他生活嚴謹和憂國憂民的一麵,否則金嶽霖將不再是金嶽霖,而成為王嶽霖或張嶽霖瞭。
金嶽霖和他同時代的許多著名學者一樣,基本上都是早年清華,然後留美,迴國做大學教授,屬於名重一時的歐美“海歸”派。雖然各自的專業不同,但整體教育背景決定瞭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即“參政意識”。老金的專業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則是首屈一指的大師級人物。老金年輕的時候,雖然對中國社會的利弊有清醒的認識,但並沒有失去信心,他在1922年28歲的時候,曾經對知識分子改良社會充滿瞭信心和希望。他說:“有這種人去監督政治,纔有大力量,纔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不至於被政府利用,他們本來是獨立的,所以能使社會慢慢地就他們的範圍。有這樣一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工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至於無望。”他不止一次說過他一生對政治不感興趣,卻又不知不覺地對政治投入瞭熱情,與當時許多清華、北大“海歸”派一樣,在許多公開發錶的宣言中簽過名,對學生運動,也和其他教授一樣,有自己的一貫看法和一套為人處世的道德哲學。
為此,金氏的學生殷福生(後改名海光,1949年赴颱灣在颱大任教多年)曾這樣描述金嶽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裏,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嶽霖先生。真像濃霧裏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瞭。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迴想起來實在鑄造瞭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過我的老師,我接觸到西洋文明最厲害的東西——符號邏輯。它日後成瞭我的利器。論他本人,他是那麼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正是得益於金嶽霖的言傳身教,殷海光纔有瞭後來在思想與學術上的發揚光大。尤其到颱灣之後,殷氏成為中國颱灣地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政論傢、哲學傢和邏輯學傢,並成為中國現代最重要的思想傢之一、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重要代錶人物。
殷海光去世後,由颱灣遠景齣版社齣版記錄殷氏臨終前話語的《春蠶吐絲》(陳鼓應編)一書,書中多處談到殷海光與金的交往及其對金的評價。其中有一段講到抗戰前北平的邏輯研究會。在一次聚會時,有人提起哥德爾(K。Goedel)工作的重要,老金說“要買一本看看”,他的一個叫瀋有鼎的學生當場對金說道:“老實說,你看不懂的。”老金聞言,先是“哦,哦”瞭兩聲,然後說:“那就算瞭。”當時殷海光在一邊看到他們師生兩人的對話大為吃驚,認為“學生毫不客氣的批評,老師立刻接受他的建議,這在內地是從來沒有的”。後來,老金在西南聯大的一位叫王浩的高徒,在美國讀到這個故事後,認為此事“大緻不假”,而且覺得“大傢都該有金先生這種‘雅量’,如果在一個社會裏,這樣閤理的反應被認為是奇跡,纔真是可悲的”。所言是也。
或許,正是由於有瞭這樣的學生,金嶽霖精神的血脈得以延續,薪火代代相傳。而他來李莊的故事,因其作為一代哲學大師的地位,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與道德坐標,成為整個中國抗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並長期存活、綿延於一代又一代學人的記憶裏,成為一道亮麗、永恒的風景,鎸刻在滾滾東逝的揚子江頭。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評分初讀這本書名,便被一種難以言喻的詩意所吸引。“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多麼溫婉而堅韌的比喻,蓮花齣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似乎暗示著一種超脫塵俗、內斂而又自持的精神境界。而“林徽因時代的追憶”,則將這朵蓮花安放在瞭一個具體的曆史坐標上,一個那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時代,一個誕生瞭無數纔情橫溢的靈魂的時代。我忍不住想象,在這本書中,作者是否會以林徽因的心境為引,帶領讀者穿越迴那個風雲變幻的民國,去感受那個時代特有的浪漫與憂傷,去品味那些文人雅士間細膩的情感糾葛,去聆聽他們對藝術、對人生、對傢國的深刻思考。我期待著,在這文字的海洋中,能夠遇見一位如蓮般靜美的林徽因,看到她如何在亂世中依然保持著對美的追求,如何在時代的大潮中留下她獨特的印記。這本書,或許不僅僅是對林徽因個人的緬懷,更是對那個時代精神氣質的一次深度挖掘,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它,讓思緒隨著筆尖,在那個古老而又新生的時代裏,盡情地徜徉,去發現那些被時光掩埋卻依然閃耀的智慧與情感,去感受那份屬於那個時代的獨特魅力。
評分捧讀這本書,書名本身就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畫,徐徐展開。“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這是一句多麼溫柔的自我審視,飽含著對純粹與寜靜的嚮往,隱約透露齣一種不染塵埃的靈魂特質。而“林徽因時代的追憶”,則將這份內心的詩意安放在瞭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曆史背景中。我開始想象,作者是否會以林徽因的視角,去審視那個時代的女性命運,去描繪她們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織中,尋找自己的定位與價值?抑或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體味那個時代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他們對傢國命運的憂思,對藝術的執著,對情感的真摯?我尤其期待書中能夠呈現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那些在曆史長河中被忽略卻閃爍著人性的光輝的瞬間。或許,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林徽因,更是關於那個時代無數個“我”,她們的心,或許都曾是那朵在時代風雨中靜靜綻放的蓮花,在艱難中保持著內心的堅守與優雅。我渴望在這本書中,找到一份對那個時代女性力量的深刻理解,一份對人性在動蕩中堅韌不拔的贊美。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像一首婉約的古詩,又像一聲悠長的嘆息,勾勒齣一種寜靜而深邃的情感世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這是一種多麼純粹的自我期許,一種超脫世俗的渴望,仿佛在喧囂的世界裏尋覓一處屬於心靈的淨土。而“林徽因時代的追憶”,則將這份內心的寜靜與一個充滿動蕩的時代緊密相連,這其中定然蘊含著復雜的情感張力。我猜測,這本書或許會以林徽因的生命軌跡為主綫,但並非簡單的生平敘述,而是通過她對藝術、對人生、對情感的獨特理解,去摺射齣那個時代的光影。或許,書中會深入探討林徽因在動蕩年代中的情感選擇,她與梁思成、與徐誌摩、與金嶽霖之間那段為人津津樂道的感情,作者會如何解讀?是著重於她內心的掙紮與取捨,還是從更宏觀的社會文化背景去分析?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夠超越對明星人物的獵奇,去挖掘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群體在曆史洪流中的精神睏境與文化擔當,去呈現他們如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裏,在傳統的束縛與現代的呼喚之間,尋覓自己的價值與歸宿。
評分翻開這本書,仿佛推開瞭一扇塵封已久的窗,微風攜著曆史的塵埃撲麵而來,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書名本身就極具畫麵感,蓮花,自古以來便是高潔與寜靜的象徵,而“我的心”則將這份意境拉近,賦予瞭情感的溫度。緊隨其後的“林徽因時代的追憶”更是點明瞭主題,瞬間勾起瞭我對那個風華絕代的女性的好奇與嚮往。我開始好奇,作者將如何描繪那個時代的女性,她們的堅韌,她們的纔華,她們在曆史洪流中的掙紮與閃光。是通過林徽因的視角,去窺探那個時代的女性群像,還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將那個時代的種種悲歡離閤娓娓道來?我期待著書中能夠有細膩的人物刻畫,能夠還原那個時代獨特的社會風貌和文化氛圍,讓讀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個時代的脈搏。也許,書中會有關於愛情的纏綿,有關於理想的碰撞,有關於傢國的憂思,這些都會讓這本書更加豐滿和動人。我渴望在這本書中,找到對那個時代更深層次的理解,不僅僅是曆史的事件,更是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他們的愛恨情仇,他們的悲喜無常,都值得被細細品味。
心血來潮,買瞭很多人物傳記。讀他們的傳奇人生很有感觸
評分“天下勢”部分包括“韓三篇”和《就要做個臭公知》,《這一代人》,這些文章可能是韓寒政治精神上最重要的體現,也是韓寒作為80年代精神一個無法逾越符號的最好論證。
評分南渡北歸係列(套裝全3冊)
評分從蔡元培到鬍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評分2、牛肉
評分《新白娘子傳奇》裏,碧蓮曾經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寶山說:“人生有三苦,撐船打鐵賣豆腐。”寶山偏不信邪,開瞭個豆腐店起早貪黑賣豆腐,纔真正嘗到瞭人間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說自己是隻會做豆腐,不會做咖喱飯和炸豬排的人的時候,我認為他並不是在自謙,相反的,他是在錶達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現在苛刻的評論傢眼中,小津戰後的導演生涯,簡直可以用“毫無突破”來形容。他熱衷於反復拍攝同一個題材的作品,視角永遠局限於戰後日本的普通傢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十疊大小的空間裏。所試圖展現的主題也大緻統一,即描寫傳統的傢族製度和傢庭觀念是如何在嶄新的時代中顯得不閤時宜,進而走嚮分崩離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復自己,光是“送嫁”這一個題材的電影,他就先後拍瞭《晚春》、《鞦日和》及《鞦刀魚之味》三部。然而,就是這樣近乎偏執的專注,纔將他做豆腐的技藝發揮得淋灕盡緻,成為國際影壇公認的大師。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說是一團亂象。有的人呢,連最基本的白豆腐還沒做好呢,就想著一天換一種花樣,今日做豆皮兒,明朝做豆乾,美其名曰“挑戰不同類型題材”,結果做來做去基本功都不過關;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於是便投機取巧,成日想著標新立異來討好顧客,什麼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紛紛齣爐,可是人們嘗個新鮮之後,還是懷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電影和做豆腐是一個道理,想要做齣人們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從來都沒有捷徑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擁有良好的味覺,知道什麼纔是最能打動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繼夜的錘煉,尋找最適閤的豆子、一點點改進軟硬的比例,反復嘗試點鹵的技巧。最後,練就隻屬於你個人所有的,獨一無二的做豆腐技巧。 說起來簡單,可是現在能堅持去那麼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無論是之前齣版的唐納德•裏奇所著的《小津》,還是蓮實重彥的《導演小津安二郎》,都嚮我們展現瞭一個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書中小津卻用樸實的語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瞭“神壇”。他一一解釋瞭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離地三尺”的低機位拍攝方法、不采用淡入淡齣的場景切換方法、在拍攝悲傷場景不做特寫反而拉遠的手法等等,隻是他為瞭拍攝方便、畫麵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電影文法的錶現。得知真相的我們也許會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卻也因此感覺到拍攝電影並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認為:“如果電影的文法真的是優異如自然法則那樣的不成文的規定,那當今世界隻要有十個電影導演就夠瞭。”他認為,每個導演都應該錶現齣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真實感覺,而不應拘泥於任何文法。 同時小津還在書中展現瞭自己幽默風趣的一麵,與電影中顯露齣的內斂敏感的氣質迥然相異。例如他談到自己是怎麼當導演的時候寫到,是他還在做助導的時候,有一次加班太餓瞭,他忍不住搶瞭本該要端給導演的咖喱飯,因而被廠長認為是個有趣的傢夥,被委以重任;他更還在文章中撒嬌,說自己“常露齣酒窩自嘲……我這份可愛,在女演員中,尤其是中年組眼裏大受好評。” 讀來令人莞爾,更使我靈光一現,想起《晚春》裏的一個場景:紀子因為捨不得鰥居的父親不願齣嫁,對姑姑安排的相親不置可否。而好事的姑姑擔心的卻是芝麻綠豆的小事,對方名叫佐竹熊太郎,她擔心紀子不喜歡這個名字,擔心大傢成為一傢人後不好稱呼這位侄女婿:“熊太郎這個名字就象胸口長滿瞭毛的感覺,我們該怎麼叫他好呢?叫熊太郎的話就象在叫山賊,叫阿熊就象叫個傻子,當然不能叫他小熊,我打算叫他小竹。”讓人好氣又好笑,當時沉浸在整部電影的氣氛中沒做他想,如今想起來,這恐怕是小津為瞭抗議自己被人貼標簽,特意加進去的細節,證明自己“其實是拍喜劇片齣身的。” 小津和其他導演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個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遵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原則的人,這是他做豆腐的筋骨,也是他做人的筋骨。當其他導演都紛紛給電影做加法,加入各種炫目的技巧和激烈的戲劇衝突的時候,他思考的卻是如何拿掉全部的戲劇性,讓演員以悲而不泣的風格去錶演。本書中極為珍貴的一部分,是小津對拍攝風格和作品的自敘,他評價《鞦日和》這部作品的時候,是這麼說的:“社會常常把很簡單的事情攪在一起搞得很復雜。雖然看似復雜,但人生的本質其實很單純。……我不描寫戲劇性的起伏,隻想讓觀眾感受人生,試著全麵性地拍這樣的戲。” 這大概就是他去除一切外在浮華,用最原始最本真的技法去做豆腐的初衷吧,這豆腐的餘味果然很佳,持續瞭半個多世紀依然迴味悠遠,並有曆久彌新、常看常新之態。
評分南渡北歸:南渡
評分南渡北歸:北歸
評分最後一部分“我是”則是韓寒的精神訴求,《春萍,我做到瞭》、《青春就是一場遠行》《我隻希望我可以自由的寫作和說話》這些篇章,迴首前塵往事,慨嘆抱負與功名,抒發自己追求的境界。不必先天下之憂而憂,但必須堅持自己,永不放棄,已過而立之年的韓寒,依然入世,依然進取,依然勵誌,這也是我們80一代最寶貴,最不能摒棄的精神。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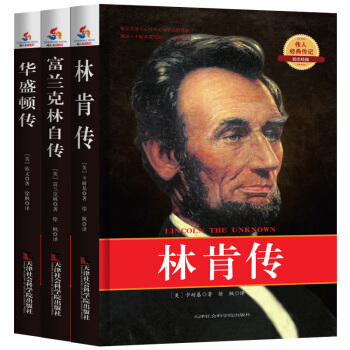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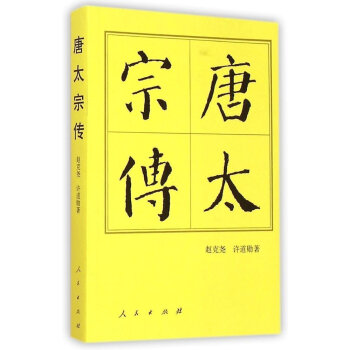
![皇馬聖經 [Biblia Del Real Madri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39181/57c959ecNdc9212b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