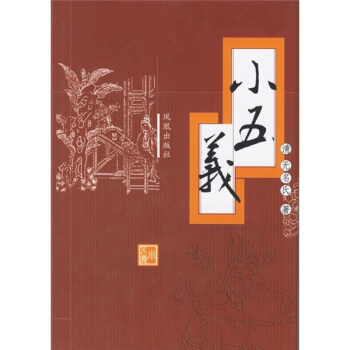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凯里生于墨尔本市郊小镇,父亲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推销员。凯里曾就读于蒙纳什大学,学习有机化学,后因一场交通事故,未及毕业便去从事广告设计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作家巴利·奥克利和莫里斯·卢里,开始接受文学创作的熏陶,阅读了贝内特、贝娄、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和福克纳等人的实验性作品。一九六_匕年,带着对国内环境的失望和对明友奔赴越南战场的忧伤,凯里离开澳大利亚来到欧洲,寄希望于得到欧洲文化的滋润。在欧洲,他周游各国,不断积累素材,但大部分时间仍侨居伦敦,靠写广告谋生。闲暇之余,精心创作,小说《寄生虫》(Wog)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但因该小说大胆前卫,出版社拒绝出版。作者简介
彼得·凯里(PeterCarey),1943年生于墨尔本市郊小镇,曾在大学学习化学,未及毕业改做广告设计,后游历欧洲并转向文学创作,现居住在纽约。凯里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领军人物,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是世界惟一的两位二度荣获布克奖的作家之一,另一位则是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因此有评论家预言,凯里将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
凯里的作品怪诞、幽默,具有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特征。
因书写《凯利帮真史》等历史题材的小说而被誉为澳大利亚"民族神话创造者"的凯里,是一位关注现代人生存困境、具有国际色彩的作家。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乍看上去小说描写的是爱情故事,是悲剧,是喜剧,是悲喜剧,还有一位艺术家身心的征程……从更深一层来看,小说的成功在于描述了人之个体所体验到的那种与世隔绝的深重的孤独,那种属于个体主观感受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不可确知性……”——《哈佛书评》
“凯里绝对是讲故事的高手,惟妙惟肖;这就或许可以理解为何读者难以将他和大师们区分开:他更像狄更斯?还是乔伊斯?还是卡夫卡?还是福克纳?还是纳博科夫?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拉什遮?”
——《伦敦书评》
“凯里的永不停歇令人叹服。他反叛,成长,再反叛……在这部小说中,决不同流合污、誓死捍卫人格独立的精神得以深刻地展现。《偷窃》可谓一部彻头彻尾的非爱情小说,凯里对结尾的处理绝妙无比。”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精彩书摘
1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庄重得可以被称做悲剧,虽然其中的确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不过这要在那悲惨的事情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才开始,那时候我不仅失去了我八岁的儿子,还失去了我在悉尼的房子和画室,在悉尼的时候,我的知名度曾经几乎达到了一个画家在他自家的后院所能指望达到的最高程度。那一年我本该获得澳大利亚勋章——为什么不呢!——看看他们都给了谁呀。可结果我的孩子却被从我身边偷走了,我被离婚律师搞得大伤元气,并且因为企图弄回我最好的作品而锒铛入狱,因为那幅作品被宣布为夫妻共同财产。
一九八○年萧瑟的春天,我从长湾监狱出来,听说立刻就将被放逐到北方的新南威尔士去,在那里,虽然我几乎没什么钱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但是据说只要我少喝点酒,就可以有钱来画一点小作品和照顾我那病态的二百二十磅的弟弟休。
我的律师们,顾主们,收藏者们都来救我。他们非常善良,慷慨。我很难承认我他妈的讨厌照顾休,我不愿意离开悉尼或少喝点酒。我没有勇气实话实说,只好踏上他们为我选好的路。在悉尼以北两百英里的塔里,我开始往一个汽车旅馆的脸盆里吐血。谢天谢地,我想到,现在他们无法把我送走了。
但我只不过是患上了肺炎,毕竟没有死掉。
是我最大的收藏者,让一保罗?米兰,制订了这个计划,让我在他的一个大农场里担任不收费的护工,他早在一年半之前就想把那个农场卖掉了。让一保罗是一家连锁私人疗养院的老板,后来疗养院改由卫生委员会投资,但他还喜欢画画,他的建筑师给他建造了一间画室,朝河边的墙上开了一扇门,好像车库的卷帘门。那里的自然光,正如他在把画室当礼物送我的时候那么亲切地提醒我的那样,也许带点绿色,那是河边的古木麻黄造成的“错误”。我原本应该告诉他,关于这个自然光的事情完全是扯淡,但我又一次闭紧了嘴巴。出狱的第一个晚上,我跟让一保罗和他的妻子一起吃晚饭,那是一顿蹩脚的没有酒的晚饭,当时我同意道,我们悲剧性地把背转向了自然光,烛光,星光,的确,在烛光里欣赏歌舞伎更精彩,借助从一扇灰蒙蒙的窗子渗进来的光欣赏马奈的画最完美。但是,去他妈的吧——我的作品会在画廊里生存或死亡,我需要靠得住的240伏交流电画我自己的画。我现在注定要生活在一个肯定没有这种东西的“天堂”里。
让一保罗如此大方地把他的屋子给了我们,可他马上就犯起愁来,怕我会损坏它。或也许真正杞忧的人是他的妻子,她早就抓住过我用她的餐巾擦鼻涕。不管怎么说,我们住进贝林根才六天之后的那个早晨,让一保罗就冲进屋子,叫醒了我。这着实把我吓得不轻,但我闭紧了嘴巴,给他煮了咖啡。随后的两个小时里,我像他的一条狗似的跟着他在农场里转,把他吩咐我的每一件无聊的事情记在我的笔记本上,这是一个皮面本子,对我来说就像命一样珍贵。这个本子里记下了我自从一九七一年那次所谓的突破性画展以来,我的每一次调色经历。这是一座宝库,一本日记,一个每况愈下的记录,一部历史。大鳍蓟,让一保罗说,我就在我可爱的本子上记下“大鳍蓟”。刈草。我拼写了出来。倒在河面上的树。斯蒂尔链锯。断木机沾了油污的螺纹接套。这时屋子下方停着的一辆拖拉机惹恼了他。木料堆堆得不整齐——我让休按着让一保罗喜欢的样子把它堆放整齐。最后我的东家和我一起来到了画室。他脱掉鞋子,好像要做祷告似的。我也学他的样。他抬起面朝河边的硕大的卷帘门,站了很久,俯视着奈佛奈佛河,说着——这可不是捏造的——关于莫奈那操蛋的《睡莲》。他的脚非常漂亮,我以前就注意过,又自足弓又高。他已经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可是脚趾直得像个幼儿。
虽然开着二十多家养老院,让一保罗本身并不是个轻易流露感情的人,但是此刻在画室里,他一把抓着我的前臂。
“你在这里会开心的,布彻。”
“是。”
他环视着又高又长的画室,然后迈开那双富有的、完美的脚,轻快地走过柔软的地板表面。要不是他的眼睛过于湿润,他看上去真像个准备参加科幻小说中的田径比赛的运动员。
“角瓣木,”他说,“是不是很好啊?”
他说的是地板,的确很可爱,一种被冲蚀的浮石的灰色。那还是一种罕见的雨林木材,但是,我一个被判刑的罪犯,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呀?
“我真羡慕你,”他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是说,我像条又老又大的纽芬兰拾猿那样驯服,我本可以求他给我画布,他会给我的,但是他会跟我要一幅画。就是那幅画,我不愿给他的那幅,我现在正想着的那幅。他不知道,我还保存着大约十二码的棉帆布,在我被迫使用梅森耐特纤维板之前,那可以画两幅好画。我悄悄地吮吸着他当做礼物拿给我的不含酒精的啤酒。
“挺好的吧?”
“像真的一样。”
然后,终于,最后的指令颁布了,该许诺的也都许诺了。我站在画室下面,看着他开着租来的汽车蹦跳着驶过拦畜沟栅。驶到最低点后,就到了柏油路上,然后就驶走了。
十五分钟后,我到了一个叫贝林根的村子,向乳牛场主合作商店的人们做了自我介绍。我买了一些胶合板,一把锤子,一把木工锯,两磅两英寸的石膏板螺丝,二十只150瓦的白炽灯灯泡,五加仑的多乐士深黑漆,以及同样分量的白漆,所有这些,加上其他一些零碎东西,我都计在了让一保罗的账上。然后我回家去布置画室。
稍后,几乎每个人都会大声嚷嚷,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在用石膏板螺丝糟蹋角瓣木,但我看不出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把胶合板复到角瓣木上。当然啦,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要在那里画画,一个画家的匦室的地板应该像一个献祭场,被u型钉刺破,但每次仪式过后,都要加以呵护,清扫,擦洗,冲刷干净。我把便宜的灰油地毡复在胶合板上面,涂上亚麻籽油,直到它散发出宛如一幅新出炉的《圣母哀子图》的异味。但是我仍然无法开始画画。现在还不行。
让一保罗的那位得奖的建筑师设计了一个高拱顶的画室,他用钢缆把拱顶绷紧,就像弓上的弦一样。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惊叹的事情,我把一排排的白炽灯从钢缆上吊下来,这一来既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他设计上的典雅,又抵消了透过木麻黄渗进来的绿光。即便有了这些改进,也很难想像有比这里更糟的做画的地方。臭虫多得不得了,小虫子盯着我的多乐士油漆,用同心圆表明它们临死前的痛苦。当然啦,那扇又大又宽的门对那些讨厌的小东西是一种公开的诱惑。我回到合作商店,签收了三只蓝光灭虫灯,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我四周尽是热带雨林,无数的树木和尚未命名的虫子,除了我来命名——你这讨厌鬼,你这小坏蛋——肆意破坏我来之不易的工作。为了防御,我只好拉起难看的防蝇电网,但是空间不够宽阔,绝望之中,我赊账定做了一块绸帘子——两边钉上维可牢,底部装上挡风沙袋。帘子是深蓝色的,沙袋是铁锈色。这下子那些破坏者掉进帘子汗津津的叉柱后就死在了那里,每晚都要死好几千个。每天早晨我扫地时,都要把它们扫掉,但我也会救下一些来做我的活模特,没别的原因,就因为画画是一种放松,我常常会——尤其是没酒喝的时候——坐在餐桌前,用灰色笔缓慢而仔细地在我的笔记本里画出它们可爱的尸体。有时候我的邻居多齐?博伊兰会替我给它们命名。
十二月初,我弟弟休和我被当做护工安置下来,到了盛夏,当我的生命开始又一个有趣的篇章时,我们还在那里。闪电击中了贝林根公路上的变压器,因此,我们又一次没有很好的灯光来干活,为了报答东家的好心,我美化了前围场,用鹰嘴锄锄掉了“待售”招牌四周的大鳍蓟。
在新南威尔士北部,一月是最热的,也是最潮湿的。连着下了三天雨后,围场都湿透了,我挥动着鹰嘴锄,只觉得脚趾间的泥土都热得像屎一样。在这一天之前,溪水一直像杜松子酒一样清澈,那是一条深不过两英尺的小溪,溪里多的是岩石,但现在,湿透的土地造成的溢流把这条原本平静的小溪变成了一头略显肿大的野兽:黄色,汹涌,地盘性的,迅速涨到二十英尺,吞没着后围场宽阔的洪泛区,吮吸着溪岸的顶部,高雅的画室就蹲伏在——显著地但并非无懈可击地——岸边高高的木柱子上。这里高出地面十英尺,人们可以在凶猛的河流边缘的上方行走,就像在码头上行走一样。让一保罗在向我介绍他的屋子时,曾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平台命名为“石龙子”,指的是那些澳大利亚的小蜥蜴,每当灾难来临时,就把尾巴甩掉。我纳闷的是,他有没有注意到这整座屋子都是建筑在洪泛区上的。
我们没有被放逐多久,也就是六个星期左右吧,我记得那个日子,是因为那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次潮水,也就在那天,休从邻居家回来时大衣里面藏着条昆士兰小花狗。照顾休本人就够难的了,现在又加上这么个额外的负担,倒不是说他老是惹麻烦。有时候他非常精明,说起话来有条有理,而有时候,他呜呜咽咽,叽里呱啦,不知所云,像个傻瓜。有时候他崇拜我,大声地,充满激情地,像个长胡子的、有口臭的孩子。但相隔一天,或一分钟,我就会变成反对党领袖,他会埋伏在野马缨丹里,扑向我,在泥浆里,或河里跟我死劲扭打,或把我拽过潮湿的季节里到处都是的绿皮密生西葫芦丛。我不需要一条可爱的小狗。我有了诗人休和谋杀者休,低能特才者休,他变得更重更壮,一旦把我摔倒在地,我就扭他的小手指,好像要把它拗断,这样才能制服他。我们俩都不需要一条小狗。
我割断了或许有上百条大鳍蓟的根,劈开了一棵小桉树,生起炉子,给日本式浴缸烧热水,这时发现休睡着了,而小狗不见了,我退出屋子,回到了石龙子上,看着河水的颜色,听着奈佛奈佛河淤青、肿胀的皮肤下面砾石相互碰撞的声音。我特别注意到邻居家的鸭子在黄色的洪水里上下起伏,而我感觉到平台摇摇晃晃,像三十节风速下绷紧的桅杆。
小狗在某个地方吠叫。它肯定受到了鸭子的过度刺激,也许以为它自己就是鸭子呢——现在我想起来,挺像那么回事。雨势一刻也没减弱过,我的短衬裤和T恤都湿透了,我突然想到,要是把衣服脱了,会感觉舒服很多的。于是我就待在那里,难得地对小狗的吠叫充耳不闻,像个嬉皮士似的赤裸着身子蹲在汹涌的洪水上面,一个屠夫,一个屠夫的儿子,惊讶地发现自己距离悉尼三百英里远,在雨中居然意想不到地快乐,要是我看上去像个膀大腰圆、毛茸茸的毛鼻袋熊,那倒也无妨。这并不是因为我处在狂喜的状态中,但我,至少在一时间,摆脱了我一贯的激动,对我儿子的伤感记忆,因为不得不使用操蛋的多乐士而生气。我非常接近,几乎,在六十秒钟里,感到平静,但随后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我常常感到其中的第一件是一种预兆,我最好多加留意。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是那条小狗,被黄色的洪水快速地冲走。
后来,在纽约,我会看见一个人在百老汇慢车站前面跳跃。他一会儿还在那里,一会儿就不见了。我无法相信我所看见的。说到那条狗,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根本不是同情那么简单。当然不能轻信。轻松——没有狗需要照料。生气——我竟然要对付休的不相称的悲痛。
我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打算,只是艰难地开始往身上套湿衣服,于是,无意间,在画室下面,通过我的大门,在拦畜沟栅过去二十码处,我清晰地看见了第二样东西:一辆黑色的汽车陷在了泥浆里,直陷到车轴那儿,车头灯亮得晃眼。
我没有正当的理由为潜在的买主生气,只不过这时间太糟,还有,操蛋,我不喜欢他们老是操心我的事情,假装评价我的画或我的家务。但是我,前著名画家,现在只是个护工,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穿上冰冷的、不舒服的衣服,慢慢地走过泥浆地,来到棚子前,发动起拖拉机。那是一台菲亚特,虽然它那喧闹的分速器箱快速损害了我的听觉,我还是对这个黄色的家伙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感情。我骑在它高高的背上,像堂吉诃德似的怪模怪样,朝我那位汽车陷在泥浆里的访客驶去。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三千英尺的多里戈悬崖高高耸立在汽车之上,迷雾从年代久远、未被采伐的灌木丛中升起,新生的云高高在上,驾着强势的热气流飘浮,那气流任何滑翔机驾驶员都会从心里感受到,但此刻群山被遮住了,我只能看见我那一排栅栏,和咄咄逼人的车头灯光。福特车的车窗上布满雾气,所以即便在十码之内,我也只看见后视镜上阿维斯的标志轮廓,汽车里面什么都看不见。这足以证实来人是个买主,我做好了以低声下气面对骄横无礼的准备。然而,我却有一种被激怒的倾向,但当我发现没有人从车里出来招呼我时,我开始纳闷,哪个悉尼来的操蛋以为他可以挡在我清晰可辨的车道上,然后等着我去伺候他。我从拖拉机上下来,砰的一拳打在车顶上。
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里,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引擎发动起来,布满雾气的车窗摇了下去,露出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一头浅黄色的头发。
“你是博伊兰先生吗?”她的口音很奇怪。
“不是,”我说。她有一双淡黄褐色的眼睛,嘴唇对她那张纤细的脸来说几乎显得过大。她的样子不同一般,但是很有吸引力,所以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以我这种多舛的命运以及几乎一以贯之的喜欢女色——她居然那么严重、那么深刻地激怒了我。
她看着窗外,打量着前后的轮子,那些轮子一直深陷在我的地界里空转着。
“我这身打扮可不方便下车,”她说。
要是她跟我道歉,我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可她却径直把窗子摇了上去,在另一边朝我发号施令。
不错,我曾经是个名人,而现在只是个勤杂工,所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把菲亚特牵引缆索空的一头系在福特的后轴上,这一来溅了我一身的泥浆,也许还有点牛屎。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拖拉机上,挂上低速挡,踩下油门。她当然没有让汽车熄火,所以我这一踩下去,就见两股长长的气体穿过青草,窜到了公路上。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说再见。我把缆索从福特上收回来,把拖拉机驶回车棚,没有回头看一眼。
我回到画室时,却发现她根本就没离开,而是提着高跟鞋,正穿过围场朝我的屋子走来。
正常情况下,这时候我得画画,我的访客过来时,我在削铅笔。河水的咆哮像血脉在我耳鼓里奔涌一样,但是当她踏上硬木楼梯时,我能感受她的脚步声,那是一种从地板搁栅上一路响过的震颤声。
我听见她的叫唤,但是休和我都没搭理,她就踏上了架在屋子和画室之间的掩蔽廊道,一种离地面十来英尺、有弹性的、摇摇晃晃的小建筑。她也许会选择敲画室的门,但是那里也有一个非常狭窄的通道,一种跳板,环绕着画室的外墙,所以她出现在开着的卷帘门前,站在丝帘子外面,河在她的背后。
前言/序言
彼得·凯里(Peter Carey,1943- )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领军人物,是继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Ftenry Lawson,1867—1922)和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912-1990)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大师,被誉为“澳大利亚最有才华和最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①迄今为止,他出版的十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非小说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屡获国内外文学大奖——两次布克奖,两次英联邦作家奖,三次迈尔克斯·富兰克林奖,是世界上仅有的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而另一位是南非作家库切,几年前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评论家预言,凯里将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凯里生于墨尔本市郊小镇,父亲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推销员。凯里曾就读于蒙纳什大学,学习有机化学,后因一场交通事故,未及毕业便去从事广告设计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作家巴利·奥克利和莫里斯·卢里,开始接受文学创作的熏陶,阅读了贝内特、贝娄、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和福克纳等人的实验性作品。一九六_匕年,带着对国内环境的失望和对明友奔赴越南战场的忧伤,凯里离开澳大利亚来到欧洲,寄希望于得到欧洲文化的滋润。在欧洲,他周游各国,不断积累素材,但大部分时间仍侨居伦敦,靠写广告谋生。闲暇之余,精心创作,小说《寄生虫》(Wog)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但因该小说大胆前卫,出版社拒绝出版。
用户评价
从纯粹的情感共鸣角度来看,这本书在我心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它没有刻意煽情,但那种深沉的情感力量却如同暗流般涌动,在不经意间击溃了读者的心理防线。我常常在阅读时感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仿佛自己被投射到了主人公那无依无靠的境地,体验着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与情感的重负。这种代入感是建立在对人类共同情感体验的深刻理解之上的,作者精准地捕捉到了爱、失落、渴望与自我怀疑这些普世情感中最细微的颤动。读到某些关于“连接”与“疏离”的描写时,我几乎要落泪,不是因为情节的悲惨,而是因为那种精准触及灵魂深处的真实感。这本书教会了我,真正的深刻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对个体痛苦的温柔凝视。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那些不愿面对的脆弱,并以一种近乎治愈的方式,接纳了这份不完美。这是一次充满温度与力量的阅读体验,让人在合上书页后,心中仍旧充盈着一种平静而坚韧的力量。
评分这本书读完后,我感觉脑海中有一片广阔的星空在缓缓展开,每一个情节的转折都像是一颗流星划过,带着不可预知的轨迹和震撼人心的光芒。作者的叙事手法简直是神来之笔,他似乎拥有某种魔力,能将最微小的情感波动放大成史诗般的波澜。我尤其欣赏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那种复杂交织的矛盾,那种在光明与阴影间游走的挣扎,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曾经历过主人公所面对的那些艰难抉择。故事的节奏把握得极其精准,时而如急促的鼓点让人心跳加速,时而又像舒缓的慢板乐章,让人沉浸在对人生意义的深思中。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停下来,抬头望着窗外,试图消化刚刚阅读到的那些令人心神俱震的场景和对话。这不是一本轻松愉快的读物,它更像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逼迫着我们去直面那些平时习惯性回避的道德困境和情感的灰色地带。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抛出更深刻的疑问,让读者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启示录。那种久久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意境,才是真正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标尺。
评分坦白说,我一开始对这本书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毕竟市面上打着“深刻”旗号的作品太多,往往徒有其表。但随着故事的深入,我完全被一种强大的、近乎宿命论的力量所牵引,无法自拔。作者构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每个人物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他们拥有各自无法言说的苦衷和深埋的秘密,他们的每一次互动都充满了试探与博弈,像是在下一盘没有硝烟的棋局。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力,已经超越了普通观察者的层面,更像是一位行走在世间,对灵魂有着深刻理解的哲学家在娓娓道来。我特别佩服作者在关键冲突点上所展现出的叙事勇气,他没有选择回避那些令人不适的真相,而是直面人性中最幽暗、最脆弱的一面,将它们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真诚与无畏,是许多当代小说所缺失的。读完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思绪,因为这本书迫使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对“对错”的界定,它留下的回响,远比故事本身更加持久。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设计堪称鬼斧神工,它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叙事,更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蜘蛛网,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最终都会在后文找到其精妙的落点。作者高超的伏笔运用技巧,让我这个习惯了提前猜测情节的读者也屡屡失算,每一次“原来如此”的恍然后,都伴随着对作者布局能力的赞叹。他巧妙地在时间线上跳跃,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切换,却始终保持着叙事的清晰和逻辑的严谨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成就。我尤其喜欢那些穿插在主线叙事中的零散片段,它们或许是主人公某次偶然的梦境,或许是一段不相干人物的简短对话,但正是这些碎片,共同拼凑出了一个宏大而立体的世界观。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看故事,不如说是在参与一场智力上的解谜游戏,每解开一个谜团,都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对于那些喜欢深度阅读,享受抽丝剥茧过程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无与伦比的礼物。
评分这部作品的文字功底达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简直就是一场文字的盛宴,每一个句子都仿佛经过了无数次打磨和雕琢,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语言的张力非常强悍,作者似乎能驾驭各种文体风格,时而古典优雅,时而又充满现代的犀利和穿透力。我最欣赏的是他对场景描写的独到见解,他笔下的世界,无论是喧嚣的都市一角,还是寂静的内心深处,都拥有了鲜明的立体感和触觉感,仿佛读者真的置身其中,能闻到空气中的气味,感受到光线的温度。更难得的是,这种华丽的辞藻堆砌并没有让故事显得空洞浮夸,反而与深沉的主题完美融合,形成了一种既有美感又具重量的叙事风格。读到某些段落时,我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放慢速度,反复咀嚼那些精妙的词组搭配,试图从中汲取更多的营养。这本书的书页已经被我翻得起了毛边,每一个重要情节的标记都像是心头的一个小小的印记,提醒着我这次阅读旅程的深度与广度。这是一次对语言艺术的极致探索,值得所有热爱文学的人细细品味。
评分感觉书是盗版书,装帧太粗糙了,京东好奇尿不湿是假货!!!假货!!!假!!!
评分推荐大家一起购买的好书!!
评分因书写《凯利帮真史》等历史题材的小说而被誉为澳大利亚"民族神话创造者"的凯里,是一位关注现代人生存困境、具有国际色彩的作家。
评分很不错的商品,非常值得推荐
评分很好,平装版,无塑封,价格实惠,如图所示。
评分好书
评分彼得·凯里(PeterCarey),1943年生于墨尔本市郊小镇,曾在大学学习化学,未及毕业改做广告设计,后游历欧洲并转向文学创作,现居住在纽约。
评分物流是很快,昨天下单,今天上午就收到了,大概翻了一下,感觉不是太理想
评分求很好,以后还来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经典畅销最新全译本)(套装上中下册) [The Complete Herlock Holm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859287/rBEhVVK5GkYIAAAAAAuZL-IeGYsAAHSLwMYhP0AC5lH79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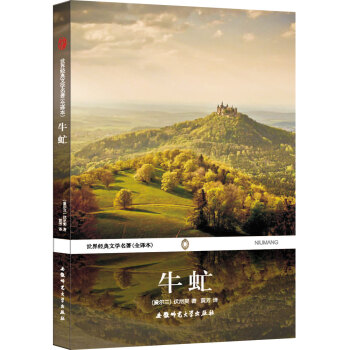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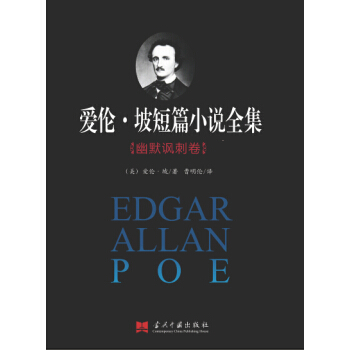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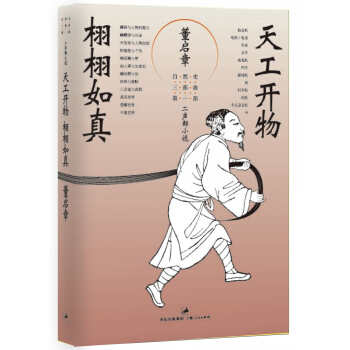




![安部公房作品系列:砂女 [The Woman in the Dun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43199/58eb6014Nef4ee77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