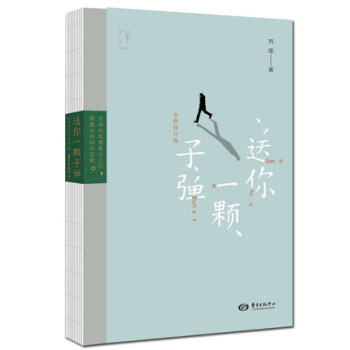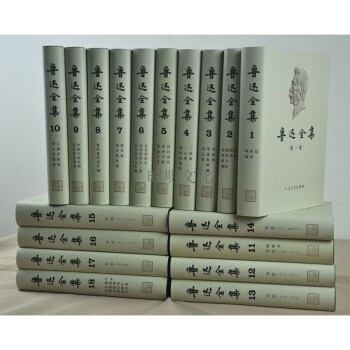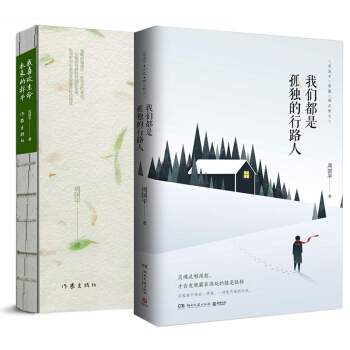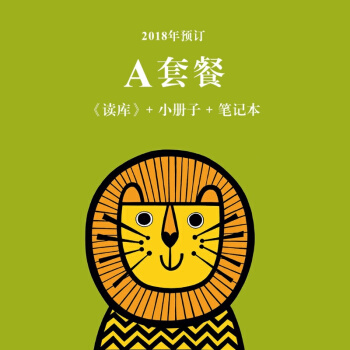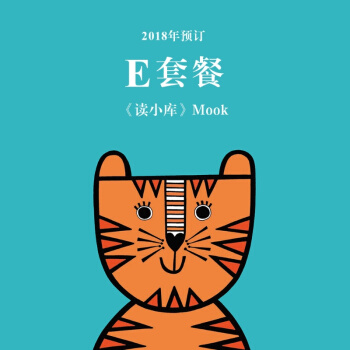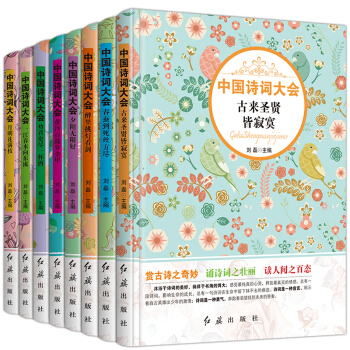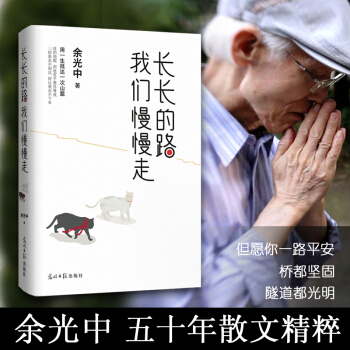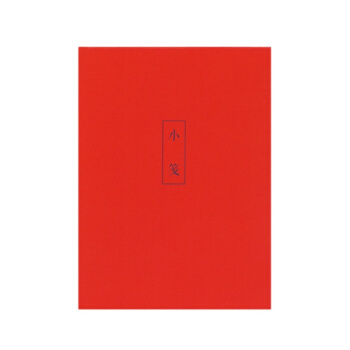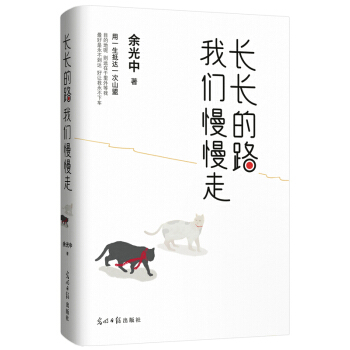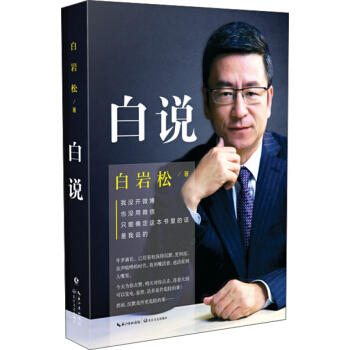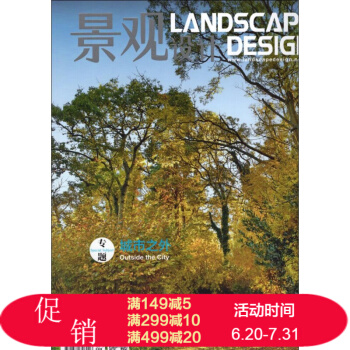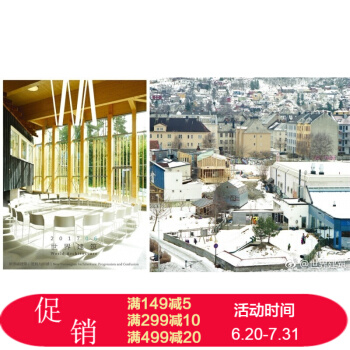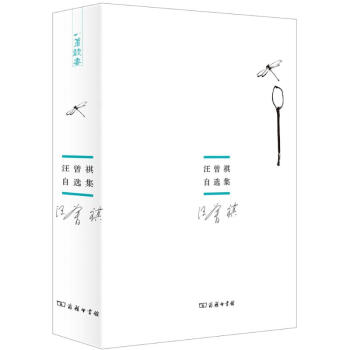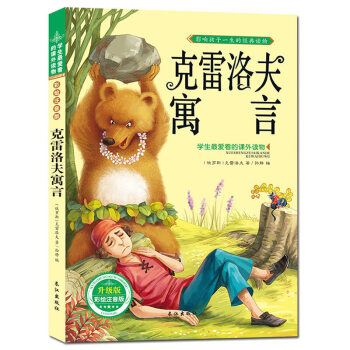具体描述
一本关于中国古典生活、建筑、手艺的沉思录,诗人于坚新力作,追问何为“诗意地栖居”。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2016年度杰出作家”于坚的*新力作。
★阅读此书,可以令你跳脱出千城一面的审美疲劳,学会理解一座古城、一座建筑、一种仪式,如何安放、庇护人类的心灵。
★礼失求诸野,论及古典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原大地、江南水乡早已被现代化尽数侵袭,唯有处于边地的古城建水,才能承托你的梦想和追寻。
★几十年间,诗人不断穿梭在建水的大街小巷,体悟建水的建筑、手艺、生活方式,查询各类古籍,*后熔铸成37篇文章、配以精挑的134张照片,述说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探寻了建水人为何至今仍能“诗意地栖居”。
《建水记》是一本关于古典生活、建筑、手艺的沉思录;也是著名诗人于坚追问何为“诗意地栖居”之作。
2015 年冬天,于坚带着比利时汉学家麦约翰来到建水。麦约翰浸淫中国文化数十载,他在建水长叹,他一辈子要找的那个中国,就在这里。
14世纪晚期, 明朝廷“移中土大姓, 以实云南”。二三十年间,数十万移民背井离乡,迁徙云南。这是一支由生活世界的行家里手、大师组成的队伍,他们从中原、江南带着各类种子、精致的手艺,依照宋元时形成的经典“营造法式”来建筑一个梦想中的天堂。建水城就这样诞生了,彼时的它,名曰“临安”——一个来自天堂的名字。
如今,建水城已经年华老去,与它同时代兴起的古城,大都焕然一新。而它却在20世纪的城市化、大拆迁的洪流中如顽石般幸存,以致今天在中国,人们要证实曾经存在过一个“雕栏玉砌”的诗意世界,找回那些传统的建筑样式、生活方式……只有去建水。建水成了古典生活世界的活化石。
于坚
1970年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至今。
1980年开始摄影至今。
1992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至今。
著有诗集、文集多种。获数十种诗歌奖、散文奖。
长篇散文《印度记》获2012年《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作品奖。
在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荣膺“2016年度杰出作家”。
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
系列摄影作品获201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夏典藏奖。
纪录片《同饮一江水》总撰稿。
*近二十年为《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旅行家》等刊物特约撰稿人。
在国内外多地举办摄影展。
于坚以文会心、为文招魂,写诗、作文、立论,皆自由挥洒,辞直义畅。他居边地数十年,独持己见,一意孤行,如今个人细语终成高论宏裁。 ——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授奖辞
于坚的散文题材广泛,语言自由,心接古今。他将口语和书面语交替使用,使得他的叙述和描写,在体验和经验、现实和历史之间来回巡游、自由穿梭,堪称当代散文精品。
——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 授奖辞
回到内心,回到生存的现场,回到常识,回到事物本身,回到记忆中和人的细节里,一直是于坚写作的一种内在愿望。
——谢有顺
1
云南建水城,古称临安。临安本是杭州,那个中国天堂的旧称,云南建水这个临安是明代命名的。就像欧洲移民到了北美大陆,沿用欧陆地名而取的“新奥尔良”“新英格兰”一样,建水这个临安是一个新临安。这个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的命名暗藏着野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建水人要在他们的家乡建造一个杭州那样的天堂,他们成了。过了152年,明嘉靖十三年(1534),被流放云南,“永远充军烟瘴”的大诗人杨慎来到建水拜访他的朋友叶瑞,建水城令他大吃一惊,杨慎写了一首诗《临安春社行》,描绘他所见的建水:
临安二月天气暄,满城靓妆春服妍。
花簇旗亭锦围巷,佛游人嬉车马阗。
少年社火燃灯寺,埒材角妙纷纷至。
公孙舞剑骇张筵,宜僚弄丸惊楚市。
杨柳藏鸦白门晚,梅梁栖燕红楼远。
青山白日感羁游,翠斝青樽讵消遣。
宛洛风光似梦中,故园兄弟复西东。
醉歌茗艼月中去,请君莫唱思悲翁。
令我惊讶的是,杨慎诗里描写的建水,并未隔世,我几乎以为,杨慎才搁笔走了不久。杨慎笔下的这个建水城大体上还在着,不仅是城池、建筑、雕梁画栋、朱门闾巷、水井、牌坊、饭馆、荷塘稻田……*重要的是,杨慎诗中写到的那个世界,虽然细节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氛围依然可以感受到。“少年社火燃灯寺”,燃灯寺还在,依然在敲着木鱼。寺院门口的那口井依然清冽,杨慎如果在燃灯寺喝过寺僧沏的茶,茶水应当就是这口井里的水。几个闲人坐在井边,聊天,嗑瓜子,要到吃午饭才会散去。只是看不见社火,因为春节才过不久,社火刚熄。当年杨慎来建水找叶瑞玩时,住在太史巷的叶氏宗祠,太史巷现在叫作太史巷街,这条街还在,这是一个奇迹。在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拆迁运动中,有些古城幸存下来,但大多数都成了民居博物馆,原住民被搬迁,只剩下建筑空壳。看上去古色古香,内里全是商店,再没有“炊烟逗屋”(仇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建水岿然不动,我行我素,“邦有道,谷”,依然是原住民的故乡,过着与杨慎来访时大同小异的日子,水井安然,汲水的、挑水的、送水的、扫落花的、做豆腐的、纳鞋底的、补衣裳的、做木工的、做凉粉的、开茶馆的、做米线的、弹棉花的、养花的、玩古董的、做陶器的、银匠、屠夫、鱼贩……洗衣的妇人也还蹲在井边,背上依然背着个娃娃。明月依然在这个城里“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015年冬天,我带着我的朋友麦约翰来建水,他是比利时人,自号无能子,一生都在研究中国文化,将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弗莱芒语。他在建水长叹,他一辈子要找的那个中国,就在这里。此后,他多次来,开始写一本关于建水的书,并将他女儿送到昆明来学习中医。
建水如今已经被一座座同质化的新城围困,危机四伏。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多次来建水,小住,长住,我目睹了它的犹豫、变化和坚定不移。人类为什么会有建水城这样的栖居地?它又为什么落后于时代?又为什么因“落后”而鹤立鸡群,不同凡响?数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11
在建水,*好玩的事就是串门。敲开这家进去看他家的水缸,敲开那家去看他家的窗子。居民好客有古风,进去参观他们很高兴,来客都是贵人。把别人的故乡当成博物馆,自己没有这样的家了么,那样的家就成了审美对象。串门幸好是老马带着,这是熟人社会,陌生人可找不到门。老马毕业于艺术学院,不画画了,做些设计混日子,活得像个古人,不求上进,没有手机,只是读书、修身养性、吹散牛,朋友来么陪着耍耍。
老马说他一个月只用几百块钱就够了。我开始有些不相信,怎么活嘛。后来发现,老马这么活:穿个可以穿一百年的皮夹克,穿到起包浆,越穿越好看。早上窗外日迟迟的时候,起床出门,先站在巷口发阵呆,看“红杏枝头春意闹”,然后去王麻子开的米线馆吃碗氽肉米线,十块钱一海碗,倒进肚子一上午就饱饱的了。然后去赵家大院看他家养在石缸里的金鱼,金鱼好看,石缸更好看,正面用柳体刻了两行诗,刻的是:初日照林莽,积霭生庭闱。还刻着几根兰草、一窝怪石。一口缸,打造得像个小博物馆似的,又是书法,又是绝句,又是浮雕,本身又是养鱼的水池,金鱼像宫娥一样游来游去,赏心悦目到了极致。恰有一尾金鱼拨开水草帘子,抬头看看天色,又一摇桨驶回深处。老马也跟着看看天色,已经忘了今天要干什么,干脆与这家的主人下盘象棋,三局两胜。半晌,伙计找来说有个花园要设计装修草图,这才回工作室去画草图,老马不喜欢电脑,他用自己的脑。想着,说着,草图让毕业于设计学院的伙计用电脑做。然后又走去云老师家看他的新作,准备“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路上经过杨妈妈家的院子,梨子熟了,大妈摘两个给他,用井水冲冲连皮吃掉,又饱了。朝正蹲在水井边洗衣的姑娘们瞅瞅,想起没烟了,又折到燃灯寺旁的小铺子去买,然后去寺里的老柏树下一坐,先抽上一根。看看上星期开的那些花开完了没有。云老师不在,敲门不应。回头见老郑家的门开着,推门进去,郑家是个小四合院,老郑也不在,老马自己找把躺椅,拉到阴凉处,小睡一刻。醒来时老郑还没有出现,抬手摘两个枇杷捏着,走了。这回走去迎晖楼前面的小广场。满场的闲人,坐着的、躺着的、蹲着的、抱娃的、下棋的、理发的、卖药的、走江湖耍把戏的、唱戏的……城里的象棋大师正在敲旗,被闲人团团围住,指手画脚,都帮着那个手生的呢。老马挤不进去,就找棵树靠着,借着树荫,听着旁边敲棋子的声音再眯上一刻。挨晚,老马回到他母亲的老宅子,老母亲千年如一日的晚餐已经摆在桌子上,正盼着儿子呢。晚上他读书,不看电视。到个九十点,老马要睡了。老马喜欢说:“天睡我睡,天醒我醒。”
跟着老马。进了这家看见一排栏杆,而主人一家正在桂树下打麻将,只是歪头笑笑说:“坐嘛,坐嘛。”进了那家,看见人家的中堂挂着钱南园先生的字,供桌上摆着建水民国时期的制陶大师戴得之做的黑陶花瓶,上面的梅花画得那个灿烂,字写得那个云烟乱飞。一人蹲在水井旁边宰鸡,四五个姑娘在洗菜,亲戚朋友坐了一院子,都等着吃呢。这些院落大多数彼此相通,你家的竹子是我家窗子前的水墨,我家后花园的桃花是你家前厅的粉彩,我家的桂花为你家的黄昏而香,你家的喜鹊为我家的客人而唱。户户垂杨、明月古井、雕梁画栋、茂林修竹、小桥流水……大家共享,都是好在的地方。看罢出来,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想要是住在这院就好了,又想住在那院也好。
跟着老马。去看土地庙,土地庙就是过去供奉大地之神的地方,现在不供了,但庙还在,改成会议室。门锁着进不去,只能隔着窗帘缝瞅瞅。院子里闪出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老者,听说我们对土地庙感兴趣,很高兴,马上喋喋起来。老者说,建筑专家认为有唐代的风格。这一指点,果然看出那黑黝黝的大梁,大气古朴,结构庄严。又说个故事,有一天夜里他看见土地公公躺在柏树下哭,他本来是坐在庙正中间的神龛上的。天亮后,土地公公的塑像就被红卫兵砸掉了。老者说罢,忽然就不见了,其实他和我们道别,还握过手,但感觉是突然不见了,觉得他就是那位被免职的土地公公。
跟着老马。已经中午,肚子有点儿空了,就去永宁街的快餐店里,花十元钱吃个三菜一汤。建水的快餐店与别处不同,不会自惭形秽,它就是为平民开的。建水一城都是平民,一切设施、服务都是为普通人着想,*高级的地方是文庙,但只是建筑高级,这个高级也是为了让平民出出进进。永宁街的小馆子一家连一家开了半条街。为了省电,小馆子里面黑漆漆的,只见杯盘碗勺在闪光,倒有一种中世纪的气氛,仿佛在里面随时可以遇见堂·吉诃德和桑丘。早三十年的话,小酒馆外面还会拴着马匹。现在没有马匹了,有时候收废品师傅的三轮车会停在附近,人在里面吃着呢。食客有闲人、失业者、老板、公务员、乡下人、土著、民工、扫大街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学生、大爷、舅公、叔叔、婶婶、大娘、姑娘、婆娘……有个流浪汉天天来吃,五十多岁,蓬头垢面,靠着天井边的小桌子,喝一盅苞谷酒,嚼几颗花生米,还哼点什么,天天来。一碟爆炒猪肝、一碟清炒韭黄、一碟老奶洋芋,一杯白酒,一碗米饭,也就是十块钱,米汤免费。炒菜的大锅支在店门口,厨娘就像众人的保姆,胖而敦实,绝不因为价格便宜而马虎,一盆子打好的鸡蛋滑溜溜地倒向热油里去,即刻哗啦啦爆响起来,大锅铲噼里啪啦拨拉一阵,一盆黄生生的炒鸡蛋已经诞生。那爆响拨拉之声使得满堂都像在一口大锅里似的,个个吃得热腾腾、喜滋滋。彝族女人黑亮的脸庞在锅边闪光,用小勺喂她的小孩,说是来城里面卖桃子,吃完饭就上山了。我点了这三样:丸子两个、小葱爆豆腐、青豆炒苞谷。老马点的是油淋牛干巴、草芽肉片、小白菜。正嚼着,抬头看见云老师路过。“来喝口嘛!”老马叫道。云老师是个画家,以前经常背着画箱去西双版纳写生,现在不去了,画建水。云老师站在大锅旁边和老马聊了几句,那保姆又炒出一窝鸡蛋,金子般地放着光。云老师说:“不吃了,先走一步,还要去浇花。”
用户评价
从个人情感投射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具有一种奇特的“共振”能力。它所描绘的许多情境,虽然在表面上可能离我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但在情感的底层逻辑上,却有着惊人的契合度。作者似乎拥有将个体微妙的、难以言喻的感受,提炼成精准文字的能力。我尤其欣赏它对“孤独”的探讨,那不是那种戏剧化的、令人怜悯的孤独,而是一种清醒的、带着尊严的独立状态。它探讨了现代人如何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中,依然固守住自己内心最后那片未被污染的净土。读完后,我没有感到被安慰,反而有一种被“理解”后的释然,仿佛有人替我把那些混沌的情绪整理成了一条条清晰的脉络。这种深层次的契合,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像是一次私密的精神对话,它的重量感和深度,久久地停留在心头,难以消散。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处理,简直是一场精妙绝伦的语言实验。它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但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像是经过了最严苛的筛选和校准,精准得让人心惊。我注意到作者非常偏爱使用那些看似矛盾或不协调的意象组合,比如“沉默的喧嚣”或者“清晰的模糊”,这种对立统一的手法,成功地在读者的认知边缘制造了一种张力,让人在理解与困惑之间徘徊。更绝妙的是,它在探讨那些宏大主题时,总是能巧妙地锚定在极其微小的生活碎片上,比如一片掉落的叶子,或者一个不经意的咳嗽声,通过这些“小点”,折射出宇宙的广阔。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让原本可能显得空泛的议题变得可触摸、可感知。读完某些篇章后,我甚至会下意识地去模仿作者的观察角度,试着用那种新奇的视角去看待窗外的街景,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阅读体验——它不仅仅是阅读文字,更是在重塑你感知世界的方式。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氛围感营造是顶级的。它不是那种让你一眼就能抓住故事主线的作品,更像是一张铺展开来的、带着湿气的旧照片,色调是沉郁而内敛的,却又在某处闪烁着不屈的光芒。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在场感”非常强烈,你仿佛能闻到空气中的灰尘味,感受到某种古老建筑的阴凉。作者对于环境的描摹,超越了简单的背景设置,那些建筑、街道、甚至光影的变化,都成了情绪的载体和哲思的载体。我个人觉得,它探讨的与其说是“人在世间”,不如说是“世界如何容纳人”。很多地方读起来,会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疏离感,但这种疏离并非全然的负面,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距离,让你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更冷静地审视自身的处境。这种独特的冷峻美学,是市面上很多追求通俗易懂的作品所无法企及的。
评分那本书一翻开,我的思绪就被一下子拽进了那种独特的语境里。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更像是一种意识的流动,作者似乎在用一种近乎喃喃自语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个半透明的场景。初读时会有些吃力,因为节奏感非常跳跃,上一秒还在描绘着极其具象的物件,下一秒就跃升到了某种哲学层面的探讨。我特别喜欢它对“时间”的处理,那种感觉不是线性的流逝,而是像一块被反复揉搓的橡皮泥,过去、现在、未来似乎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呼吸之中。比如,他对“等待”的描绘,不是枯燥地描述等候的过程,而是将等待本身塑造成一个具有重量和质感的实体,让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时间的密度。这种写法很考验读者的耐心,但一旦你适应了它的频率,就会发现里面蕴含着一种惊人的生命力,仿佛所有的日常琐碎都被赋予了一种近乎神性的光芒。它迫使你慢下来,去重新审视那些你以为早已看透的细节,那种细腻入微的观察,常常让人拍案叫绝,感觉自己仿佛被拉入了一个更深邃的内心迷宫。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设计,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座精心搭建的迷宫。它没有明确的章节划分,文本的推进更多依赖于情绪的起伏和意象的联结。我读到某些段落时,会有一种强烈的“回响”感,前文的一个不经意提到的词汇,可能在后半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再次出现,形成一种螺旋上升的阅读体验。这种复杂的互文性,要求读者必须保持高度的专注,并且乐于在文本内部进行穿梭和连接。对于习惯了线性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挑战,但对于愿意投入时间去“解构”和“重建”意义的人来说,它提供的回报是巨大的。每当你以为自己掌握了作者的思路时,他总能用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将你的认知推向新的维度。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其魅力所在,让每一次重读都可能带来新的发现和感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