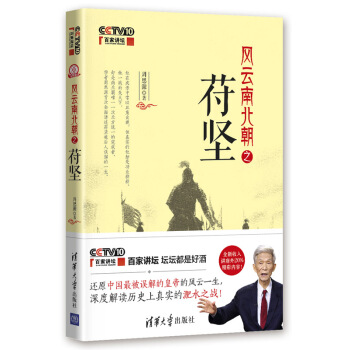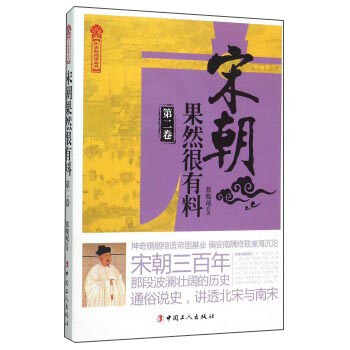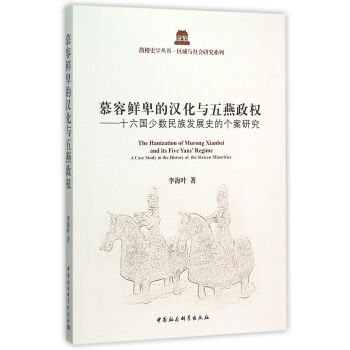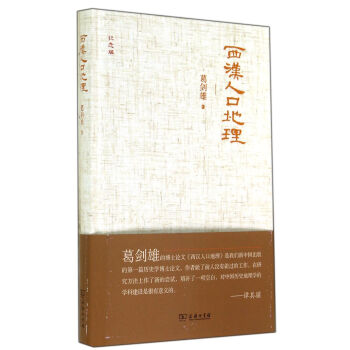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西汉人口地理(纪念版)》系作者的博士论文,也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作者在系统梳理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人口迁移。书后附有各郡国人口数量、增长及迁移的表格。《西汉人口地理(纪念版)》为研究汉代历史必备之书,也是目前博士研究生撰写论文的经典参考书。作者简介
葛剑雄,1945年出生于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历史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人口史,》(卷一)、《中国移民史》(卷一、二)、《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悠悠长水:潭其骧传》、《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走非洲》等。目录
序绪论
第一节 研究历史人口地理学的意义
第二节 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的有利因素
第三节 本书以西汉时期为研究阶段的原因
第一篇 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第一章 现有研究成果及史料的评价
第一节 关于西汉初人口数的研究状况
第二节 《汉书·地理志》户口数的意义
第二章 从文献记载考察各地区、各阶段的人口变化
第一节 从部分侯国推测第一阶段的人口增长
第二节 部分地区一、二、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三辅地区/原长沙国地区/原吴国地区
第三节 部分地区二、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真定国/泗水国/齐郡和临淄县
第四节 部分地区第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山阳郡/营平侯国/扶阳侯国
第三章 从人口变化规律考察西汉期间的人口增长率
第一节 人口政策
第二节 婚姻状况
第三节 生育状况(总生育率及繁殖率)
第四节 净繁殖率
第五节 家庭规模
第四章 从农业生产及粮食产量考察人口的增长
第一节 粮食产量与人口的关系
第二节 主要农业区与垦田面积
第三节 农具、耕作制度、水利设施
第四节 粮食亩产的估计
第五节 从三辅地区的粮食产量增长率推测全国水平
第五章 关于武帝、宣帝时期的人口变化
第一节 武帝时“户口减半”的文献记载
第二节 武帝时影响人口变化诸因素的分析
1.自然灾害/2.战争与徭役/3.严刑杀戮/4.赋税制度的改变/5.结论
第三节 武帝末年至宣帝时户口数的特殊现象
第四节 几种误解的剖析
本篇结论
第二篇 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
第六章 人口的地理分布
第一节 研究现状的评价
第二节 利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汉志》测定
人口密度的几个问题
1.北方、西北边区的计算范围/2.行政区划变动的处
理/3.几项说明
第三节 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表及其说明
第四节 人口分布概述
第七章 人口分布的形成原因
第一节 自然条件
第二节 经济条件
第三节 政治条件
第四节 历史条件:秦代人口迁移及其影响
第五节 社会条件
第六节 上述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影响
第三篇人口迁移
第八章 关中的人口迁移
第一节 汉初的“实关中”政策
第二节 陵县的设置与徙陵县
第三节 其他徙关中类型
第四节 自关中迁出的类型
第五节 人口迁移数的推测
第六节 人口迁移的特点和影响
第九章 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
第一节 内地人口徙边
第二节 匈奴人的内徙
第三节 汉人徙入匈奴
第四节 羌人、氐人的迁徙
第五节 汉朝内地与西域间的人口流动
第十章 东南地区的人口迁移
第一节 汉初人口的基本状况
第二节 越人内徙
第三节 武帝时徙民会稽辨正
1.有关史料分析/2.会稽不具备接纳大量移民的条件
第十一章 其他地区的人口迁移
第一节 西南地区
第二节 南部地区
第三节 东北地区
第四节 特殊迁徙地——房陵、上庸
结束语
后记
附表
1.部分侯国的户口增长
2.人口密度最高郡国
3.各州每户平均人口
4.各州人口密度
5.武帝期间人口增减年份统计
6.部分侯国户口增长率比较
7.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人口密度
8.人口密度最低郡国
9.元康四年有后裔注籍关中的功臣侯
10.元康四年后裔不在关中注籍的功臣侯
11.徙关中实例表
12.自关中迁出实例袁
13.西汉徙陵县人口及其后裔统计表
14.关中内部迁徙实例表
15.匈奴降人封侯内徙例表
16.东越降人封侯内徙例表
17.南越降人封侯内徙例表
18.朝鲜降人封侯内徙例表
19.徙房陵、上庸诸侯王例表
附图
1.汉初“长安六百里内”范围图
2.汉初长沙国图
3.汉初吴国图
4.秦王朝与西汉王朝疆域比较图
5.西汉人口增长示意图
6.西汉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人口分布图
7.西汉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人口密度图
8.赵国地形与县治分布图
9.西汉盐铁工官及主要交通线分布图
10.西汉陵县图
11.人口迁入关中示意图
精彩书摘
《西汉人口地理(纪念版)》:第二节 《汉书·地理志》户口数的意义
一既然找不到任何现成的确切数字,我们只能根据西汉末元始二年的户口数进行推算。这里先讨论一下这项数字的有关问题。
秦时已经有了全国的户口资料,由汉政权接管并加以利用。刘邦入咸阳时,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使刘邦能“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①,以后在楚汉之争中,萧何在“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②,刘邦查问曲逆县的户口时,能得到秦时和当时的具体数字③,都是明证。西汉时有一套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每年中央政府都能掌握各郡国及所属县、道、邑、侯国的户口数④。应该说,从秦末至整个西汉的户口资料本来是很完备的。
可是在《汉书》中,汉初的户口数毫无提及,甚至对几十年前西汉末年的户口数也已语焉不详。《地理志》中以平帝时户口为“汉极盛矣”,而《食货志》中却说哀帝时“天下户口最盛”。两者虽差不了几年,但如果每年户口数齐全的话,完全可以讲清究竟哪一年是最盛。《地理志》的行政区划以元始年间为断,而侯国却以成帝元延年间为断⑤。有的诸侯王国也没有反映元始年间的实际情况,如梁国,据《汉书·文三王传》,武帝元朔中,梁国被削五县,“梁尚余有八城”,成帝鸿嘉中又削了几次,“或千户,或五百户”,元延中又削五县,则元始时最多只剩三县①,但《地理志》所载仍为八县。而且,各郡国人口数相加实际是57671401,而总数是59594974,县道邑侯国总数是1587,实际相加为1577,可能来源于不同的资料。一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中,只有五县有户、口数,五县有户数。这些都说明,西汉的户口资料在东汉初年已经残缺不全。
尽管如此,《汉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仍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汉人口最基本、最重要的数据。因为班固作《汉书》时,毕竟还可以利用残存的西汉官方户籍档案,数字来自第一手资料。而且当时去西汉未远,出于追忆、传闻的材料也必不少,这就保证了《汉志》的大致正确,各郡国的户口数,更绝非出之臆造。当然,这并不排除其中个别地区的错误计算或传抄的脱漏讹误,故必须在运用时具体分析、辨正。
正因为这是唯一比较完整的资料,对其含义必须正确理解。
第一,班固在总述户口数时只说是平帝时的情况,并未确指何年,仅在京兆尹下注明为元始二年数。考虑到原始资料的残缺以及《汉志》颇有体例不一之处,我们很难断定其他郡国都是元始二年的数字,只能说是西汉末期(哀、平间)人口高峰时的数字。但数年的差异对于我们统计数十年乃至二百年的变化时影响不大,目前又无法确定每个数字的具体年份。为便于计算,在以下论证中仍都作为元始二年数处理。
……
用户评价
说实话,初拿到这本“纪念版”时,我还有些疑虑,担心它不过是旧作的简单翻印,缺乏新意。然而,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和对新史料的整合,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它成功地挑战了过去一些将西汉人口波动简单归因于政治事件的传统观点,转而深入挖掘了气候波动、瘟疫传播路径乃至地方行政区划调整对人口密度的潜移默化影响。其中关于“郡国并行制”下,人口在中央直辖区和封国领地间流动差异的对比分析,尤为精妙。作者旁征博引,不仅引用了《汉书》中的记载,还结合了考古发现的聚落遗址数据,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验证体系。这种严谨的交叉验证,让结论的说服力大大增强,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研究视野。这哪里是简单的“人口研究”,这分明是一部用数字和地图重塑的西汉社会动力学模型,值得所有严肃的历史爱好者珍藏。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渐进式的,初看时会被其庞大的数据和略显古奥的学术术语所震慑,但一旦你抓住其核心逻辑——即地理区位决定了人口的潜力和韧性——就会豁然开朗。它真正厉害之处在于,它教会了读者如何“阅读”一张历史地图。作者并非是简单地把人口数据“贴”在地图上,而是通过空间分析技术,揭示了资源梯度如何形塑了古代的社会等级和经济联系。例如,书中对“九江郡”等长江中下游关键区域的人口结构演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揭示了当地土著与中原移民融合过程中的人口流动趋势。这种研究方法,对于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扩散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地理学支撑。它迫使我跳出“朝代更迭”的线性思维,转而思考历史的“空间惯性”和“地理制约”,受益匪浅。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我的初始预期,它成功地将枯燥的人口统计学转化成了一门引人入胜的叙事艺术。它不仅仅是研究西汉的人口,它实际上是在描绘一张西汉“权力”与“资源”的地理分布图。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地理区域(如高原、盆地、沿海平原)人口密度与生业结构变化的对比分析,构建了一套可量化的“区域发展模型”。这使得我们可以用更科学的眼光去审视汉代边疆政策的得失。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精确的标尺,去衡量历史变迁中的“尺度感”。读罢全书,我感觉自己不仅重新认识了西汉,更对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决定论”与“人文能动性”之间的复杂博弈,有了更为辩证和深刻的理解,这绝对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评分这本《西汉人口地理(纪念版)》实在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著作!作者在构建历史版图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口数字的罗列,而是巧妙地将地理因素融入其中,描绘出了一幅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古代社会图景。我尤其欣赏其在解释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时的细腻笔触。例如,书中对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与相对贫瘠的西北边疆地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承载力差异的论述,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通过精细的地图和图表分析,你能清晰地看到,每一次王朝的兴衰、每一次重大水利工程的修建,是如何在微观层面影响到数以万计百姓的迁徙与定居。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亲身感受到汉代郡县设置背后的深层逻辑,理解了为何某些战略要地会长期保持高密度的人口聚集。这种将宏观历史事件与微观地理约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拓宽了我对西汉社会结构理解的维度,远非一般通史著作所能比拟,读完后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提升了一个全新的层次,简直是历史地理学的饕餮盛宴。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也值得称赞,作为“纪念版”,它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那些原本在老版本中模糊不清的古代地理图谱,在这里都得到了高清的重制和精准的标注,这对理解西汉郡县的边界变迁至关重要。我特别喜欢其中穿插的几篇“专题研究小品”,它们像是为主要章节准备的美味甜点。比如,其中一篇专门探讨了汉武帝时期河西走廊的人口拓殖与后勤保障体系的相互关系,这个角度非常刁钻,也极其重要。它不仅仅是描述了“有多少人去了那里”,更深入地探讨了“如何维持在那里的人口生存和战斗力”,这涉及到了水源、盐场和军事屯田的地理学布局。阅读这些小品,感觉就像是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走进了历史的幽微之处,那些教科书上被一笔带过的地名,此刻都鲜活了起来,有了具体的地理和人口故事。
评分人日二首步少陵韵(选一)
评分八十年代的经典著作,精装重印
评分葛劍雄博士論文!!!
评分跟周先生的政区地理一样,都是名著,收藏。
评分葛剑雄先生的代表作,期待
评分答张意霞
评分经典之作,看看大汉雄风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评分SA-9393III 15.1英寸超强升级版防水1680D面料时尚休闲双肩笔记本电脑背包 黑色
评分八解(尾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古埃及史话:埃及的神+埃及艺术+埃及生活+埃及历史+埃及发明(全彩页套装共5册)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98293/56fb85a1N6bdeb5a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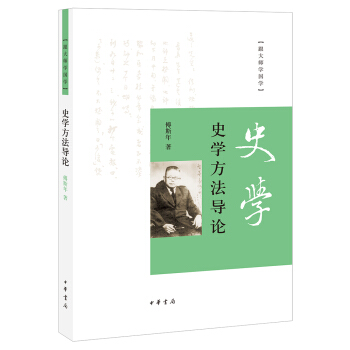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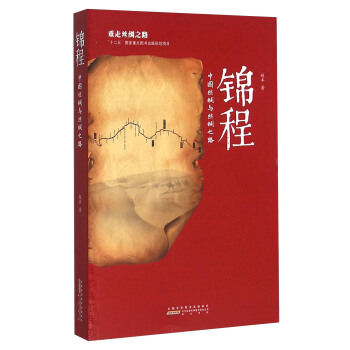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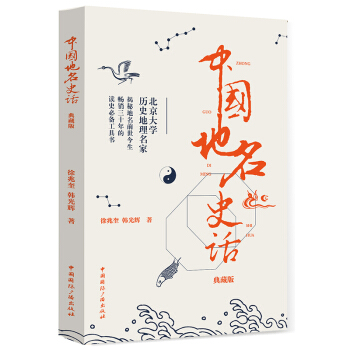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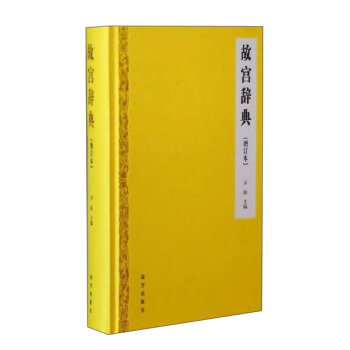
![三国史秘本(套装全2册) [秘本三国志]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67033/57cf815cNcca64ed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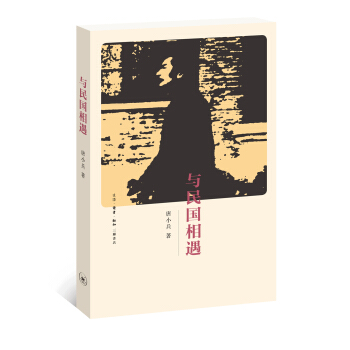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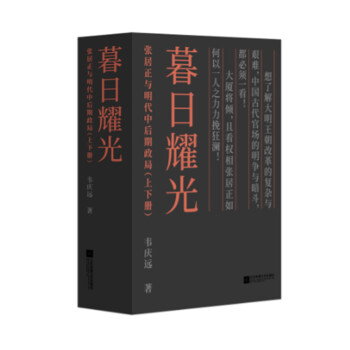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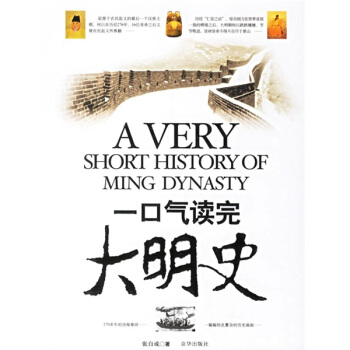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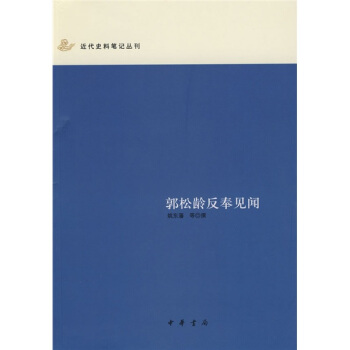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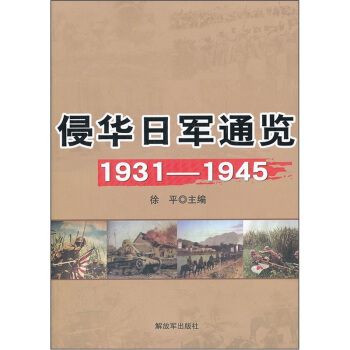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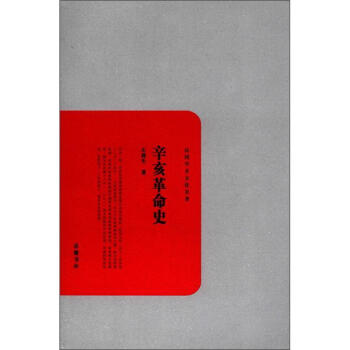
![老照片(第83辑) [Old Photo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046891/rBEGD1AfjmEIAAAAAADHCiH1OH0AABU8wGZjDwAAMci07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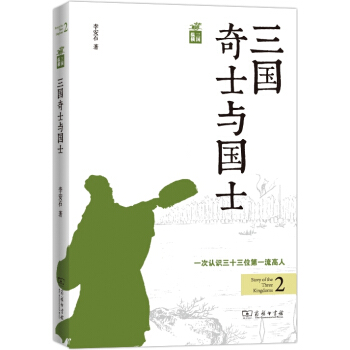
![遗失的城市 [Ancient Civilizatio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63159/54471140N1f29e0b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