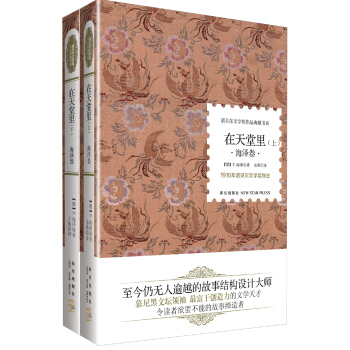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至今仍无人逾越的故事结构设计大师,慕尼黑文坛领袖,最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天才!令读者欲罢不能的故事缔造者!
内容简介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在天堂里 海泽卷(套装上下册)》生动地描写了慕尼黑艺术家的生活,并以此来反映道德问题,描写了反对清教苦行主义、保卫艺术纯洁性的斗争。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作者简介
P.海泽,他的作品主题多是吟哦爱情,艺术上讲求构思、运笔细腻、引人入胜,坚持典雅秩序的古典风格。他持续创作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作品异常丰富。他的“猎鹰”写作理论,让他的每篇小说都充满结构的张力,成为令读者欲罢不能的经典。目录
第一部分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二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三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四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五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六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七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
精彩书摘
那是1869年仲夏的一个星期六。南方的空气经过昨夜雷雨的清洗,依旧温润如玉,呼吸也变得自由顺畅,但是在阿尔卑斯以北,却出现了少见的持久晨光。慕尼黑圣母教堂大弥撒的钟声已经响起,这声音穿过竖立着伟大的巴戈利亚雕像的特瑞西恩广场。这里地处郊区,人迹罕至。巨大的青铜少女塑像独自伫立在这荒野之中,手中握着置于头顶的花环,脸上的表情迷茫而恍惚,仿佛在思索是否应该在此刻走下大理石基座,去城镇里闲逛。如今,这片荒野上修起了塔楼和房屋,就像在一个裸露的绿色平原上修建一片墓园。时不时会有一只小鸟从万神殿后面的小树林飞过来,拍拍翅膀落在少女的肩膀上,或者在旁边狮子的鬃毛上小憩一会儿。这只狮子紧挨着女主人的膝盖,懒懒地坐着,似乎在聆听。但是在城镇的远处,钟声依然飘荡。空气的温度开始持续升高,远处打钟的嗡嗡声引发了空气的颤动,昨天才刚收割过的牧场飘来一阵浓烈的青草香味,这一切混杂在一起,让人不觉昏昏欲睡。最后,钟声停止了,所有的声音也随之消失,只余一阵笛声时断时续地从外城某条街上的某间房屋中传来。吹笛的人仿佛每完成一节都要停下来调整一下呼吸,又或者因为其他思绪的扰乱,忘记了自己正在演奏的曲调。
这间在西郊随处可见的房屋离街道很远,笛声从其敞开的二楼窗户的房屋中传出,弥散在夏日的空气之中。这些像盒子一样的房屋非常朴素,没有任何装饰,只在北面有一扇窗。四边形的窗户开口很大,想尽了各种办法让天上的太阳能够持续不断地给屋内供给阳光。夏天,很少会看到某户人家自家的炉膛冒烟,在饭点跨进门槛的访客也不会闻到饭菜的香味,慕尼黑大多数的人家都是这样。在敞开的窗户上飘荡的只有光和若隐若现的烟草气味,混合着清漆、燃油和松节油让人神清气爽的芬芳——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此地,你能找到的吃食就只有神圣的艺术火花,而且,此地静默的圣餐桌①上所供奉的祭品,甚至都不能庇佑提供祭品的神父免饥肚饿的折磨。
我们所说的这间房屋没有窗户的南面朝着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四处散落着各种尺寸的大理石和砂岩石料。从北面四扇工作室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见一个受到精心照顾的、窄小的花园,为它们遮挡了所有让人不快的反射光。花园中间一个狭长的小喷泉,慵懒地喷着水花,环绕在喷泉周围的是一群热烈开放的玫瑰。紧挨着的是几个花坛,花坛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果蔬植物,花坛边上长了一圈厚厚的木樨草。花园里没有燃油和松节油的味道,尤其是在二楼工作室只有两间的窗户打开的时候,这些味道就完全无法渗透到花园中了。站在院子里一堆堆的石料旁边,可以看到在一楼工作室里,有一位雕刻家正在赶制他的艺术品。
艺术家的日子通常都过得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在工作时有一种无限期的度假情怀,他们也不需要时常忙于安息日的定期庆典。那些必须参加这些庆典的人,就不得不在一些小生意上花费精力,在一个所谓的“艺术之城”中,很少有人愿意接手像“艺术俱乐部”订购的图片这样的生意。
但是这种小房子里的居民并不是这样的人。
在底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温暖气流能够进入这间太阳照射不到的房间,窗户上所有能够打开的窗格都打开了。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吸入更多芬芳的花香或者楼上悠扬的笛声。一群麻雀利用一切机会在这个花园中呼呼地飞进飞出,似乎已经习惯了将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它们啁啾打骂,在铺满了工作室其中一面墙的常青藤丛中扑棱欢跳,踏遍每一个角落,寻找遗漏的面包屑。然而,所有的这一系列动作似乎都受过良好的教养,它们从不制造任何麻烦,除了喧闹的叫声——它们在半身像和泥塑模型之间穿梭,在房间的地板上、画架上、托架上驻足观望,留下杂乱的拜访痕迹。这个大大的房间中间放着一块湿布,湿布里面仔细地包裹着一大团新鲜的黏土,这样做可以让黏土不致干裂。一只看起来有些蓬头厉齿的老麻雀坐在湿布上,以一种相当端庄的姿态静静地观望着他。显然,它是这群野军的头领。对它来说,这个座位清爽舒适,惬意非常。它没有和那群小辈一起嬉戏打闹,而是以一种挑剔而严肃的眼光注视着这位穿着灰色工装的雕塑家,他将他的塑模桌移到了窗边的位置,正忙于从模特儿身上取材,塑造一尊舞动的酒神女祭司塑像。
模特儿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看样子还不到18岁。她站在雕塑家对面的一个小板凳上,她的手臂向上抛出,略微往后,紧紧地抓着一根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横杆——因为女祭司的塑像便是手中握着一只手鼓,正猛地往上抛出。这个姿势完全称不上舒服。这个女孩儿已经一动不动地保持这个姿势整整半个小时了,却一点儿都没有抱怨想要休息。即使她不得不将脑袋尽力往后仰,红褐色的头发也已垂到了腰部以下,但是她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她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这样一来长长的金色睫毛就会静静地盖在脸颊上——看着雕塑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挑剔和比较的眼神。她的青春美丽受到雕塑家如此认真仔细的研究,这似乎是对她极大的奉承,虚荣心的满足已然让她忘记了疲惫。她的身形确实不同寻常,修长而优雅,粗糙的褐色棉布裙紧紧地包裹着她那富有弹力的腰身,就像一朵从糙壳中开出的美丽花朵。少女的肤质白皙细腻,仿佛这个可怜的孩子平时没什么别的消遣,只顾护理自己的皮肤似的。她的面容完全称不上漂亮:鼻子非常扁平,大大的鼻孔下方是一张大大的半合着的嘴。这张不太规范的嘴让她的整张脸看起来有些野性,像极了某种动物。但是在这张嘴巴里,却闪耀着两排完美而漂亮的牙齿。她丰满的双唇露出了一个快乐、天真、孩子般的微笑,但是她的眼睛却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她脸上的肌肤明亮、透明、白皙,零星点缀着几颗雀斑,脖子上和胸前也有两三颗。当她发现有人如此专注地研究她的美丽时,孤芳自赏的得意便难免显得有些滑稽;而当她看到自己少女的一面受到如此尊重时,她似乎已然忘了要怎么在这种场合卖弄风情。
“你一定累了,岑茨,”雕塑家说道,“你不想休息一会儿吗?”
她笑着摇了摇红褐色的头发。“这儿太冷了。”她说着,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在如此宽敞的空间里,你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况且花园里还有木樨草的香味传来。我相信我能坚持到晚上。”
“如此便好。我正想要问你冷不冷,想不想要一个披肩。肩膀部分我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做手臂部分。”
他继续认真且安静地进行着自己的雕塑。柔顺而夹杂着几分灰白的金发勾勒出了他相貌平平的脸庞,一眼望去,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他的眼睛,闪耀着不同寻常的坚定和热情。当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点上时,他的一双眼睛似乎要将其看到的东西完全吞噬,完全掌控。除了这双眼睛,脸上的其余部分不会展现更多的表情。
“楼上吹笛子的人是谁啊?”女孩儿问,“一周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楼上还非常安静;但是今天每隔几分钟,楼上就有人走过来、走过去,而且还有人吹笛子,然后又会安静一会儿。”
“我的一个朋友租下了楼上的工作室,”雕塑家回答道,“他是一个战争画家,罗森布施先生。如果工作进展不顺利,他就会那样走来走去,并吹起他的长笛,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然后,他会在画架前面停下来,看着自己的画作,直到想好下一笔落在何处。你在笑什么呢,岑茨?”
“他的名字,罗森布施!还有画战争!——他是犹太人?”
“我觉得不是。但是,现在你想要休息一小会儿了吗?——你的脖子肯定已经很僵了。”
她立即放开了横杆,从板凳上跳下来。他拿起他的塑模工具开始打磨已经完成的部分。此时她站在他身旁,双手交叉放在身后,仔细地看着这尊漂亮的雕塑,一束特别的光亮打在她的身上。最后一个小时的进展很快,但是也只完成了上半身。这位舞者如泻的长发遮盖了她那栩栩如生的臀部和四肢,只能粗略地看到轮廓。
“满意吗,孩子?”雕塑家问,“但是我最多也只能用大理石来为你雕刻,其实你更适合做画家的模特儿。你那如雪的肌肤和火红的头发真的很漂亮——如果你生活在两千年前就好了,那时他们都用黄金和象牙塑像,那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黄金和象牙?”她若有所思地重复道,“那肯定都是一些有钱人!但是,能用漂亮的白色大理石我就非常满足了——就像你身后的那尊年轻人,还没完工的那个。”
“你喜欢他?那是我很久以前刻的了。这样不好吗,小小的、圆圆的脑袋坚定地挺在宽宽的肩膀上?可惜我只刻了脸,不然你也会喜欢的。”
“你也会用那儿的那些黏土为我塑像吗?我的意思是,做成我的样子——我的朋友一看到就会说‘快看,红发岑茨’?”
“说不准。我可能只会用你的小鼻子和尖尖的小耳朵。但是,孩子你知道的,我还有另一个愿望;而且,只要你愿意帮我,我就能向你保证,绝没人会想到红发岑茨是我的模特儿。你考虑好了吗——上个星期我问你的事?”
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岑茨,而是继续细致地打磨揉捏那柔软的黏土。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最近刚看完的一本小说,叫《百年孤独》,简直是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盛宴,它的叙事结构复杂得让人赞叹,像一棵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生命之树。马尔克斯用那种近乎神谕般的语气,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兴衰,时间在书中不再是线性的,而是螺旋式上升和循环往复的。你读着读着,就会被那种浓郁的拉丁美洲气息所包裹——黄色的蝴蝶、冰块的神秘、无休止的战争与爱情的纠葛。最绝妙的是,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升天、瘟疫般的失眠,被叙述得如同日常生活一样真实可信,这正是其魅力所在。我特别喜欢作者处理“记忆”的方式,它时而是祝福,时而成了诅咒,将一代人的命运紧紧锁在家族的宿命中。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与其说是看故事,不如说是在参与一场盛大的、充满宿命感的家族梦境。我常常需要停下来,捋一捋那些重名的人物关系,但每一次梳理,都会发现新的隐喻和暗示,实在是一部需要反复品读的文学巨著。
评分最近接触了一本非常锐利的社会批判小说——《蝇王》。威廉·戈尔丁的笔触冷峻得像是手术刀,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文明外衣下的人性本能。故事的设定非常简单,一群英国寄宿学校的男孩流落荒岛,却在极短的时间内,从试图建立民主秩序,迅速滑向野蛮与屠杀。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令人不寒而栗。书中的象征意义非常丰富,从那根象征秩序的“海螺”,到象征理性的“猪眼石”,再到那个纯粹的“傻蛋”皮吉,每一个角色和物件都承载着沉重的哲学重量。我尤其被那种气氛的渲染所折服,那种从阳光明媚的沙滩到阴森恐怖的丛林的转变,不仅仅是环境的改变,更是内心世界的崩塌。读完整本书,我久久无法平静,它不提供任何廉价的安慰,只是冷酷地揭示:如果没有外部的约束,所谓的文明可能只是一层薄薄的釉彩。对于探讨人性幽暗面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无疑是必读的经典。
评分最近我重温了一部非常经典的侦探小说,它不仅仅是关于解谜,更是关于时代的侧影和人性的幽微之处。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构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那个最不可能的人。我非常欣赏作者在布局上的严谨和缜密,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对话、每一个角落的细节,最终都成为了揭开真相的关键钥匙。读这类作品,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参与”推理过程,试图在作者的引导下,抢先一步看穿迷雾。然而,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最后揭示真相时,不仅完成了逻辑上的闭环,更提供了一个关于动机的悲剧性解释,使得原本冰冷的案件突然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与无奈。它证明了优秀的类型文学可以跨越流派,具备深厚的文学价值,阅读体验酣畅淋漓,仿佛经历了一场智力上的角力,既满足了对“真相”的渴望,又在故事的结局处体会到一丝人生的唏嘘。
评分我最近在读一本探讨存在主义的法语小说,具体书名我需要查一下,但那种沉闷、疏离的氛围至今仍萦绕心头。作者擅长用极简的语言,描绘一个完全“无意义”的世界。主人公仿佛是一个局外人,冷静地观察着生活中的一切荒谬和重复,他拒绝被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情感所裹挟。阅读体验是缓慢而内省的,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推动,更多的是对日常琐事的细致解剖——比如在海边晒太阳、吃东西、面对别人的询问。但正是这种近乎枯燥的细节,反而凸显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巨大空虚感和对自身存在状态的质疑。这种“抽离感”让我体会到一种独特的文学张力,它迫使读者将视线从外部事件拉回到“我是谁,我为何在此”的根本问题上。那种清晰到近乎透明的孤独感,是很多宏大叙事作品难以企及的。
评分这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在天堂里 海泽卷(套装上下册)》的阅读体验真是令人回味无穷,虽然我这次要评价的不是您提到的这套书,但很高兴能分享一下最近读过的另一部佳作的感受。最近沉浸在里尔克的诗集《杜伊诺哀歌》中,那文字的质感仿佛带着古老的尘埃和清晨的露水,每一行都像是对存在的深刻叩问。里尔克对“美”的执着,那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捕捉,让人不禁停下来,反复揣摩那些关于天使、死亡和爱的主题。他的语言不是用来描述的,而是用来“召唤”的。读到“哦,主,已是时候了。伟大的时刻已到……”时,那种宏大而又私密的叙事张力,简直能让人感受到宇宙的呼吸。全书的节奏舒缓而悠长,像是一首缓慢展开的交响乐,层次丰富,需要沉下心来才能体会到其中暗涌的情感洪流。相比起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这本书更像是一次精神的朝圣之旅,带你深入自我最幽微的角落,重新审视生命与无常的关系。对于那些渴望在文字中寻找形而上慰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剂良药。
评分书还没看,包装很好…
评分好书
评分很好的书籍很好的学习必备佳品,,,,希望宣传能给力的,能越做也好,下次还会在来的额,京东给了我不一样的生活,这本书籍给了我不一样的享受,体会到了购物的乐趣,让我深受体会啊。
评分值得拥有,一直想买,可以夜读了。
评分很好!真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评分非常好的一本书,也是别人介绍的,还没有看
评分那是1869年仲夏的一个星期六。
评分海泽长篇小说,版本难得,值得购买!
评分书还没看,包装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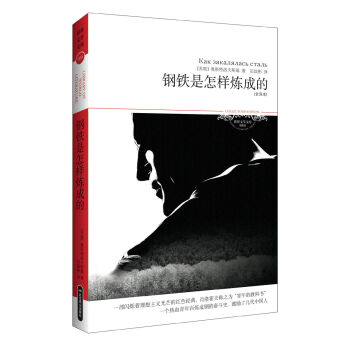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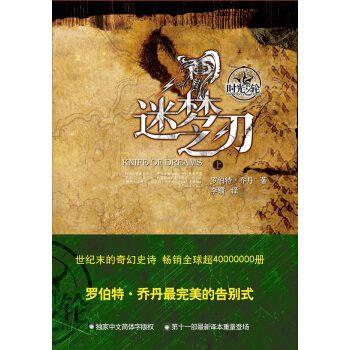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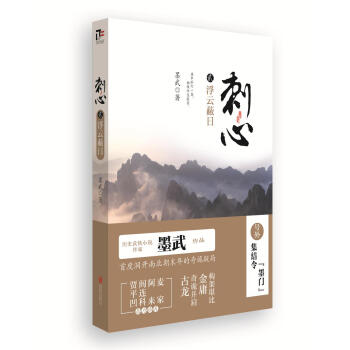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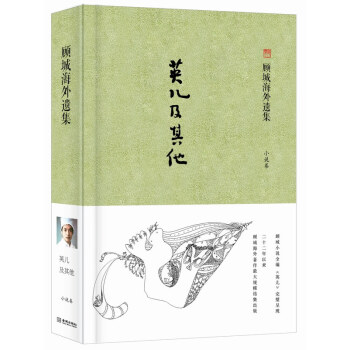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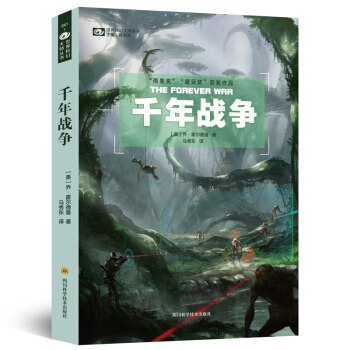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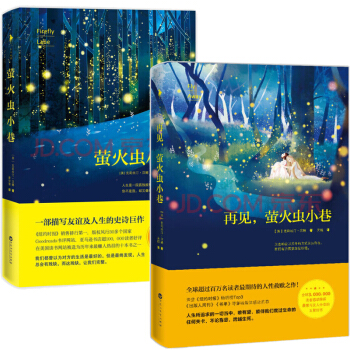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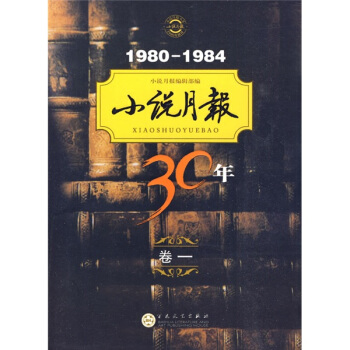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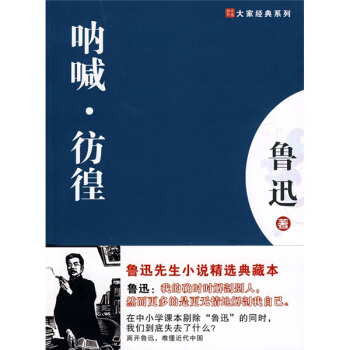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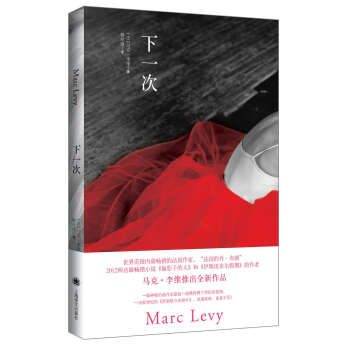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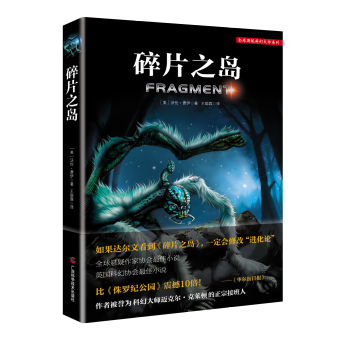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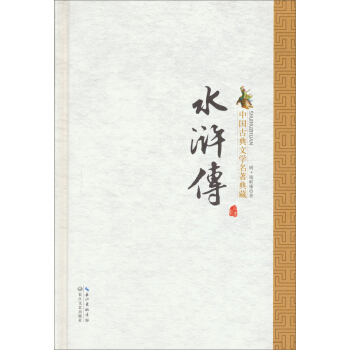

![我的心灵藏书馆:夜色温柔 全英文原版名著 软精装珍藏版 [Tender is the Nigh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28358/56b1b192N4059f49d.jpg)
![译文经典:奥利弗的故事 [Oliver's 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79249/rBEIDE_Neb4IAAAAAADK2tYASY4AAAZBAHp9F4AAMry93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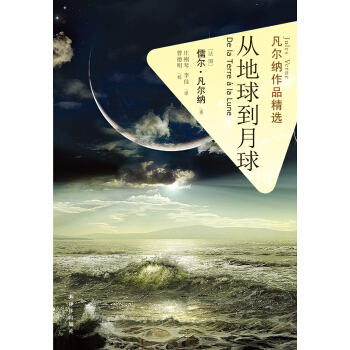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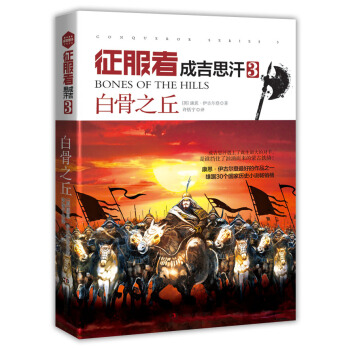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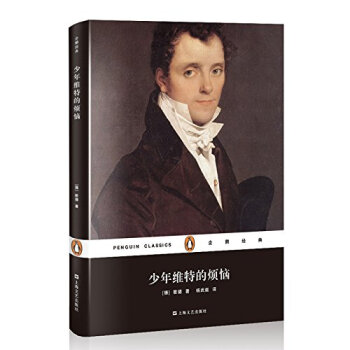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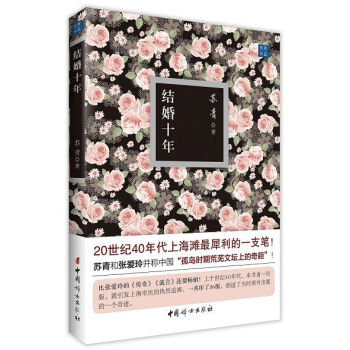
![若非此时.何时? [If Not Now, Whe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31289/566a8d3fN3e2fcd6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