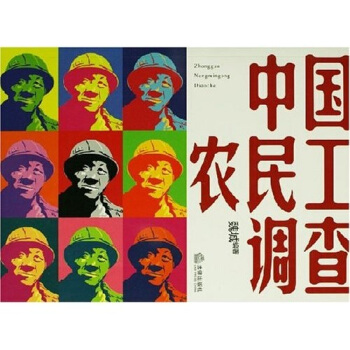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魏城为此前往中国,与许多农民工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和接触,并采访了中国这个领域著名的诸多专家和学者,此外,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也通过接受采访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参与了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讨论。如今,法律出版社使《中国农民工调查》成书,以飨读者。内容简介
《中国农民工调查》作者魏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其间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少有三个“世界之”:人类历史上规模大的人口迁徙潮:民工潮;人类历史上增速快的城市化率;全世界人数为庞大的城市人口。作者简介
魏城,男,1959年出生于中国北京,1992年移居加拿大,1998年移居英国。现居英国首都伦敦。1977年至1980年:在中国当兵。1980年至1984年:在上海读大学。1984年至1986年:毕业分到北京,在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从事立法工作。1986年至1992年:《中国青年报》记者。1992年至1994年:在加拿大留学。1994年至1998年:《星岛日报》加拿大版英文翻译。1998年至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记者。 2005年至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爱好:读书、游泳、旅行和听音乐。最大的梦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终重新移居中国。精彩书评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超过了欧洲和日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目录
序言/1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1
中国城市化走势图 ——胡鞍钢访谈/8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13
第三章 流动中的中国农民/21
珠三角地区城市化中的农民工 ——周春山访谈/28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33
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葛剑雄访谈/41
农民工的零点调查 ——袁岳访谈/46
第五章 “特”不起来的特区/51 “刘易斯转折点”来临 ——蔡昉访谈/57
本地人和外地人 ——金城访谈/63
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71
城市化反思 ——温铁军访谈/78
第七章 户籍与土地/89
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 ——曹锦清访谈/96
历史地看待中国城市化 ——彭希哲访谈/107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115
我赞成农民就地城镇化 ——茅于轼访谈/121
农民工成就城市化 ——刘开明访谈/127
第九章 农民“的哥”/131
出租车司机的酸甜苦辣 ——一位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访谈/138
农民工政策在执行中变形 ——宋洪远访谈/143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147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梦想 ——邱启光访谈/154
从农家小子到京城老板 ——彭雄兵访谈/162
第十一章 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171
让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176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185
后记/193
精彩书摘
异乡不再有虫鸣一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
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
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
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可疑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换了一条椅子,试图与另一位独处的青年女子搭讪:“你从哪里来?”
“我就是东莞人。”同样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但她的安徽口音“露了馅儿”:她不是本地人。
不过,她说的也不全错。行前,我的那位朋友说,东莞目前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肯定超过一千万,但外来打工的农民工是东莞本地人的七、八倍,现在东莞市政府对双方有一个新的称呼:东莞本地人是“老莞人”,外来打工者是“新莞人”。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碰到有人操外地口音、但自称“东莞人”,你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已经在东莞打工多年。
二
如果说珠三角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那广东东莞诸镇就是中国人口大流动、大融合的缩影,凤岗镇也不例外。
我走出车站,迎面扑来的,除了一大堆“摩的”司机(开摩托车的出租车司机)之外,还有缤纷杂乱的店铺招牌:“广西士多饭店”、“河南老乡餐厅”、“凤阳钢丝”、“湖南特色,宝轮物流”……就像美国纽约可以自称为地球的“国际城”一样,凤岗似乎也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因为凤岗街面上的这些店铺在亮出自己的省籍时不仅毫不忌讳,甚至还有点儿自傲、招摇。
那位朋友知道我要去凤岗镇,有些不以为然:“凤岗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外资企业也不是最集中,如果你想看看电子厂最集中的镇,就要去石碣、清溪;如果你想跑跑车衣厂最集中的镇,就应该去厚街、虎门。”
但我要去凤岗镇见一个人:《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的“打工仔”。我比预约时间提前两个小时赶到了凤岗镇,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
离开汽车站,左转,是一条无精打采、颜色污浊、蜿蜒穿越工业垃圾的小河,跨过尘土飞扬的桥梁,再左拐,便是密集的工厂区了。右手第一家,是一个院落不大、但围着铁丝网的工厂,大门上漆着字号很大的繁体中文和英文的厂名,旁边还有两行竖写的小字:“上班时间,谢绝探访”;大门套小门,大门关着,小门开着,小门上贴着一张招工告示,其中诸如“出粮准时”这类典型的港式语言显示:这可能是一家港资企业。
不久,一位踩着自行车的年轻男子悄悄地站在了我的身旁,像我一样,仔细琢磨起这份招工告示来。
“你也在找工作?”我递给他一支香烟。
“是啊!”他露出了烟黄的牙齿,有些局促地接过我的香烟,但他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告诉我:他不相信我是他的同类。
“刚来东莞?”遗憾的是,我只会说没有口音、毫无特色的普通话。
“我以前在这里做过。农忙,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刚回来,重新找工。”他凑近我的打火机,点着烟,深吸了一口。此时,他眼中的怀疑淡了,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但他眼中的困惑,却始终没有随着他不断吐出的烟圈而飘走。 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困惑:不管是在各类工厂门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还是在“凤岗劳务大市场”出入的人,都是20岁上下的农村人模样的年轻人。后来,我索性放弃了装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表白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了攀谈对象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在随后一个多小时的等人时间内,我就是以这种开诚布公的新方式,又与几位来自湖南、湖北、江西、云南的找工者聊了起来。
凤岗镇大概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
不过,尽管他们眼中的困惑消失了,但我心中的困惑却随着攀谈者人数的增多而浓重起来: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年轻的农村孩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涌入这个热闹但肮脏的南方小镇,自愿地投身于这些围着有形或无形铁丝网的工厂?
遗憾的是,大多数找工者行色匆匆,我只能与他们泛泛而谈,难以深聊。就在我试图向一位谈得还算投机的云南乡村青年提及这个问题时,我的手机响了……
三
“你在哪里?”我环顾四周,对着手机喊道。
“我看到你了。”远处一辆“摩的”向我驶来,后座一位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一手拿着手机,一手高高地向我挥舞着。
他就是吴胜发,《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我采访的一位“打工仔”。行前,袁小兵向我介绍说,吴胜发来自江西余干县的一个贫穷山村,因家贫读不起书,所以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出外打工了,但他来到东莞后,从出卖体力的底层工人干起,踏踏实实,勤奋好学,如今已经混到了工程师和中层管理者的地位。“应该说,吴胜发是农民工中的成功者。”袁小兵最后补充了一句。
袁小兵与吴胜发是江西老乡,袁小兵曾写过一篇题为《异乡的机器, 模糊了家乡的虫鸣》的报道,就是专门写吴胜发夫妇的。来凤岗镇之前,我也在网上详细读了这篇报道。
吴胜发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与我握手、问好。他中等个头,瘦瘦的,虽然袁小兵说他年龄已经三十岁出头,但他笑起来,很朴实,甚至还有些拘谨,仍像刚从农村走出来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与我刚刚攀谈的几位找工者似乎没有太大不同,倒是与我想象中的“成功者” 大相径庭。
“没吃晚饭吧?我请你吃饭。”寒暄之后,他对我说。
“哪能让你请,还是我请你吧。”
争抢一番,他让了步。我们坐在另外一辆“摩的”的后座上,穿越傍晚时分凤岗镇那潮热、喧嚣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家东北菜馆。
等待饭菜上桌时,我才发现,他的笑容很有“欺骗性”──他其实很爱说话。他不断问我英国的情况,仿佛我是被采访者:他问了英国的住房、问了英国的医疗、问了英国人的收入、甚至问了当时中国电视报道的英国首相易人的新闻……他的问题那么多,以至于我无法“翻身”,找不到反问的机会。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脑子里却始终缠绕着一个问题:难道当时把吴胜发从熟悉的山乡吸引到陌生的工厂的牵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问的那种对外界的好奇心?
四
离开那家东北菜馆,吴胜发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长的夜车路途中,我终于找到了“翻身”反问的机会。
不过,我发现,谈到自己时,吴胜发不像询问英国风土人情时那么兴奋,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语似乎一直没有“飞扬”过。
吴胜发自己的小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离他的工作地点凤岗镇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为距离遥远,也因为经常加班,他每周仅仅与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共同渡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其余时间只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为什么不在东莞城区找一份工作?或者让你妻子来凤岗镇工作?”我反问。
“不容易啊,我们俩都很难找到收入、职位类似的工作。”车上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他此刻眉头紧锁。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不过一千来块钱。”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简称,没技术,也没“钱”途。而吴胜发现在是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妻子则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东莞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中,能混到这一步的夫妇,实属凤毛麟角,但代价就是“一家两地”。
当然,12年离乡打工的代价远远不限于两地分居。吴胜发夫妇是1995年前后分别来到东莞打工的,那时恰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年代。
尽管吴胜发在东莞生活了十多年,但他对这个由农村演变而成的城市和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仍然没有归属感。
“你问的是什么?什么‘感’?‘归属感’?”此时,我们乘坐的公交车正在穿越另一个灯火妖媚的城镇,借着迷离闪烁的霓虹灯光,我看清了吴胜发眼中的困惑,“没有,没有。我有的只是‘不安全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吴胜发全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租的公寓。吴胜发的妻子吴玉梅正在辅导儿子功课,见我们进门,起身给我们切了一个香瓜。七岁的儿子景辉一边吃着瓜,一边床上床下地跳着:这套一室一厅的公寓,也只有屋里屋外几张床可供景辉跳跃。
吴胜发告诉我,这套月租300元的公寓,其实住了五个人:他们一家三口住里屋,外屋则是吴胜发两个侄女的睡处,她们也在东莞打工。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吴胜发说,这是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当地原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七、八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像他这样的农民工。
吴胜发对亲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在东莞已经干了十二、三年,也未实现他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然而,吴胜发夫妇也没有在东莞买房子。尽管按照他们夫妻俩的收入,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贷款购买自己的房产,但他们至今仍然住在这套狭小、简陋的公寓中。
“为什么不买房呢?”我问。
“在哪里买呢?” 吴胜发反问我,“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确实,没人能够保证。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会阶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还是一个没有东莞户口、因而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外来工”。
见我沉默良久,他又说了一句大概是为了活跃气氛的话:
“趁还能干的年纪,多攒些钱,以后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吧。”他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袁小兵那篇描写吴胜发夫妇报道中的画面──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时怀有对田园牧歌式爱情不可复返的惆怅。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从知识建构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范式。它似乎在挑战传统社会科学中那种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转而强调“自下而上”的经验积累和现象归纳。我注意到,书中对某些社会矛盾的呈现是高度辩证和复杂的,作者并没有急于将群体标签化或脸谱化。比如,在探讨不同代际的农民工之间的观念差异时,描述得极为细致,没有简单地用“新一代更激进,老一代更隐忍”这种二元对立来概括。相反,它揭示了在共同的生存压力下,个体内部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他们对资源分配的不同策略性考量。这种对复杂性的拥抱,使得这本书的结论更具韧性和持久的解释力。它不是一本读完就束之高阁的快餐式读物,而更像是一本需要被反复翻阅和对照的工具书,它提供了一套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底层逻辑框架,其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无数个观察点,而非一个终极答案。读完后,我发现自己看待城市中任何一个忙碌的身影时,都会不自觉地多想一层,去探究他们背后那条漫长而曲折的“在路上”的故事。
评分阅读过程中的感受,更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压抑的潮汐运动。书中的文字,如同被一层薄薄的、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即便描绘的是生活中的希望和努力,也总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漂泊感。我注意到作者在处理个体命运时,展现出一种克制的、近乎残酷的客观性,没有过多矫饰的煽情,没有廉价的道德审判,这使得那些关于工作环境、社会保障乃至子女教育的困境,显得愈发真实和沉重。比如,某段关于返乡的描述,没有渲染离别的伤感,而是冷静地列举了返乡后可能面临的资源稀缺和价值重估的困境,这种抽离感反而加深了读者的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归属”?这本书成功地将一个宏大的经济现象,拆解成了无数个微观的生存困境,每一个困境都像是一根刺,扎在读者的良知和认知上。读完一个章节,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关上书本,在房间里踱步许久,不是因为内容有多么晦涩难懂,而是因为那些被记录下的生活重量,让人难以迅速回到日常的松弛状态中去。它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我们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结构中,那些被高速发展所遗漏和挤压的底层动力。
评分这本厚厚的书,初捧在手,便觉沉甸甸的,不仅仅是纸张的分量,更像是承载了无数汗水与期盼的重量。我原本以为这是一本纯粹的社会学报告,充斥着冰冷的数字和晦涩的理论模型,毕竟“调查”二字摆在那里,总让人联想到PPT上的柱状图和回归分析。然而,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那些朴素的叙事片段,如同从田埂边直接挖出来的泥土,带着未经雕琢的质朴和热烈。作者似乎并未急于构建宏大的理论框架,而是选择了一种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细腻笔触,将我们带入那些熙熙攘攘的城中村、嘈杂的建筑工地和简陋的出租屋。读着那些零散的访谈记录,我仿佛能听见远方的乡音,感受到他们为了生计奔波时脚下的尘土飞扬。这种真实的触感,远比任何二手资料的总结都来得震撼人心。它不是在“研究”一个群体,而是在“倾听”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喜悦、迷茫、对未来的憧憬,以及那些深藏在心底的无奈,都以一种近乎文学化的方式被呈现出来,让人在阅读中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共情,仿佛自己也成了这庞大迁徙洪流中的一滴水珠。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去精英化”倾向。它避免了学术界惯用的那种过度抽象和晦涩的术语堆砌,而是采用了大量直接从受访者口中提炼出的、生动而充满烟火气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策略带来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让非社会学专业的读者也能轻松进入情境;另一方面,它在无形中提升了信息的可信度和情感冲击力。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引用口述材料时所保持的精准度,那些未经润饰的方言词汇和俚语,仿佛带着原生地质的印记,为冰冷的调查数据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它不是在“翻译”他们的生活,而是在努力“复刻”他们的表达。这种对语言原貌的尊重,使得我们接触到的信息不再是经过中介过滤的“二手现实”,而是尽可能接近当事人视角的“第一现场记录”。这种对细节的执着和对底层声音的捕捉,构成了这本书强大的内在张力,让它区别于许多流于表面的社会观察报告。
评分我习惯于在阅读社会议题时,期待一种清晰的问题界定和逻辑严密的论证链条,毕竟,复杂的社会现象最忌讳的就是含糊其辞。因此,一开始我对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有些不适应。它更像是一幅由无数个微小碎片拼凑而成的马赛克画卷,没有一个单一的主线贯穿始终,而是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声音,不断地拓宽我们对议题的理解边界。有时它聚焦于一个家庭的数次迁徙轨迹,详述了他们如何在不同的城市间寻找最优的劳动力交换价格;有时又突然转入对某个特定行业工人群体的深入观察,探讨了他们技能的迭代与市场价值的波动。这种“散点式”的结构,初看之下似乎缺乏传统学术著作的结构美感,但细品之下,才发现这恰恰是作者高明之处。社会现实本就如此碎片化、多面向,单一的线性叙事只会掩盖其复杂性。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拒绝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张无比详尽的、充满褶皱的地图,邀请读者自己去探索那些路径和连接点。它迫使我们跳出“宏大叙事”的舒适区,去直面那些未经美化的、充满矛盾的现实肌理。
评分中国农民工调查中国农民工调查
评分不错!
评分内容差,不符合实际,书的质量也不好
评分公司购买,内容没看过
评分公司购买,内容没看过
评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魏城为此前往中国,与许多农民工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和接触,并采访了中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诸多专家和学者,此外,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也通过接受采访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参与了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讨论。如今,法律社使中国农民工调查成书,以飨读者。,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中国农民工调查作者魏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其间最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少有三个世界之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民工潮人类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率全世界人数最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超过了欧洲和日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要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要扩大内需,而内需从哪儿来,内需主要来自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前景。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要致富,必须靠非农产业,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进行得很快。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的农民比例也非常高,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袁岳(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异乡不再有虫鸣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
评分不错,京东信的过 不错,京东信的过
评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魏城为此前往中国,与许多农民工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和接触,并采访了中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诸多专家和学者,此外,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也通过接受采访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参与了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讨论。如今,法律社使中国农民工调查成书,以飨读者。,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中国农民工调查作者魏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其间最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少有三个世界之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民工潮人类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率全世界人数最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超过了欧洲和日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要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要扩大内需,而内需从哪儿来,内需主要来自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前景。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要致富,必须靠非农产业,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进行得很快。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的农民比例也非常高,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袁岳(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异乡不再有虫鸣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
评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魏城为此前往中国,与许多农民工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和接触,并采访了中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诸多专家和学者,此外,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也通过接受采访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参与了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讨论。如今,法律社使中国农民工调查成书,以飨读者。,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中国农民工调查作者魏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其间最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少有三个世界之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民工潮人类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率全世界人数最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超过了欧洲和日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要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要扩大内需,而内需从哪儿来,内需主要来自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前景。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要致富,必须靠非农产业,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进行得很快。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的农民比例也非常高,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袁岳(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异乡不再有虫鸣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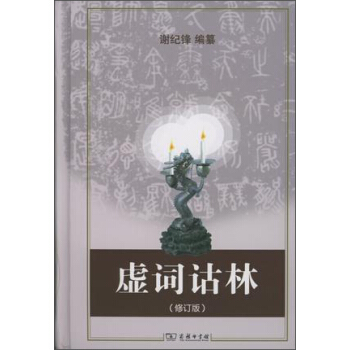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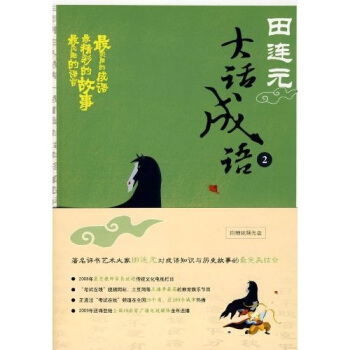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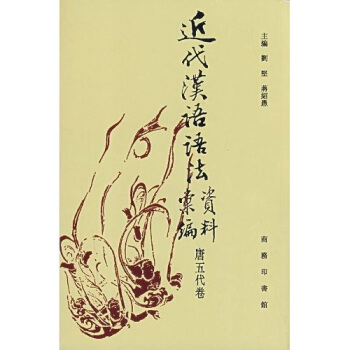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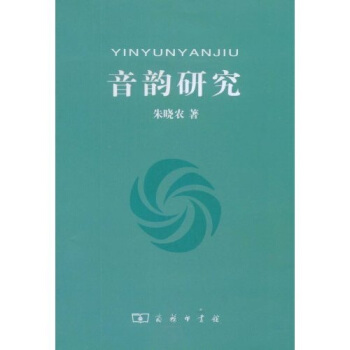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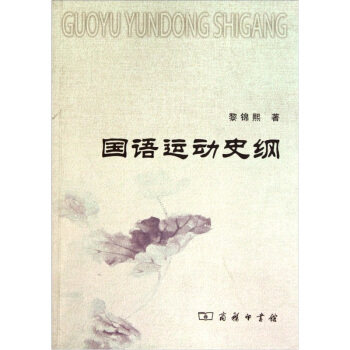

![故事的变身 [Avatars of 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83370/5476c657N2f24f96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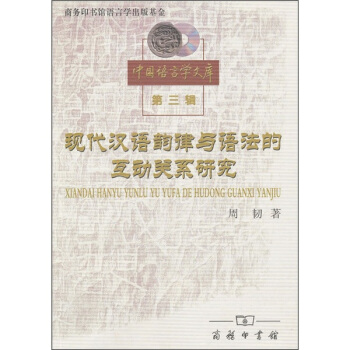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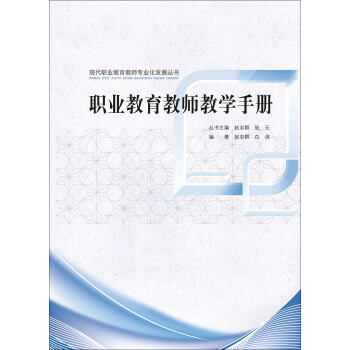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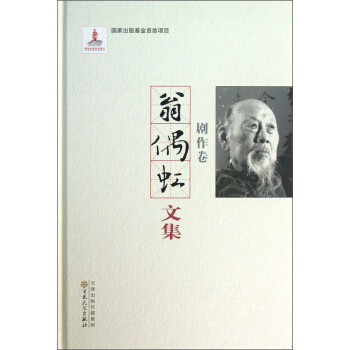





![废墟中的大学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77469/f2fcb2af-954c-43a3-a1e8-e53831d7e042.jpg)